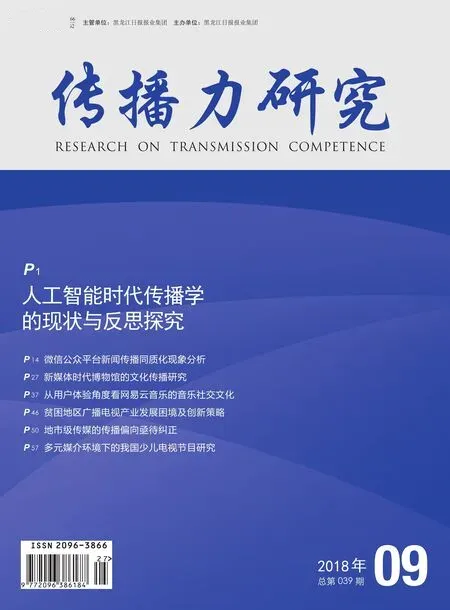女性主義視角下宮廷劇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梁曉琳 澳門科技大學 連云港電視臺
一、研究背景
隨著2018年夏季于正制片的《延禧攻略》的熱播,姍姍來遲的《如懿傳》引起受眾的熱議。事實上以女性為主體的宮廷劇一直是制片方和受眾追捧的對象,雖然廣電總局早在2011年就限制了此類題材電視劇在“黃金檔”的播出,但這似乎并不影響人們的觀劇狂潮。自2011年《甄嬛傳》一劇的成功,《武則天秘史》《羋月傳》《那年花開月正圓》等一部部大女主戲便接踵而至,小說改編、舊劇翻拍等各種載體紛紛被搬上熒屏,數目種類繁多,品質參差不齊,卻仍然引領著收視熱潮,形成全民狂歡式的熱度。
本文試圖站在女性主義的視角,對當下炙手可熱的宮廷劇中的女性形象進行研究,并解析其間利弊。
二、文獻回顧
時至今日,女性的話語權逐漸被賦予,關于女性主義思潮的歷史發展已經引起了社會學、傳播學等學科越來越多的關注,成為近年來文化研究的繁榮領域,但定位在宮廷題材電視劇的研究卻十分有限,筆者對相關文獻作出整理,希望能夠參考前人理論,在這些文獻得與失的基礎上提出創新性的想法。
(一)大眾傳媒中關于女性主義的探討
蘿莎琳德·考沃德所著的《女性欲望》對女性在大眾文化中獲取的快感進行了分析,其考察對象廣涉言情小說、流行音樂、星座算命、視頻等文化文本與實踐,并指明女性是如何被卷入快感和自責的輪回的:“自責,是我們的專利。”[1]作者之所以對以女性為主角的大眾文化感興趣,在很大程度上緣于在過去的時間里,女性主義和這種大眾文化幾乎是同步發展的,雨后春筍般風靡的宮廷劇就是很好的表現。約翰·斯道雷的《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聚焦于文化研究的脈絡和理論演變,對身處大眾文化的女性主義進行了細致深入的介紹。
英國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家勞拉·穆爾維在《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1975)一文中從性別意識的形成這一角度,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將“被看的女人”一說進行了發揮。[2]盡管穆爾維的這篇論文很短,但文中展現的父權社會的無意識對電影形式的建構過程及女性形象在其中作用的分析,層次清晰、態度鮮明,是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的奠基之作,影響廣泛。
相比西方對女性主義在大眾傳媒中的豐富研究成果,目前,國內對此類的探討文獻雖然不乏其數,但整體呈現較為集中、偏向的狀態,如葉暉的《當代大眾傳媒表述女性形象的話語特征》,文中用話語分析方法研究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建構和表達,討論了被忽視或者漠視的女性貢獻,但視角多聚焦于大眾傳媒這個大方向,研究過于寬泛,沒有分類闡述。如蔣暉的《從女性主義視角審視中國女性美》一文,作者沒有從社會學角度出發,而是另辟蹊徑,以美學審視中國女性美的總體特征,思考方式與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大不同,但研究方法卻是值得借鑒的。
(二)電視劇中關于女性形象演變的探討
女性形象在影視作品中的移植和再生時間已久,中國影視作品塑造了眾多的女性形象,有賢妻良母、巾幗英雄,當然還有紅顏禍水、蕩婦妓女,在男性目光的凝視下,這些女性如果吻合男權傳統對女性賢良、忠貞的品德要求,便成為無我的妻子、奉獻的母親或是忠于君王、馳騁沙場的女中豪杰,如《羋月傳》劇中寄托振興楚國以“霸星”出現的羋月,因女性不能繼承王位,而隨羋姝遠嫁秦國,在一步步走向太后、助興秦國富強的路上,先后依附秦王的保護、義渠君的相助等,始終無法跳出男權制社會的怪圈。隨著女性在社會中地位的提升,傳統影視劇中的女性形象典型逐漸不能滿足視野不斷開拓的受眾,熒屏上的女性形象較之前也有了文化鏡像似的演變。“在任何情況下,女性都以特權的他者出現,通過她,主體實現了他自己:她就是男人的手段之一,是他的抗衡、歷險和幸福。”[3]法國女權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著作中從生物學和精神分析學關于女性的觀點出發,闡釋了女性變成“他者”的原因,探討了從原始社會到現代社會的歷史演變中女性所展現的性別差異和不同處境,確證了女性的主體存在意義。
關于電視劇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很多集中在近些年具體的變化上,對女性形象在不同時代不同類別電視劇中的演變進行梳理,分析變化現象及其產生的原因。像是何靜與胡辛的《性別視角與被看的風景》、王玉玨《當代我國以女性為重要角色的宮廷劇中女性形象的演變》等文章。
從以上文獻的回顧情況可以看出,由于性別元素與中國傳統觀念的不一致,學者對宮廷劇中的女性形象的經驗性研究較少,或者說對此涉及不深,筆者對上述文獻進行分析發現,宮廷劇出現的官方限制與大眾熱捧的反差現象、人們對這些宮廷劇的解讀以及如何揭示女性的隱性弱勢地位等等還是很有必要探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