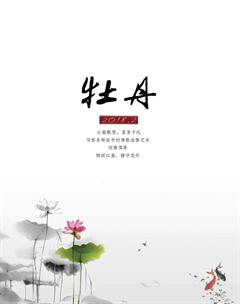守望孤獨
羅浩
“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煙在新建的房屋上飄蕩,小河在美麗的村莊旁流淌。一片冬麥、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我們世世代代在這田野上生活,為她富裕,為她興旺……”二十多年前,彭麗媛唱出的這幅新農村藍圖,今天卻變成了尷尬的現實。
新房建起來了,卻大多數長期沒有炊煙;小河在村旁流淌,昔日魚蝦成群、水草清晰可見的小河卻成了黑水河,臭氣熏天;冬麥、高粱、水稻不見了,取代的是野蠻生長的蒿草與茅草;荷塘、果香成了夢中的場景,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冒著黑煙的一根根煙囪;而小村的主人們如今可能在四面八方飄蕩,這些漂泊的游子發出了無奈的感慨:不要問我從哪里來,因為我已經沒有故鄉。
本世紀初,轟轟烈烈的城鎮化運動讓村里的大部分人離開了他們祖祖輩輩生活的小村,一頭扎進了深不可測的城市。只有少數故土難離的老人還在小村里守望著屬于他們自己的那份孤獨,過去遠離城市喧囂的小山村也隨著這些孤獨老人的離去正在從中國地圖上逐步消失。
我的老家位于湘南茫茫大山中,從村口抬頭看,一條小路蜿蜒伸展,時隱時現、若有若無,最終消失于山上的密林之中,幾排土坯房散落在半山腰上,屋頂蓋著稻草或杉樹皮,帶著一絲原始的野性。四季美景樸素、淡雅。春天,梨花怒放,像天上飄下一朵朵雪白的云霞;夏天,樹木欣欣向榮,青翠欲滴;秋天,遍野金黃,霧繞煙籠;冬天,大雪覆蓋,粉妝玉琢,清新素雅。
村子不大,只有十來戶人家,都是一個家族的,祖先是從另外一個縣過來的,到我這也就五六代,因此人口不多,但彼此離得不遠,雞犬之聲相聞,倒也熱鬧。
20世紀80年代,村里的年輕人開始到廣東打工,村里平時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小孩,小村開始一天天變得蕭條。本世紀初,小村也難逃城鎮化運動的洪流,村里人開始外遷,到鎮上買地蓋房或到縣城買房居住,村里的土坯房也逐漸被拆除。到現在,整個小山村就只剩下了半棟房子,只有一個70多歲的老堂哥還生活在此。
這個堂哥的老婆三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他有三個女兒,小女兒腿有殘疾,完全無法站立行走,也在前幾年死了,另外兩個女兒遠嫁他鄉。他原來一個人住在山上,從小村沿著小路爬一個小時左右的山才能到家,由于山上的房子已經搖搖欲墜,他不得不從山上搬下來。一個人的日子是寂寞的,所以他經常爬山到山頂的一個廟里打發日子,順便修修上山的路。好多次回家,我都發現他家里的門拴著一根鐵絲,然后用一根樹枝穿過鐵絲插在門框上。家里沒什么東西,也沒什么人光顧,已經用不著鎖了,用樹枝穿過鐵絲插住門只是為了防止動物進去。
春節前回去,我再一次到小村里去看看生活了將近二十年的地方變成了什么樣子,尋找童年的足跡。盡管離開小村二十多年了,小村里童年時的圖景總是揮之不去,這大概就是我們常說的“鄉愁”吧!
在山腳下就能看到村里剩下的唯一一座土坯房,這棟房子是當時整個家族最好的房子,中間是堂屋,大門很氣派,門檻是一整條石頭做成的,左右兩邊各有一個石頭門墩,小時候我們經常在門墩上玩。大門上方“秀才第”三個字現在還依稀可辨,聽父母說,家族里曾經出過一個秀才,這是整個家族引以自豪的一件事情。堂屋的北邊有四間房子,當時一個堂伯父住在這兒,現在已經拆了,剩下一堆殘磚爛瓦,上面長著一人多高的樹;南邊還剩下六間房,當時有四間住著另一個堂伯父一家,還有兩間住著這位堂哥的弟弟一家,他弟弟、弟妹都不在了,侄女遠嫁他鄉,侄兒住在鎮上,現在他就住在弟弟曾經住過的兩間屋里。遠遠望去,原來對稱的一棟房子由于北邊被拆了,就像斷了一只翅膀的老鷹一樣兀立在那兒。
我走到房子跟前的時候,他正坐在屋前椅子上曬太陽,由于背弓的上半身與腿近乎90度了,坐那兒被太陽投射到地上的影子猶如一個大大的“逗號”。旁邊的一棵老柳樹被山風吹得枝條亂舞,樹尖上剩下的一片黃葉被風吹得不停顫抖,隨時都有飄落下來的危險。此情此景,我想起了馬克·吐溫的一句話:“為什么你坐在那兒,看上去就像一個沒寫地址的郵封。”
他久久地遙望著遠處重重疊疊的山巒和籠罩著山巒變幻莫測的濃霧,神情呆滯,空洞的眼睛中透著難以捕捉的心思。想著過去,看看現在,真是何事西風悲畫扇,無處話凄涼。
老人的日子在這寂靜的山中已經熔成為黃色的沉渣,在這些沉渣中,他的心里是否也會浮現出一片輕飄的薔薇色的云呢?
跟老人聊了一會兒,我就起身告辭了,我真的無法承受這種苦澀的孤獨。久居城市的人常說:“孤獨和喧囂一樣難以忍受,如果要做出選擇的話,寧愿選擇孤獨。“我們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我們根本沒有真正體味到孤獨的滋味。
一位在寂靜中守望孤獨的老人,有朝一日也將融入這片亙古長存的寂靜中,而曾經熱鬧的小村從此將永遠成為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