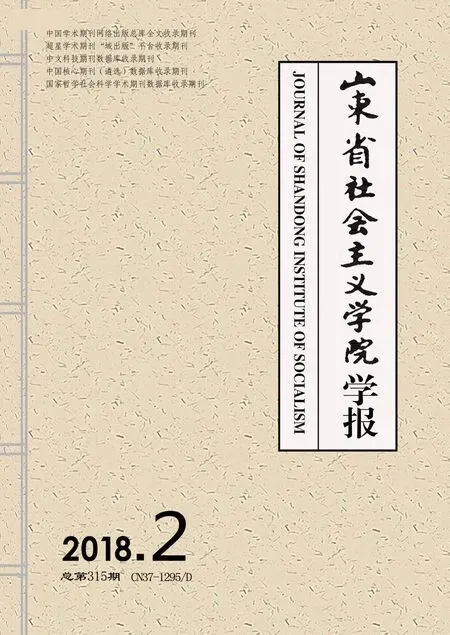《呂氏春秋》的規矩意識及其現代向度
劉 奇 鄭 順
“不以規矩,不成方圓”,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治世名言,“規矩”無論對于個人還是國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呂氏春秋》融合了先秦各家的思想,是先秦時期一部集大成的理論巨著,其核心思想便是治國之道。《呂氏春秋》具有明顯的規矩意識,并首次把“規矩”作為一個政治術語引入到國家治理之中,與禮義和法度密切相關。《呂氏春秋》中的規矩意識具有較強的務實指向,對于當今以德治國、培養公民規則意識等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一、“規矩”內涵辨析
“規矩”一詞由來已久,由“規”和“矩”組合而成。《玉篇》云:“規,正圓之器也。圓曰規,方曰矩。”[1]“規”的本義是指畫圓的器具,“矩”的本義是畫直角或方形的工具。《說文》云:“規,有法度也。矩,巨也。”段玉裁對此注曰:“圜出于方。方出于矩。古規矩二字不分用。法者,刑也。度者,法制也。”[2]可見,從本義上來講方圓與規矩便有密切的聯系,后規矩不斷被引申而成為現代的意義。
“規矩”一詞形成以后,便很少分開使用,常與“規繩”“準繩”“繩墨”“矩墨”等概念并用,如漢朝王符《潛夫論?贊學》:“譬猶巧倕之為規矩準繩以遺后工也。”《楚辭》中有不少描述“規矩”的詩句,如《離騷》:“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宋玉作的《九辯》:“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可見,“規矩”已經成為當時人們的一種行為準則。
在現代漢語中,“規矩”一般引申為一定的標準、法則、常理或習慣,常表示規則和禮法。
二、《呂氏春秋》的規矩意識及其對諸子百家的繼承
《呂氏春秋》著成于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晚期,在對“規矩”的理解方面,也表現出綜合諸子百家的特點。
(一)諸子百家的規矩意識
《史記?夏本紀》記載了大禹治水,“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3]司馬貞索引云:“左所運用堪為人之準繩,右所舉動必應規矩也。”可見,“準繩”“規矩”已經由物質屬性的指向引申以哲學或理性的思考。人們在不斷的生產實踐中,不斷發現了“規矩”對于“方圓”的重要作用,而愈發重視“規矩”對于人類社會的規范意義。
先秦時期,諸子紛紛對“規矩”加以闡發。儒家非常重視“規矩”在禮義規范方面的作用。孔子沒有明確闡述規矩的內涵,但是他在自述中提及“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4]可見,在孔子心中一直有一條“紅線”,那就是“規矩”,隨心所欲也不可為所欲為,也要在“規矩”的框架內。孟子進一步指出:“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5]又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6]孟子指出了規矩對于百姓日用和治理天下兩個層面的重要意義。他認為,只要依循歷史上的法度就不會犯錯了。作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主張以禮治國。他在《荀子?王霸》篇中提出,“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于輕重也,猶繩墨之于曲直也,猶規矩之于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7]禮的本義為祭祀的儀禮,引申為禮法,即規定社會行為的規范、傳統習慣。荀子主張以禮治國,正是強調制定規則對于國家治理的重要性。
墨家同樣認為規矩具有重要意義。《墨子?天志》篇中記載:“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8]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墨家同樣要求人們做事必須符合規矩。同時,規矩也是天志的一種體現,這是墨家對“規矩”的理解,反映出其宗教色彩的天道觀。
管子和韓非子是法家的代表。《管子?法法》篇曰:“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圣人能生法,不能廢法以治國。”[9]《韓非子?有度》篇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斷,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辟大臣,賞善不遺匹夫。”[10]同時,在《韓非子?解老》篇中更進一步認為,“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事,計會規矩也。圣人盡隨于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11]可見,韓非子特別強調“規矩”和“法度”的公正性和不可逾越性。法家是最為看重“規矩”的,他們堅持以“法”治國,主張嚴刑峻法,因此強調不可一日沒有規矩,也不能不懂規矩。
(二)《呂氏春秋》對諸子百家規矩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呂氏春秋》的學派屬性問題一直爭論不休,漢代班固將其歸入雜家,后來又有儒家主體說、道家主體說、法家主體說、陰陽家主體說等。無論《呂氏春秋》屬于哪一學派,它的治國之道中都蘊含著豐富的“規矩”意識,體現了它綜合各家思想的特色。其中,荀子和韓非子對其影響較大。在綜合各家思想的基礎上,《呂氏春秋》采擷各家的思想精華,克服其思想缺陷,比較強調“禮”和“法”并重。“傳統文化意義上的規矩,主要體現在‘禮’與‘法’兩個方面。”[12]《史記?禮書》云:“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這正是對《呂氏春秋》“規矩”思想的準確表達。
《呂氏春秋》中提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不茍論?自知》)。高誘注曰:“規,圓;矩,方也。”這句話與孟子所說“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如出一轍。在《呂氏春秋》的治國之道中凝聚著很強的“規矩”意識。
其一,《呂氏春秋》結合儒家思想,提倡以德治國,主張對民眾施以教化。“禮”是“規矩”積極的一面,循禮也就是遵守規矩,因此禮樂教化就顯得非常重要。古時周公對百姓的教化,就是制禮作樂,制定“規矩”。“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荀子?勸學》),強調了德治和教化對于平治天下、安定百姓的重要意義。《呂氏春秋》中提到:“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離俗覽?適威》)《呂氏春秋》認為君主要以仁義治天下,倡導忠信。
其二,《呂氏春秋》認識到,德治必須輔以法治。“今有人于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為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眾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事出乎不可同,此為先王之所舍也。”(《似順論?處方》)所謂“法”,就是要求人人都要做到的規矩。《呂氏春秋》還改正了法家專任法術、嚴刑重罰的弊病,“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離俗覽?上德》)又說:“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用民有紀有綱。”(《離俗覽?用民》)同時,“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不茍論?當賞》)《呂氏春秋》認為賞罰分明對于治國安邦具有重要意義。
《呂氏春秋》全書多次提到“規”“矩”“繩墨”“規矩”“準繩”等詞,可見其編撰者清楚地認識到“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的深刻道理,其“規矩”意識意義深遠。
三、《呂氏春秋》規矩意識的現代向度
中華民族是一個講規矩的民族,當今時代更是一個講“規矩”的時代,但現實社會中還是存在諸多不講“規矩”、破壞“規矩”的現象,培養公民規則意識任重道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規矩意識的思想寶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寶庫中汲取營養,其中《呂氏春秋》的規矩意識更是直接關乎治國之道,對于當代國家治理亦有借鑒意義。
(一)個人層面
在個人層面,無論對于天子、百官還是民眾,《呂氏春秋》都要求各自遵守相應的“規矩”。首先,對天子的德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天子要加強自身的修養,“反求諸己”,體現在《重己》《先己》《審己》《下賢》《上德》等篇中。《圜道》篇曰:“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要求天子遵循治國的規則,取法其理。其次,君臣各有職分,不得逾越自己的規矩。“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似順論?分職》)就像建造宮殿,作為能工巧匠的臣子,要認真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遵守規矩。再次,百姓要守規矩。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孟春?孟春》)“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季秋紀?季秋》)在不同的季節,制定不同的教化禁令,告訴老百姓所要遵守的規則。
當今時代,對于個人來說,“規矩”意味著遵守社會的規則。以游戲為例,不論參與者年齡大小、性別,必須遵守一定的規則,否則游戲就無法進行下去。游戲規則可以改變,但是不能廢除。人具有社會性,生活在社會中,必須遵守社會的規則。近年來發生了很多不遵守規矩的典型事件,比如八達嶺野生動物園動物傷人事件、“扒高鐵”事件等,都體現出人們規矩意識的淡薄。我們需要大力弘揚《呂氏春秋》的規矩意識,對于不講“規矩”或破壞“規矩”的人,要進行懲罰,最終目的是為了形成規范。“規范之手段,在于賞罰;賞罰之本,在于勸善懲惡。”[13]養成了根深蒂固的“規矩”意識后,人們才能“從心所欲不逾矩”,思想覺悟、道德水平、文明素養隨之提高。
(二)國家層面
對于國家來說,“規矩”則意味著紀律、法律、法規、制度等,這就需要依法治國,以規矩治國。十八大以來,“規矩”一詞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中出現頻率非常高,他還引用過《呂氏春秋》中的相關語句,“說明他非常重視抓規矩和樹立規矩意識的問題”[14]。
要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正確處理治黨與治國的關系。“我們黨高度重視治黨與治國的關系,一方面強調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另一方面強調黨的建設必須緊緊圍繞和服務黨領導的偉大事業,按照黨的政治路線來進行,圍繞黨的中心任務來展開。這些要求深刻揭示了治黨與治國的有機統一關系。”[15]治國必先治黨,治黨旨在治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狠抓黨的紀律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一中全會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后,便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認真學習黨章,嚴格遵守黨章》,提出了黨的紀律和政治規矩的問題。他指出,“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黨章就是黨的根本大法,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規矩。在各級黨組織的全部活動中,都要堅持引導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自覺學習黨章、遵守黨章、貫徹黨章、維護黨章”[16],文章強調了黨章作為全黨總規矩的重要意義,表明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決心。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引用了《呂氏春秋?自知篇》中的一句話“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并強調:“沒有規矩不成其為政黨,更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我認為,我們黨的黨內規矩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和規則。”[17]規矩就是紀律,是不可逾越的警戒線,對于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來說更是生命線。
關于依法治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法律是治國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規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依法治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18]十九大報告也將“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列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體現了以《呂氏春秋》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中的規矩意識在黨的治國思想中地位不斷增強。
參考文獻:
[1]張玉書,陳廷敬.康熙字典[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282.
[2]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01.
[3]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1.
[4]朱熹.論語集注 [M].北京:中華書局,1983:54.
[5][6]焦循.孟子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2017:511,521.
[7]王先謙.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7:248.
[8]孫詒讓.墨子間詁[M].北京:中華書局,2017:189.
[9]黎翔鳳.管子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4:196.
[10][11]王先慎.韓非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98:41,162.
[12][13]李建永.須從規矩出方圓[N].人民日報,2016-01-20(24).
[14]孫業禮.擔當?定力?規矩——學習習近平系列講話中的新概念、新韜略[J].黨的文獻,2014(2):84.
[15]杜艷華.深刻認識治黨與治國的有機統一關系[N].人民日報,2017-04-07(7).
[16]習近平.認真學習黨章,嚴格遵守黨章[N].人民日報,2012-11-20(1).
[17][18]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嚴明黨的紀律和規矩論述摘編[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1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