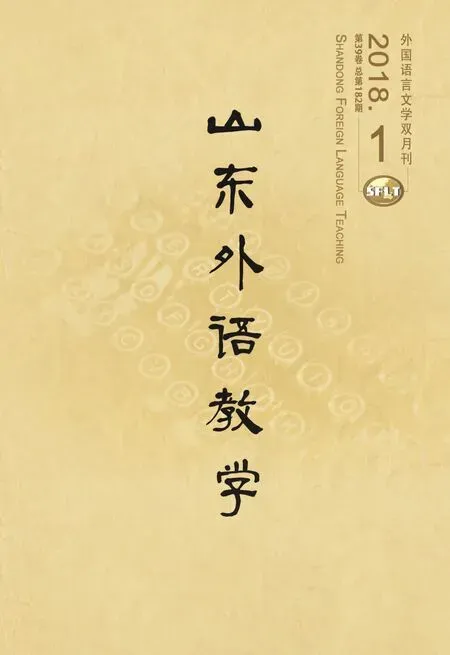喬伊斯文學批評思想中的非洲情結
張敏,譚惠娟
(1.浙江金融職業學院 國際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1.0 喬伊斯非洲情結的根源
喬伊斯(Joyce Ann Joyce,1949- )是當今美國文壇才華橫溢但飽受爭議的非裔文學批評家,在非裔研究、美國文學以及女性研究等領域頗多建樹。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非裔美國人的種族狀況和經濟狀況的改善,眾多美國非裔文學批評家傾向于運用白人主流批評理論來解讀黑人文學作品,而喬伊斯則強烈反對這種做法,主張非裔文學批評理論一定、也必須秉持非洲文化和黑人歷史。她通過專著、文章、演講等各種形式鏗鏘有力地呼號非裔文學理論界堅持非洲情結,對作品無論是批評還是支持,都是對黑人名族的激勵和鞭笞,都是在構筑黑人從中汲取力量的精神家園。喬伊斯濃重的非洲情結是融化在血液中的,是名族歷史和個人經歷的雙重作用形成的。
1619年西班牙海盜船船長為了獲取食物,把17名非洲人作為“人貨”賣到了北美大陸的詹姆斯鎮,這17名非洲人踏上北美土地的腳印開啟了黑人在美國血與淚的歷史,同時也將璀璨的非洲文明之種播撒到北美土地之上。這些來自非洲的黑人奴隸,在奴隸制中繁衍著、煎熬著、斗爭著,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環境。盡管白人社會并不愿意承認,也不把他們當人看,他們還是在殘酷的環境下慢慢變成了非裔美國人。18世紀40年代后黑人奴隸的數量急增,他們帶來的非洲文化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不少非裔美國作家比如詹姆斯·歐鐵斯就指出“所有殖民地的居民都是生而自由的”(Bruce,2001:6)。在這個時期的非裔美國人創作了民間傳說、勞動歌曲和號子、歌謠等民間口頭文學,這成為非裔美國文學的重要源頭之一。經過南北戰爭與馬庫斯·賈維領導的黑人運動的洗禮,非裔美國文學從萌芽階段進入到成熟期,即20世紀20年代的哈萊姆文藝復興。這一時期的非裔美國文學突出種族意識、黑人自我意識和非洲文化意識。到了20世紀30年代一種文化融合主義或者稱作文化同化主義開始蔓延到非裔美國文學批評界,大多數這一時期的批評家認為非裔美國文學不是存在于美國文學之外的,而應是美國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
60年代開始一批批評家以巴拉卡、拉里·尼爾為代表,開始主張“去美國化”的文學理論觀,他們致力于追求探索非裔美國人作為黑人的文化獨特性,這種思想成了60年代到70年代非裔美國文學的核心美學理念。此時也正值喬伊斯的青年時代,喬伊斯承認自己是黑人藝術運動中作家的“帶有學者氣質的學員,(我的)作品反映了黑人美學的理念和風格。①”倡導“黑人權力”的政治主張成為黑人追求自我定義的準則,挑戰美國社會一切不利于這個自我定義的思想和行為。70年代,“黑人權力”運動和黑人藝術運動合二為一(龐好農,2013),后者是黑人政治意識的藝術表達,并強烈反對任何疏遠黑人社區的藝術行為。 黑人藝術是“黑人權利”概念的精神姊妹(龐好農,2013),這兩者對于喬伊斯批評思想的形成影響深遠。
從70年代末期開始,以蓋茨、貝克為代表的非裔美國文學批評家又倡導了一次理論范式的轉變(周春,2016)。他們主張要真正發展非裔美國文學僅僅重視文學文本創作是遠遠不夠的,一定要重視審視以往文學作品中的黑人美學。從而構建黑人文學的批評理論體系,而這種批評理論應該以后結構主義等西方主流文學批評理論體系為基礎。他們在自己的文學批評實踐中踐行了自己的理論主張,開始用后結構主義等西方批評理論解讀美國黑人文學,并建構理論體系。這意味著這一時期的非裔美國文學批評開始注意文本、語言和敘事結構等形式研究,對文本所反映的政治文化等的外圍研究漸漸減少了。無疑,貝克和蓋茨的這些理論和實踐有利于非裔美國文學的制度化、學術化,因此也受到了主流文學批評界的推崇。隨之,許多貝克和蓋茨理論的追隨者也進入了美國的主流教學和科研機構。
然而,非裔美國文學研究應該把政治意義放在首位,還是應該自由展現美學特點,非裔美國文學批評理論到底應不應該把所謂的西方主流批評理論奉為經典,這些幾乎一直在美國非裔文學史和批評史上存在爭議。貝克和蓋茨的批評思想也受到了喬伊斯為代表的文學批評家的強烈質疑,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影響深遠的文學理論論戰。喬伊斯堅定地認為文學的主要功能是喚醒、教育、救贖同胞揭露白人社會對黑人的壓迫、歧視和迫害。文學批評理論也完全沒有必要討好似的套用所謂的西方主流批評理論的框架,而一定要把非洲文化作為文學批評理論的原點和中心。
喬伊斯的個人生活經歷也給她的靈魂系上了非洲情結。喬伊斯的出生地是美國佐治亞州朗茲郡的政府所在地瓦爾多斯塔市,佐治亞州是非裔美國人和黑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占其人口的比重將近三分之一。瓦爾多斯塔曾經是美國長絨棉花的種植中心,歷史上大量的黑人被奴役從事棉花種植。喬伊斯1970年畢業于瓦爾多斯塔州立大學,這一年是瓦爾多斯塔實行種族隔離的最后一年,喬伊斯是該大學早期為數不多的幾個非裔美國學生之一。大學畢業后她進入佐治亞大學攻讀英語碩士學位,1972年畢業后回到瓦爾多斯塔州立大學任教,她是在該校執教的早期的幾位非裔美國人之一。她于1974-1979年到佐治亞大學攻讀美國文學博士學位,先后擔任助教和講師。1979年博士畢業后在馬里蘭大學帕克分校任副教授,1990年作為正教授任教于內布拉斯加大學。1992年在芝加哥州立大學的格溫多琳·布魯克絲研究中心擔任副主任,后成為該校黑人研究所主任。從1997年到2001年在天普大學擔任美國非裔研究所主任,目前在該校的女性研究中心任職。喬伊斯在佐治亞大學就學期間,給她上課的教授幾乎清一色是南方人,許多是在瓦爾多斯塔接受的教育,是重農派或者新批評文學批評流派的后裔。受他們的影響,喬伊斯非常重視文本的細讀。通過羅伯特·斯坦普多和德克斯特·費雪編寫的《非裔美國文學史:結構重構》(Stepto & Fisher,1979: 45),喬伊斯了解到黑人作家批評中居于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學派正在被某個將語言與社會體制隔離的新學派所取代。通過對該書的閱讀,喬伊斯開始理解階級、文化和意識形態三者間的相互關系。
另外,許多非裔文學家和批評家對于喬伊斯批評思想也具有深刻的影響,其中尤以理查德·賴特和索妮亞·桑切斯為重。喬伊斯初次接觸賴特的作品是在讀博期間。一次偶然的機會她閱讀了賴特的《土生子》,立即被主人公比格·托馬斯所吸引,接下來閱讀了佐治亞大學圖書館所有賴特的以及與其相關的著作。最后決定將賴特作為畢業論文的選題,從此開啟了賴特的研究之路。“對賴特來說,生存的最高境界就是無所畏懼的批判思想與公平正義的政治責任并存”(譚惠娟、羅良功,2016:169)。喬伊斯也像賴特一樣“敢于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的文學思想”(譚惠娟、羅良功,2016:178),力求做一個自由思想家,由此可見賴特對喬伊斯的影響至深。喬伊斯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講解和研究桑切斯的詩歌。她理解桑切斯藝術的復雜性,了解并深入研究了其作為一個詩人走向成熟的過程,以及作品的多樣性。桑切斯作為一位女性,一位黑人女性,一位詩人,一位劇作家,她敢于挑戰和摧毀針對黑人藝術、黑人女性、黑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種的反人道主義觀念。喬伊斯在賴特和桑切斯研究上成果頗豐,而她在文學批評思想上的左傾轉向與二者的影響不無相關。
2.0 喬伊斯非洲情結的內涵
非洲情結是對非洲文明的溯源和回歸,它貫穿于喬伊斯文學批評研究的始終,對于她的批評思想具有重要的影響。喬伊斯對于非洲傳統文化的認同和維護體現了其濃厚的非洲情結。
喬伊斯對于非洲傳統文化態度集中體現于其對于非洲中心主義理念的強烈認同。1994年由第三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戰士、巫師和牧師:論非洲中心主義文學批評》是其非洲中心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在該文集中,喬伊斯對非洲中心主義進行了界定,強調其對于美國非裔文學創作和批評的重要價值。她認為基于歐洲中心主義的西方美學批評標準對于美國非裔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毒害頗深。非裔文學作家和批評家應當回歸自我和族群,以創造富有特色的黑人藝術,塑造健康的非裔美國人心理空間(Joyce,1986)。喬伊斯認為美國非裔文學源于非洲傳統,美國非裔文學批評的功能價值也根植于非洲傳統,藝術在非洲是種族性的,是黑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喬伊斯通過作品不斷證明非洲傳統的獨特,欣賞非洲傳統的美麗,宣傳非洲傳統的價值。她把非洲傳統視為非裔美國人(包括民眾和藝術家)的精神之光,不斷撫慰著他們的創傷,同時也銳利著、豐富著他們的思想。因此,“文學批評要與黑人美學保持一致,必須仔細考察美國非裔文化,尋找一直以來貫穿美國非裔文學傳統的脈絡,這條脈絡可以是內容的,也可以是形式的”(Joyce,1986:31),這對于藝術家風格創新、讀者欣賞水平提高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那些偉大而多元化的現代美國非裔文學批評家身上肩負著尋找、繼承和發揚這種傳統脈絡的責任,“通過文學理論傳播非裔美國人應該認知的價值觀”(Joyce,1986:36)。美國非裔文學批評家不應該以任何方式或理由抹煞黑人性,否定被批評作品中的非洲傳統。喬伊斯強調要顛覆白人至上的神話,使黑人藝術永葆生機,需要堅持非洲中心主義的立場,從燦爛的非洲文明中汲取營養(Joyce,1986)。
此外,喬伊斯的非洲情結還間接體現于其對于非洲文化和文學批評傳統的維護。對于后結構主義在非裔文學批評中的應用,喬伊斯持否定態度。1987年喬伊斯撰文對非裔文學批評領域后結構主義的領軍人物蓋茨的后結構主義立場予以了抨擊。喬伊斯認為后現代主義者要傳遞的價值觀和許多讀者體會到的價值觀之間有一種固有的矛盾(Joyce,1987)。后結構主義者反對黑人美學,他們完全脫離美國非裔文學的固有的、重要的傳統,自顧自地首先創造一種理論,然后再去書寫文學作品來適應這種理論(Joyce,1986)。非裔美國人具有“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Joyce,1987:295),一層是對黑人和黑人的非洲傳統的意識,一層是對自己美國身份的意識,“二者融合的媒介恰恰是語言”,而后結構主義者“把語言僅僅看成一種符號系統或一種游戲”,喬伊斯認為現在不是時候也幾乎不可能這樣做,因為許多偉大的美國非裔文學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20世紀60年代和60年代后的詩歌都超越了語言,用價值觀把一個民族團結在一起,公然挑戰后結構主義。喬伊斯坦言自己厭惡專業理論術語,因為這些術語無非是源自現實再將其抽象化而已。有些批評家出于追逐名利的需要不得已而使用歐洲中心主義術語去批評美國非裔文學②。 總之,喬伊斯堅定的認為:“后結構主義情結”是不適合應用于美國黑人文學作品的(1987:296)。
喬伊斯抨擊亨利·蓋茨不應該否定黑人性(blackness)或種族作為分析黑人文學的一項重要成分。她指出“黑人批評家不論采取何種策略,貶抑或……否定黑人性都是陰險狡詐的”(Joyce,1987:292)。喬伊斯認為,黑人批評家就像黑人作家一樣,傳統上認定黑人現實和黑人文學之間存在著直接的關系。黑人作家和批評家的功能是在扮演引導和中介的角色,解釋黑人與壓迫他們的力量之間的關系。蓋茨的文學與學術活動是黑人文學與歐美文學的合并體,蓋茨等于自動放棄黑人作家和批評家傳統上應該承擔的中介角色,接受了基于歐洲中心主義的美國主流社會的精英價值與世界觀,其文學與學術活動,向美國白人社會投降、靠攏,同時更擴大了自己與仍然飽受白人社會壓迫的黑人大眾之間的鴻溝。喬伊斯對于“黑人性”和批評家責任和立場的論述反映了她在文學批評中對非洲中心主義立場的堅持,體現了其濃厚的非洲情結。
3.0 喬伊斯非洲情結的彰顯
喬伊斯在其文學批評實踐中處處彰顯著濃濃的非洲情結。她在進行文學批評時,注重把非洲黑人文化的元素納入文學批評的范式和內容。喬伊斯認為美國非裔文學都源于非洲傳統文化,而且任何對美國非裔文學、尤其是非裔詩歌的理論研究都必須把非洲語言、音樂、舞蹈和宗教置于整個研究的中心位置,語言包括城市、鄉村、傳說中的市井語言,音樂包括圣歌、民歌、布魯斯、爵士樂(Joyce,1996)。
喬伊斯從非洲土著語言中汲取營養,建構其文學批評話語。喬伊斯認為對美國非裔詩歌的批評要使用黑人文化中的術語,尤其是那些黑人聚集區使用的語言,比如班圖語。這些語言的使用可以維系強烈的團結意識,也能夠保持文化活力,這是美國非裔文化發展的基礎(1996:40)。例如其代表作之一《索尼婭·桑切斯和非洲詩學傳統》(Ijala:SoniaSanchezandtheAfricanPoeticTradition)的題目就充分體現著她的這種情結。在約魯巴語言中用不同的詞來描述詩人朗誦詩歌時的音調,比如有艾薩調(esa)、奧弗調(ofo)、啦啦調(rara)等,而伊扎拉調(ijala)指的是一種音調較高的聲音。書名中選用伊扎拉這個詞,一方面因為桑切斯朗誦詩歌時往往音調較高,另一方面因為在約魯巴文化中,伊扎拉調都是由獵人或約魯巴鐵血戰神歐剛(Ogun)的信徒們使用的,暗喻桑切斯用聲音喚醒自己的同胞,用詩歌反抗社會政治壓迫。題目中伊扎拉一詞的使用包含了喬伊斯將桑切斯等同于戰神歐剛信徒的隱喻,刻畫出桑切斯在非裔詩歌傳統中無可比擬的地位。另外,桑切斯認為非裔解放詩歌需要具備六個特征以創造社會價值:功能性、激勵性、教育性、引導性、意識形態性和政治性。非裔詩歌是應一種文化需求而誕生,因此與這六大特征密不可分。喬伊斯使用伊扎拉一詞還意指桑切斯的詩歌具備這六大特征,凸顯其對于各種壓迫的斗爭。
喬伊斯在探討美國非裔詩學傳統時,全文引用了草根瑞格音樂中最偉大的靈魂樂手彼得·湯士的一首歌曲《壓迫者》(Joyce,1996),并將其作為范式,以此可見喬伊斯對于非洲音樂的熱愛。這首歌曲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歌唱了世界末日,運用了圣經典故,另一方面抨擊了種族壓迫和預言了白人對黑人強權的毀滅。“這首歌體現的語言、政治、宗教和音律的特點把處于流散狀態的黑人詩歌關聯在了一起,并洋溢在整個美國非裔詩學傳統中”(Joyce,1996:31),從菲利斯·惠特利到蘭斯頓·休斯再到拉斯·巴拉卡。喬伊斯認為非洲音樂的主題與美國非裔詩歌的主題都具有積極向上的特點。當代歐美白人詩歌多是關于孤獨和絕望,與此不同,美國非裔詩歌歌頌生命、肯定生活,這與非洲音樂的主題是高度吻合的(Joyce,1996)。蘭斯頓·休斯把布魯斯和爵士樂的節奏融入進詩歌,阿米力·巴拉卡、索尼婭·桑切斯等人與樂隊一起表演詩歌。喬伊斯指出音樂不僅是他們詩歌主題的一部分,而且對詩歌的行文格式和詩人的朗誦表演都產生了很大影響。這種把音樂作為一種群體活動的方式本身就沿襲了非洲傳統(Joyce,1996:36)。
喬伊斯還將非洲舞蹈的特征引入其批評話語。 雖然非裔美國作家不得不使用白人的語言寫作,美國非裔文學批評家也不得不使用白人的語言去評析文學作品,但是喬伊斯呼吁“不管作家的文學作品如何具備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一個非洲中心主義的批評家的工作就是利用自己的想象力去解讀這些優秀作品中那些微妙的、被忽視的非洲中心主義特點” (Joyce,1986:111),因為不可能期待歐美白人批評家去發現“那些黑人風格與技巧的微妙和意義”(Fuller,1994:199)。如果說探索桑切斯等人作品中的非洲傳統是明顯的和容易的,那么發掘格溫多琳·布魯克斯詩歌中的非洲傳統就變得很艱難了,因為布魯克斯的詩歌深深扎根于歐洲中心主義語言傳統。經過深入研讀,喬伊斯把她的詩歌從歐美詩學傳統的泥土移植到非洲中心主義的土壤中,發現了布魯克斯詩歌與非洲舞蹈的關聯。布魯克斯的詩歌符合非洲舞蹈的七大特點:多旋律、多中心、空間感、重復、曲線形、敘事記憶和整體性(Joyce,1986:111)。她的詩歌始終將黑人置于主體地位,而不是客體,強調種族價值和形式的整體性。 詩歌就是語言的舞蹈,喬伊斯的解讀是藝術的和理性的。
4.0 結語
綜上所述,喬伊斯早年的生活經歷、教育經歷和工作經歷從一開始就在其心中烙下明顯的非洲印記。黑人權利運動和黑人藝術運動中所倡導的藝術功能、藝術基調和藝術理念對于喬伊斯批評思想的形成影響深遠,奠定了其非洲中心主義主張的基礎。許多非裔文學家和批評家對于喬伊斯批評思想也具有深刻的影響,其中尤以理查德·賴特和索妮亞·桑切斯為重。
她在文學批評思想上的左傾轉向與二者的影響密切相關。可見,非洲情結是貫穿于喬伊斯的非裔文學批評理論和實踐的始終的。一方面,喬伊斯認同非洲中心主義的理念,并專門著述對相關文學批評理論和實踐進行介紹和探討。此外,她致力于維護非裔文學批評的整體性,提倡文學批評家應盡的社會責任,對后結構主義文學批評持否定態度,彰顯了其濃厚的非洲情結。另一方面,喬伊斯在其非裔文學批評實踐中注重從非洲和非裔文化中挖掘適用于非裔文學批評的元素,將非洲土著語言、音樂和舞蹈等語言和文化元素應用于非裔文學批評,極大拓展了非裔文學批評的話語空間和緯度。
注釋:
① 引自Joyce寫給筆者的電子郵件(2017年1月22日),Joyce在郵件中這樣寫道:“I am a scholarly mentee of writers of the Black Arts Movement; thus my work reflects the ideology and style of the Black Aesthetic.”
② 同引自Joyce寫給筆者的電子郵件(2017年1月22日),Joyce在郵件中這樣寫道:“... they use Eurocentric terminology because they think they have to in order to get a job, to get tenure, to be famous, etc.”
[1] Bruce, D. D. Jr.TheOriginsofAfricanAmericanLiterature1680-1865[M].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1.
[2] Fuller, H. W. Towards a Black Aesthetic[A]. In A. Mitchell (ed.).WithinTheCircle:AnAnthologyofAfricanLiteraryCriticismfromtheHarlemRenaissancetothePresent[C].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199-206.
[3] Joyce, J. A.Warriors,ConjurersandPriests:DefiningAfrican-CenteredLiteraryCriticism[M]. Chicago: Third World Press, 1986.
[4] Joyce, J. A. The Black Canon: Reconstructing Black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J].NewLiteraryHistory, 1987,18(2): 290-297.
[5] Joyce, J. A.Ijala:SoniaSanchezandTheAfricanPoeticTradition[M]. Chicago: Third World Press, 1996.
[6] Stepto, R. & D. Fisher.Afro-AmericanLiterature:TheReconstructionofInstruction[M].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979.
[7] 龐好農. 非裔美國文學史(1619-2010)[M].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
[8] 譚惠娟,羅良功. 美國非裔作家論[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6.
[9] 周春. 美國黑人文學批評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