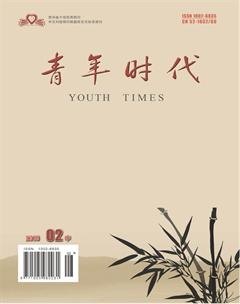《奔月》夷羿形象分析
伍宇平
摘 要:《奔月》的夷羿作為落入世俗生活的戰士,走出了平凡的偉大,而在與嫦娥的愛情中,他作為“獨異個人”為了愛做出了很多犧牲,當犧牲所導致的虛無感不斷積累后,終于在嫦娥奔月后對壓抑已久的虛無進行反抗。反抗失敗后,夷羿從原先的虛無主義轉變成虛妄主義。
關鍵詞:夷羿;戰士;個人;虛妄;犧牲
一、引言
在《故事新編》中,魯迅用“革新的破壞”方式改編了中國傳統的歷史神話。這與用先賢的綱常倫理來證明自己思想的正確性不同,魯迅解構了原有故事中賦予人物的思想倫理,僅保留了故事框架。正如尼采的“重新估價一切價值”,魯迅在傳統文化的解構中,重建起自己對文化的現代性解讀。
《奔月》雖然以“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這兩個神話故事為題材,卻打破了讀者的期待視野,沒有把射日英雄夷羿塑造成一個可歌可泣的人物,而是沿著“人的文學”的思路,解構夷羿的英雄性和傳奇性。魯迅在“油滑”的字里行間,讓讀者對英雄落入世俗生活進行思考。
二、夷羿從射日英雄變為生活英雄
夷羿的功績在小說中沒有用現在時態呈現,而是用回憶往事的方式進行,著重描寫了英雄完成業績后的遭遇。這是魯迅所關注的,即關注人物的命運走向。小說中的夷羿是一個為了物質生活奔波的人,但并不意味著他走向了英雄末路,還沒到連普通人都不如的可悲境地,因為英雄也需要生活。
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中把人格需求分為了5種,其中生理需求指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睡眠等。夷羿和嫦娥對食物的要求是生理需求,而夷羿射封豕長蛇屬于人格理論中的自我實現,這是一種“頂峰體驗”,然而這種自我實現只是偶然事件,并沒有占據生活的全部,不可能每天都有封豕長蛇。在人格需求的金字塔底層仍然是物質生活,夷羿仍要處理瑣碎問題。
魯迅提到:“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奔月》或者其他文章中,都體現了魯迅承認人追求物質生活的合理性。魯迅在《“這也是生活”……》中提到“戰士的日常生活,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實際上的戰士”指的是既能完成可歌可泣的事業,也能處理好生活枝葉的戰士,而不是那種“以為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的單向度英雄。《奔月》的夷羿就是魯迅筆下實際上的戰士,為了能讓嫦娥不再吃炸醬面,他每天廢止朝食,去遠地方尋食物。在兩性關系中,男性會以滿足愛人的需求來實現自我價值,雖然夷羿不能在射擊事業中實現自我價值,但是在愛情生活中實現了價值。
當夷羿射死了老太太的老母雞而被責罵,并且不承認他的英雄身份,夷羿并沒有無休止地與她辯論,而是說“那也好。我們且談正經事罷。這雞怎么辦呢?”夷羿把射老母雞當作是“正經事”,而沒有管別人的侮蔑話語,說明他從一個從事偉大事業的英雄轉化成一個善于處理生活問題的日常英雄了。夷羿敢于直面現實,不再糾結偶然性偉績給他帶來的榮譽,只想先求生存與溫飽,但追求物質需求并不意味著他能夠隨意被“無物之陣”宰割。當面對逢蒙的暗中攻擊時,他卻也能夠保持戰士形象,使出自己的“嚙鏃法”來應對逢蒙,并維護自己的形象,這是英雄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另一種偉大。戰士之所以偉大,也是因為他們滿足了自己的生存欲望而向更高層次實現自我價值。
三、夷羿對嫦娥的愛要求打破隔膜與自我犧牲
魯迅小說常常出現個人與庸眾這兩種文化形象。魯迅說道:“‘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
夷羿是魯迅筆下的“獨異個人”,他曾經為人類射下了九個太陽,讓萬物得以生長。雖然物質生活占據他生活的大部分,但他心里還存在著為人類謀福利的理想,他并沒有因此覺得自己是無用之物,而嫦娥作為一個“庸眾”,她只關注自身物質需求和自我欲望。
夷羿作為“個人”,當他向嫦娥說起自己的豐功偉績時,嫦娥的答語寥寥無幾,“這是封豖長蛇么?”“哼。”“是么?”等。嫦娥似乎無法理解夷羿做出的貢獻,她無法對夷羿的遭遇產生共情,他們之間有一層隔膜,這種由于彼此不了解所引起的冷漠,是嫦娥竊藥離開夷羿的重要原因。“個人”總是試圖努力打破自己與庸眾之間的隔膜,這個打破的過程是以“個人”的犧牲為代價的。
嫦娥拒絕夷羿的價值觀,而夷羿作為英雄個人本可以服下道士給的仙藥而奔月,但是他首先先得替嫦娥打算,于是他就在服侍嫦娥中消耗自我,最終被嫦娥拋棄,也犧牲了吃仙藥奔月的機會。這種“庸眾是最后的戰勝者”是荒誕的效果,英雄每次企圖證明自身價值的行為總是歸于失敗,個人的自我肯定與他人否定造成了內心沖突而加重痛苦,讓人痛心的是,這種痛苦與犧牲是毫無價值的。嫦娥還是奔月了,而且夷羿射月后,月亮“發出和悅的更大的光輝,似乎毫無損傷。”這就象征著嫦娥,在她眼中不過是笑話,發出更大光芒來反抗夷羿的射月行為。“只是這犧牲的適意是屬于自己的,與志士們之所謂為社會者無涉。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
打破隔膜與自我犧牲都源于夷羿的愛。愛是夷羿存在于世俗世界的基礎,也是他的痛苦來源,因為他愛嫦娥,所以習慣了嫦娥的抱怨,連吃飯都惴惴。夷羿對嫦娥的愛是成熟的,他通過自己的努力喚起愛,這體現了他作為“個人”的人道主義,但是作為妻子的嫦娥不但不體諒他的辛苦,還“似理不理”。嫦娥是沒有能力去愛的人,在愛情生活中的她是不斷地“得”,而沒有“給”,因此她在愛情生活中永遠得不到滿足。
然而,夷羿對嫦娥的復仇也是源于愛的。“‘憎的基礎仍是‘愛,因為‘憎是‘愛所無法實現的焦慮和對象化的轉化形式,即對于愛的障礙物的不妥協地拒絕和排斥的情感反應。所以‘憎是深度表征了愛的深度。”夷羿的恨正是因為他對嫦娥的愛太深刻了,他暫時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四、夷羿從虛無走向虛妄
夷羿想要重振當年的雄姿,把月亮射下來,然而他失敗了。夷羿的“反抗”行為加深了夷羿思想的復雜性,射月行為不僅是對庸眾的反擊,也是作為獨異個人對虛無的反抗。首先要辨析存在與虛無這對概念。海德格爾認為,生存的本質在于生存的意義,當人進入世界后,“成為自己的可能性”,便是真實的存在;如果不能實現“成為自己的可能性”,便是不真實的存在,即為虛無。在他發覺嫦娥棄自己而去之前,他表現出來的是一味的縱容,讓他陷入了“無物之陣”,從而產生虛無感,“他終于在無物之陣中衰老,壽終。他終于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
勝者”。
夷羿對虛無的抗戰是無可奈何的現實選擇,是一種對絕望的承擔和對人生尊嚴的維護。射月之后,他從對虛無的反抗中獲得的一絲希望變成了絕望。“月亮不理他,他前進三步,月亮便退了三步。”這種抗戰是無力的,夷羿再次喪失了自身存在的確定性。
在絕望中,夷羿并沒有再次用射月的方式進行反抗,而是“懶懶地將射日弓靠在堂門上”并且還在家傭們面前反思了自己的不足,“莫非看得我老起來了?”“烏老鴉的炸醬面確也不好吃,難怪她忍不住……。”在經過一番自我反省后,夷羿平和地對家傭們說:“還是趕快去做一盤辣子雞,烙五斤餅來,給我吃了好睡覺。明天再去找那道士要一服仙藥,吃了追上去罷。”
最后一段中,夷羿改變行為模式,他要“保存現在生命”。這可以說是從失敗后的虛無轉變成懷有希望的虛妄。“虛妄”是魯迅在《希望》中提出來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虛妄是一個中性詞,希望和絕望是一樣的,它們是存在的,卻都是不確定的,沒有分絕對的否定與絕對的肯定。
夷羿表現出來的虛妄是“在絕望中所熔鑄起來的內在信心。”這是超越希望與絕望的戰斗姿態,展現了作為一個實際戰士的鍥而不舍精神。希望的消逝并不意味著探索的終結,明天雖然是未知的,但是追求也是無止境的。明天不是肯定有希望能讓嫦娥回心轉意,但也不是肯定沒有這個希望,這是生活最真實的狀態。
夷羿完全釋然了,他完成了從反抗絕望到虛妄的轉變。他不再有之前的不安和憂心忡忡,不再去想明天是否一定能追上嫦娥,也不再獨自唉聲嘆氣,而是先處理好現實生活,“吃飽”和“睡好”是夷羿現在最為要緊的事情,剩下的事情就交給時間吧。也正是由于未來的不確定性才使得未來變得有意義,人才能保持對未知將來的期待向往。
參考文獻:
[1]馮光廉.多維視野中的魯迅[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
[2]魯迅.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3][英]亞伯拉罕·哈羅德·馬斯洛.動機與人格[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