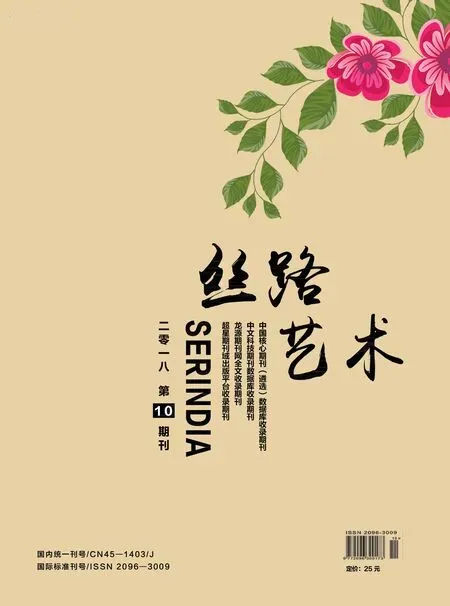李陽冰書風特點淺談
歐寶琛(廣西藝術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0)
李陽冰,字少溫,祖籍趙郡(今河北趙縣),其后徙居云陽(今陜西涇陽),遂為京兆(今陜西西安)人。[1]約生于開元九、十年(721、722)間,卒于貞元初年(785、787)。歷任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將作少監、秘書少監,世稱“李監”。竇臮《述書賦》說:“通家世業,趙郡李君。《嶧山》并鶩,宣父同郡。洞于字學,古今通文。家傳孝義,氣感風云。”[2]李陽冰出身官宦之家,其家族以好學著稱,好的家庭環境對于李陽冰的學書也是極好的。
自魏晉以來迄至初唐,所寫書體,以真、行、草為大宗,隸書絕少,篆書幾成絕響,偶有幾通碑額與志蓋,也不見高明。貞觀后,書科學生雖以《石經》《說文》《字林》為專業,精研小學,善寫篆籀的也不乏其人,顏真卿一族即多以此而名世,但功夫在文字,并不以書法相重。[3]
李陽冰的篆書,舒元輿《玉箸篆志》所稱“秦丞相斯變倉頡籀文為玉箸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代,更八姓,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受以趙郡李氏子陽冰……當時議書者亦皆輸伏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于秦相(李斯)有倍矣。”竇臮《述書賦》以為“初師李斯《嶧山碑》,后見仲尼《吳季札墓志》,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李陽冰學書《嶧山碑》后,書藝大增,書法線條更為挺拔,結字舒朗,筆力雄勁。而秦代李斯的《嶧山碑》開元以前原碑已佚。《封氏聞見記》卷八:“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拓,然尤止官求請,行李登涉,入吏轉益勞敝,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或數片,置之縣廨……今間有《嶧山碑》者,皆新刻之碑也。”
據史料記載,李陽冰碑刻共計50多種,現存的有《三墳記》、《謙卦碑》、《般若臺題名》、《崔祐甫志》等等。孫承澤云:“篆書自秦漢以后,推李陽冰為第一手。今觀《三墳記》,運筆命格,矩法森森,誠不易及。然予曾于陸探微所畫《金騰圖》后見陽冰手書,遒勁中逸致翩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4]《三墳記》是李陽冰的代表作,原石刻早已不存在,現在的石刻是后來重新翻刻的。《三墳記》繼承秦朝李斯《嶧山碑》的篆書特點,以圓潤瘦挺為主,字形偏長,線條粗細勻稱,整篇端正雅致,美妙至極。《般若臺題名》是李陽冰的摩崖刻石,康有為曾言:“篆書大者唯有少溫‘般若臺’,體近咫尺,骨氣遒正,精采沖融,允為楷則。”[5]《般若臺題名》與《三墳記》風格有所不同,《般若臺題名》字體線條厚實且粗細不一,用筆方圓結合,字形變化莫測,與《三墳記》線條不同,《般若臺題名》線條帶有古拙之意,蒼勁雄厚。《崔祐甫志》篆蓋是近年出土的,篆蓋只有僅僅的十二字,線條圓潤,字字規整,‘唐尚法’在篆蓋中能體會到它的‘法’度。
學者曾說:“有唐三百年以篆稱者,惟陽冰獨步。”同時,北宋朱長文在《續書斷》中對唐宋九十四位書家列評,分為“神、妙、能”三品,將李陽冰為神品,顏真卿與張旭也為神品,可見朱長文對李陽冰的篆書評價很高,曰:“自陽冰后,雖余風后激,學者不墜,然未有能企及之者。”
“臺上三分鐘,臺下十年功。”書法則是書家奉獻畢生,李陽冰曾兩度隱居,專研篆書三十余年,復興沉寂千年的秦朝統一全國文字的篆體。以自身為規范,李陽冰刊定《說文》,自此后,起到了規范篆書的作用,少了很多亂作篆的現象。李陽冰的篆書,對后代元朝、明朝、清朝,甚至近代,學篆者無不習李陽冰篆書,李陽冰的篆書是書法篆書史上的經典。
注釋:
[1]朱關田《李陽冰散考》,下同。
[2]《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版,第257頁。
[3]《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朱關田著見124頁。
[4]孫承澤《庚子消夏記》
[5]康有為《廣藝舟雙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