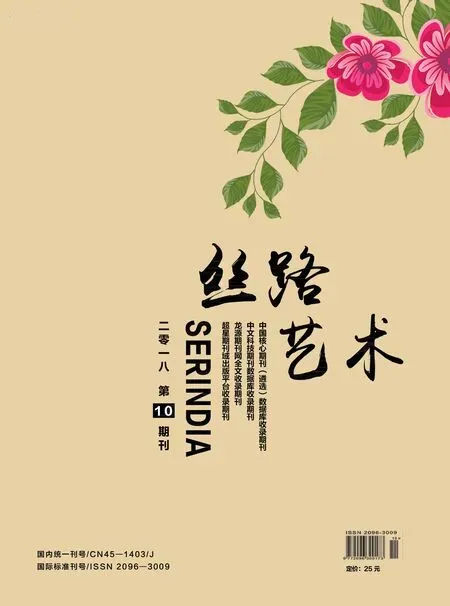論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區基本法的解釋權
朱敏艷(浙江大學,浙江 杭州 310008)
一、事件梗概
2016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選舉過程中,一些宣揚“港獨”的人員報名參選,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主任依法決定其中6名公開宣揚“港獨”主張的人不能獲得有效提名。
10月12日,在新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上,候任議員梁頌恒及游蕙禎等宣誓時辱國并宣揚”港獨”在宣誓時擅自篡改誓詞或在誓詞中增加其他內容,蓄意宣揚“港獨”主張,并侮辱國家和民族。
10月18日,香港特區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裁定,5名立法會候任議員上周在第六屆立法會首次會議上的宣誓無效,需要重新宣誓。[1]
11月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明確了宣誓的法律意義,對宣誓的形式、內容要求與效力問題做了清晰說明。
這當中涉及的《香港基本法》的解釋主體、權限和程序問題值得討論。
二、基本法解釋主體
香港基本法解釋主體主要有兩個,一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我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的時候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權力是中央授予的,而非固有的,這依賴于中央對地方的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同樣也是由中央授權的,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二款規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區法院的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于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對條款自行解釋”。
全國人大對基本法解釋權的主要法律依據是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根據《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享有解釋法律的權力。同時,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是最終解釋,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亦對其解釋權進行了規定:“本法的解釋權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至此可以看出一方面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的解釋對香港法院進行了部分授權,另一方面,人大常委會保留對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那什么情形下基本法只能由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和香港特區法院均可以進行解釋時,應當采取哪個解釋?又該采用什么標準進行判定?
三、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權適用情形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二款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于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對條款自行解釋”。由此,下文將對基本法中的特區自治范圍之內條款和特區自治范圍之外條款的解釋權歸屬進行討論。
(一)人大常委會對自治范圍之外條款的解釋權
香港特區自治范圍之外有哪些權力?基本法第二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政府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那么,在此規定未列舉的權力就應該是屬于自治范圍之外的,比如外交權、軍事權、對行政長官的任命權等,對于涉及這些權力的條款,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解釋權。這種做法和加拿大對于聯邦政府和聯邦組成單位之間的權力劃分方式很像,“遂于憲法上將中央與各省的事權,俱明白列舉。但所列舉者終究不能包括一切事權,于是復以未及規定的殘余權歸諸中央”[2]。其中,需要注意的是,香港特區所享有的立法權,不同于全國人大所享有的立法權,而僅僅是一種地方立法權,也就是說香港特區對香港基本法這種憲法性法律不享有立法權。
似乎香港法院對自治范圍之外條款也具有解釋權,該條第三款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對其他條款也可解釋。但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系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但是,此款規定的香港法院需要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的關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系的條款,基本上涵蓋了自治范圍之外的條款,因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實際上對自治范圍之外的條款具有最終解釋權。
(二)人大常委會對自治范圍之內條款的解釋權
雖然香港法院對自治范圍之內條款具有解釋權,但是這來自于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亦對此類條款擁有解釋權。比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1月作出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對宣誓的形式、內容要求與效力問題做了清晰說明。該解釋所針對的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屬于公務人員管理,應當是政府管理權范疇內的條款。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對屬于香港特區自治范圍之內的條款進行了解釋,此行為符合憲法和基本法對全國人大法律解釋權的規定。然而,問題是:對于香港特區自治范圍之內的條款,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主動解釋的標準是什么?是不是所有條款都可以進行解釋?如果是這樣,對香港法院解釋權的授權就失去了實際意義。筆者認為其解釋應當符合“一國兩制”的精神,有利于國家和特別行政區的穩定和繁榮。
注釋:
[1]中國法院網,5名香港立法會候任議員宣誓被裁定無效,2016-10-18,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6/10/id/2319813.shtml,2016-12-01。
[2]王世杰、錢端升:《比較憲法》,商務印書館,1999,第3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