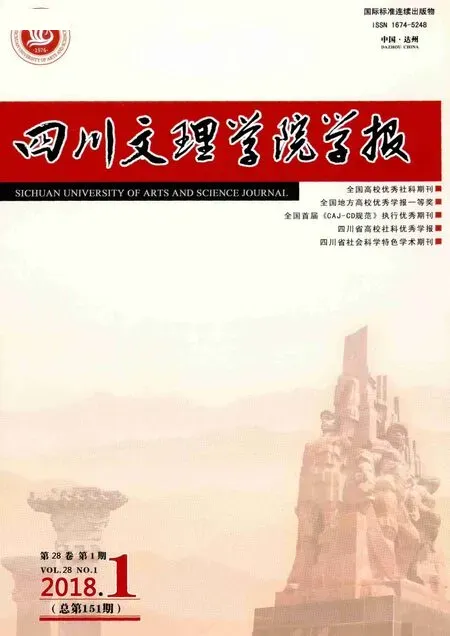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中被拐人利益保護機制之反思
——基于正當防衛的合理性分析
王文霞
(甘肅政法學院 民商經濟法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屬于侵犯刑法所保護的人身法益類犯罪,與侵犯財產類犯罪一同成為當下刑法所保護的重點局域。由于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中被拐賣人所處的人身、社會環境的復雜性,如何合理定性被拐人侵害拐賣人、收買人法益之行為,我國刑法條文規定簡陋,學者討論亦不足。因此,有必要探討被拐人侵害收買人法益的行為性質,以期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結構化完善有所裨益。
一、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之法構造的悖論檢視
學界有學者就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誘因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認為當下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之所以猖獗的直接原因乃在經濟原因,[1]但拋卻拐賣犯罪之社會成因,就該罪的基本法構成上筆者意為其內部仍存諸多矛盾。
(一)被拐賣人自助救濟己身利益時的法缺陷
我國現行立法在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中僅規定了拐賣人的刑事責任,就被拐人對拐賣人、收買人實施的侵害行為,刑法保持了緘默。《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下簡稱《刑法修正案九》)為了進一步保障人權、維護司法公正,將刑法240條第6款中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修改為“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然筆者以為此次立法雖然以側重保護被拐人利益為核心,實現了法典的條文更新,但仍存兩方面問題:
其一,立法的局限于傳統的法構造。此次《刑法修正案九》在立法上以加大對犯罪嫌疑人的處罰為出發點,從而在法規范意義上調整了定罪與量刑的幅度。但筆者認為此條款的修改雖加大了對收買方的懲處力度,但當被拐婦女、兒童為維護自身利益時所實施的行為如何定性,刑法修正案依然固守于傳統的法構造之下,即當被拐人實施的行為侵害拐賣人時可能導致犯罪。然而,作為統一的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之構成,若僅側重于傳統的刑事立法技術則可能對事物相反的忽視使得處于對當事人利益的模式。
其二,現行法構造未全面發揮刑法之社會保障機能。目下,在買方市場潛在存在的情況下,刑事立法固然將刑法的觀測點定位在如何規制拐賣人的行為上有其重要性,但刑法的功能不僅僅在于打擊犯罪,亦在防止犯罪發生。實踐中由于被拐人本身的法益處于高度的危險之中,拐賣人不僅可以隨時實施加害行為,嚴重時亦可侵害他人生命安全等。如若將被拐人的利益保護完全寄托于國家的打拐行動和對拐賣人的制裁之時,刑法本身的功能將無法得到全面發揮。
(二)以故意類犯罪規制被拐賣人行為的正當防衛理論之困局
現實生活中,大量被拐婦女、兒童人身權利得不到及時保護,且囿于所處客觀環境使得相關的公權力救濟無法及時給予,致大量被拐婦女、兒童持續遭受侵害。然當被拐賣人實施侵害收買人之法益時,司法實踐中以故意類犯罪處罰的態勢使得與民眾普遍的法認知相悖,亦與正當防衛制度相悖。詳言之:
首先,與正當防衛時間條件相悖。目前刑法學界關于正當防衛的要件討論上學說各一,但通說認為正當防衛的構成要件為防衛時間、防衛目的、防衛意識、防衛對象及防衛限度。[2]而就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中被拐賣人實施的侵害行為而言,其完全與正當防衛所要求的防衛時間條件相契合。意即,在被拐賣人被綁架、誘騙時起已處于現實的不法侵害中,其已從防衛時間上取得了實施保護自身法益的正當防衛之權利。對此亦有學者指出正當防衛的時間認定,應該從著手實施不法侵害時起,進而不法侵害正在進行,抑或為保護法益的必要而實施的行為,也應認為是正當防衛。[3]只有實施的防衛行為能夠保護自身的法益,就可以認為不法侵害尚未結束,從而認定為正當防衛。[3]因此,司法實踐中對被拐賣婦女、兒童所實施的保護自身法益的侵害行為而言,其理應具備正當防衛時間條件的正當性。
其次,與正當防衛的防衛意識相悖。構成正當防衛除具備時間條件外,還包括防衛意識,防衛意識又涵蓋防衛認識與防衛目的。防衛認識是指行為人對于不法侵害的主觀認知;而防衛目的則指在主觀認知下所實施的行為,并且希望所達至自己心中所預期。防衛意識要求行為人在面對不法侵害時須具有一定的認識與目的,有學者指出在現實生活中很多刑事被害人由于缺乏防衛認識,從其主觀方面而言根本不具有防衛意識,對危險的反抗出于本能,所以只要是在面對不法侵害時實施的防衛行為就成立正當防衛。[4]可見,其將刑法中的防衛意識有所擴大。同時,在現實中當行為人的防衛意思與假想加害意思并存時,行為人認為先前的不法侵害尚未結束,但被害人認為可能存在事后加害行為進而準備進行防御,則構成正當防衛。[4]因此,當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意識到自己的人身權利將繼續遭受不法侵害時,在自我防衛意識促使下便會實施如上述案例所提及之行為。因之,刑事被害人運用事先準備手段以抵御將到來之不法侵害理應成立正當防衛。
最后,以故意類犯罪處之與正當防衛之立法目的相違背。目前,我國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了無過當防衛,就目前我國刑法的規定來看,法律將無過當防衛的范圍限制在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之中,對于一般危及人身利益與生存權利的犯罪予以排除。易言之,對于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進行防衛,導致不法侵害人死亡或者其他結果,沒有超過明顯的限度,即認定為正當防衛,不承擔刑事責任。因此,從現行立法意圖來看刑法設置無過當防衛之目的主要針對故意侵害他人人身權益的暴力性犯罪,且犯罪分子主觀惡性較大。然而,在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之中,被拐賣婦女、兒童實施侵害收買人法益的行為時,主觀上雖出于故意,但此時之故意實乃不得已情勢之下之“故意”,意即被拐賣人對于犯罪后果的發生在主觀上是反對的,其類似于過失犯罪之心態。故在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中被拐人為救濟自身權益而實施的侵害收買人法益的犯罪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若以故意類犯罪處之,與立法目的明顯悖離。
二、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中被拐人犯罪的成因分析
針對司法實踐中將被拐人侵害收買人法益的行為以故意類犯罪進行規制,并忽略民眾普遍的法預測與法認知的情形,需要分析其中立法的深層次原因,方可化解此矛盾。對此,主要有如下三方面原因:
(一)社會、經濟等多因素誘發
長期以來,我國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失衡影響了我國的婚姻結構與養老模式,尤其農村地區經濟落后導致青壯年勞動力大量流失并致使婚姻結構更顯不合理。同時,現階段我國養老制度的建立亦存在疏漏,即其仍處在家庭養老階段,家庭結構的完整與否與養老制度的運行息息相關。[5]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亦正是在此種社會背景之下延展開來。在邊遠山區經濟欠發達、男女比例的失衡,但為維持此種社會養老結構與婚姻模式,從而促使了拐賣類犯罪的多發。
(二)環境因素制約下的被害人欠缺期待可能性
在刑事拐賣類犯罪中由于被拐人在實踐中不僅遭受人身權利的長期被侵害,同時就其心理壓迫性而言也受制于收買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心理上亦遭受再次打擊。同時,從實踐中的諸多案例來看,收買人收買被拐人之后多對其施予二次傷害——實踐中多伴隨的是性侵害、故意傷害、虐待等。[6]故在此種情形之下被拐賣人為獲得自身權益的救濟采取行為時雖兼有報復性成份,但從整體來看其并不具備期待可能性。
(三)刑法觀測點的定勢
學界關于刑法的調整對象曾在長時間內引起諸多學者爭論,有學者認為刑法別于民法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其調整對象不同——破壞法律制度的行為。[7]亦正是長期以來刑法學界將刑事犯罪的觀測點界定在犯罪人的犯罪行為上,天然的在刑事法律關系中將法律的側重點集中在犯罪人一方,進而使得對于被害人的行為觀測往往采取觀測犯罪人方式一樣。因此,才使得實踐中處理被拐人實施的侵害拐賣人、收買人法益的行為采取故意犯罪基本范式。簡而言之,在立法上觀測拐賣類犯罪時不能繼續以傳統的刑法觀測視角為切入點,而應當充分考慮被拐人的生理、心理環境等因素,從而改變刑法長期的觀測點定勢性問題,進而達到對被拐人利益的全面保護。
三、正當防衛視閾下被拐人利益保護機制的構建
承前述,我國拐賣類犯罪的立法構造上存在一定的悖論,忽略了對被拐人客官情事之考量。因此,面對我國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的多發,應盡快構建完整的救濟體系,具體在刑事立法過程中應著力從保護被拐人合法法益的社會救濟與法律救濟兩個方面入手。
(一)賦予被拐人救濟自身法益時的正方防衛之法構成
依前述,被拐賣人在被拐賣后可能基于多種原因實施侵害拐賣人,但此種侵害本身不具備期待可能性。同時,其亦符合正當防衛之法構成。因此,在后續的法律修改中應著重注意兩方面:
一是明確“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在刑法第20條第3款中的法規范地位。我國刑法第20條第3款中對于無過當防衛的范圍限制在“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之中,其對于“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在法律規范的形式化表達上存在欠缺,且“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本身可能基于罪刑法定原則也不能被解釋為屬于“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8]因此,這使得“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中被拐人救濟自身法益時的行為多被作為故意類犯罪處理成為可能。而此種立法不僅不利于被害人自身的救濟行為的實施,亦不利于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打擊。故而,有必要將刑法的無過當防衛之范圍進行有限的擴大,以此切實保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利益。
二是定罪與量刑的適當性考量。對于拐賣類案件不僅要從正當防衛的合理性方面去考慮,而且還要從其犯罪情節與犯罪手段、目的等綜合考慮,進而修改與完善現有相關法律,對于此類行為也應當免于處罰。亦需注意的是,即使在司法實踐中需要對被拐人侵害收買人法益的行為進行懲治時,也絕對不能上升至違法犯罪之高度。法律是維護社會公平的底線,被拐人被拐賣后其本身已經遭受了不公正的對待與權利侵害,如若再將其自救行為一定意義上納入犯罪對其實乃不公。當然,就其過激的報復行為,也不能認定為違法犯罪,充其量進行行政處罰。
(二)完整的社會救濟體系的逐步構建
現下,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日益高發,保障被拐賣婦女、兒童的利益需政府各部門與社會通力協作,建立完整的社會救濟體系。對此,可從如下兩方面入手:
一是公安部門應當逐步、有條件的建立“人口DNA信息庫”制度,從而為打擊拐賣犯罪,遏制源頭市場提供制度支撐。目前實踐中被拐賣人多無法核實其身份,故而政府應該根據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同,逐步推進“人口DNA信息庫”機制的建立,為打擊拐賣犯罪提供有效的數據核查途徑。筆者還認為,相關的政府部門——計生委、民政等部分,在具體的信息庫建設過程中亦應加強人口登記與管理,各省之間整合相關的人口資料,為建立全國統一的人口流動信息制度提供制度基礎。
二是建立快速高效的群眾反饋機制。打擊拐賣類犯罪需要全社會所有機制的參與,尤其我國歷來有聯系群眾的實踐做法,因此,筆者以為需要加強社會大眾對于此類事件的關注程度。同時,還應當加強普法宣傳,對于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應進行宣傳,使社會民眾能夠將拐賣類犯罪積極地反映至相關部門,以便于及時地打擊與解救被拐賣的婦女兒童。
四、結語
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不僅侵害婦女兒童本身的法益,同時亦不利于社會之穩定。然,囿于現行法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法構造之定勢,使得在處理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中被拐人實施侵害行為時與民眾普遍的法預測和法感知相違背,同時亦不利于對該類犯罪的打擊。因此,基于期待可能性和刑法社會保障機能之全面發揮,則應對于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中被拐賣人實施的侵害行為給予必要容忍,并在完善社會救濟措施的基礎上漸進修改刑法第20條第3款之無過當防衛之立法規定,全面保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
[1] 高曉瑩.拐賣兒童罪之犯罪學探析[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0(6):92.
[2] 高銘暄.刑法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63.
[3] 胡東飛.正當防衛的時間條件[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3(6):114-115.
[4] 黎 宏.論正當防衛的主觀條件[J].法商研究,2007(2):65-66.
[5] 靳小怡,郭秋菊,劉 蔚.性別失衡下的中國農村養老及其政策啟示[J].公共管理學報,2012(3):72.
[6] 張瑞軍.拐賣婦女、兒童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J].內蒙古財經大學學報,2013(3):132-133.
[7] 肖 洪.刑法的調整對象[J].現代法學,2004(6):62.
[8] 張 力,龐偉偉.大規模侵權損害救濟機制探析[J].法治研究,2017(1):2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