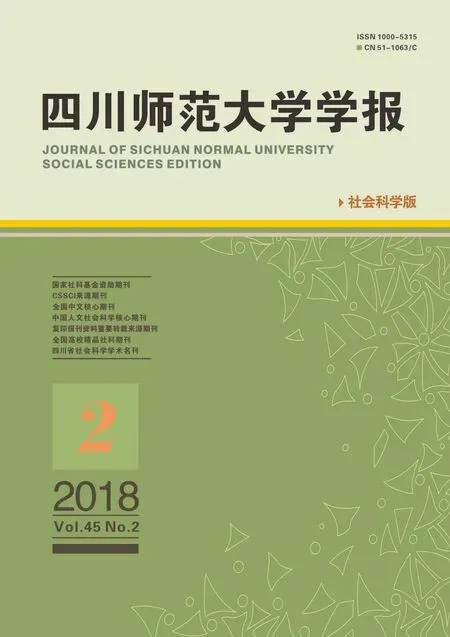“法律信仰”危機與選擇:伯爾曼的問題與方案
(上海交通大學 凱原法學院,上海 200240)
“法律信仰”或許是20世紀最響亮的法律語匯之一,伯爾曼在講演中無數次提及的“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同樣振聾發聵[1]28。由此,伯爾曼的《法律與宗教》進入中國法律人的視野,甚至每個法學院的必修課程都會提到它。然而,這句話本身的光鮮亮麗卻讓我們有意或無意地忽視某些問題:伯爾曼為何會提到“法律必須被信仰”?這個命題旨在解決什么樣的問題?如果解決的問題確定的話,那么有無與之相競爭的理論?對于中國當下而言,是應該把這個論題作為某種“訓誡”,抑或是作為某個解決問題的理論?如此種種問題,盡管長期包含在關乎法律信仰的話題中被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但似乎依舊缺乏有說服力的論斷以及與之相應的深度闡釋。
從一個更寬泛的論域來看,近年來,圍繞法律信仰所進行的論述大多是在認肯其對法治事業起積極推進作用的基礎上展開的,而對法律信仰本身的可能性抱有批評和否定態度的論者則相對較少。但是,對法律信仰論進行批判的觀點,其論證力量卻不容忽視。比如,有論者直言法律信仰本身作為命題的錯誤性,究其原因則在于法律并非信仰的合宜對象,并且也難適中國國情[2]。也有論者從功能視角出發,認為在社會控制方面發揮不同作用的法律與宗教實難合一,并且從有效性的角度而言法律更要求正當合理與現實可行的特性[3]。一些學者在理論移植的角度上指出法律信仰與中國法治實踐之間的內在悖論,并歷數法律信仰與傳統間的鴻溝、在法律信仰的理解上傾向于法律實證主義與工具主義等弊病[4]。還有一些批評聚焦于作為自為領域的信仰與具有可錯性和工具性特征的法律之間的張力,認為信仰法律缺乏法理上的依據[5]。
上述批評多是在一般意義上的法律信仰論上展開的,其中伯爾曼的觀念大多時候只是作為論述的引子或線索,并非論述所關照的中心。而專門以伯爾曼的論述為基礎并在回溯和反思其觀念基礎上進行批評闡述的,當首推范進學先生《“法律信仰”:一個被過度誤解的神話——重讀伯爾曼〈法律與宗教〉》一文,伯爾曼的經典論題在文中得到了重新審視[6]。范先生從歷史的角度闡釋了伯爾曼所提到的“整體性危機”及其應對之道,繼而對伯爾曼的貢獻進行了概括,認為其旨在尋找“法律與宗教的內在聯系,喚起人們對法律的忠誠”;認為伯爾曼所言并非“信仰”,而是“信奉”或“信任”,我國法學界可能都誤讀了伯爾曼;最后對法律信仰的國內研究進行了批判,并提出“信任”模式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范先生的文章或許是在要求我們不要對某些未經仔細辨別的論點采取盲目引用的態度,由此,仔細的尋找文本的原有之意以及澄清可能出現的錯誤成為范文的重點所在。就范文提出的論點而言,筆者同意其對整體性危機的歷史梳理,但不贊成將“信仰”改變成“信奉”或“信任”,對中國語境下的守法模式從“信仰”變化為“信任”也另有異議。下文僅就范先生的論點以及前文之問題展開論述,并就此問題對于我們意味著什么提出某些可能性的思路。
一 整體性危機及其各方應對
西方法律在20世紀遭遇的整體性危機在《法律與宗教》中得到詳述,這場危機是“自我對覓得秩序和意義”[1]8的信心的缺失。而《法律與革命》也在導論中回溯了這一危機,并將其表述為“對作為一種文明、一種社會共同體的西方本身的信念和對9個世紀以來維系西方文明的那種法律傳統普遍喪失了信心”[7]46。按照伯爾曼的理解,法律喪失整體性后,西方文明恐怕也難免受到威脅,固然,這可能是將論題予以放大以引起各方關注的做法,但伯爾曼以此也是為了突顯他所重視的問題:如何重構這種整體性?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這場危機的肇始或許可以追溯到休謨,其“是”與“應當”分離的著名論證實則給出了整體的幻滅,此后邏各斯中心主義的逐漸式微加速了危機的形成[8]509。在法學領域,實證法學運動也擺脫了法律源于某種神秘莫測的教條這一陳舊觀點,而是被當作一種“事實”。邊沁認為法律是符號的集合(an assemblage of signs),因此不涉及價值而僅僅只是事實[9]1。由此,“事實命題”成為了廣義法律實證主義的標志,用事實陳述替代規范性陳述,用“習慣命題”替代合法性命題,成為了19世紀和20世紀西方法學的主流。奧斯丁認為,如果不訴諸于制度事實,就無法說明構成法律的規范是什么,也無法說明作為行為理由的規范是什么[10]1。就作為制度事實的法律而言,對其正當性的判斷,不能訴諸那些有效性不依賴于人類意志和制度的先驗標準;恰恰相反,制度正當性所依賴的不是社會理想,而是社會成規——習慣和慣例[11]723。然而,由實證主義帶動的這場運動卻為自己留下了難解之謎:基于科學的法律體系無法保證其完整性,法律存在漏洞無法避免,邏輯本身不能替代現實的生活。由此,之后的法學思潮便專注于反實證主義(反邏輯)和反形而上學(反自然法),規范性問題被消解,邏輯性問題被放逐,法律在一朝之間幾乎被徹底的現實化。在那個時代,霍姆斯曾用尖酸刻薄的話語揶揄自然法,認為自然法只是“醉漢”眼中的“絕代佳人”[12],而法學家追尋普遍有效準則的努力注定要失敗,“法律的生命在于經驗而非邏輯”的觀點幾乎將實證主義逼得理屈詞窮[13]3。由此,由形而上學來保證的法的整體性成了玩笑,由邏輯來保證的整體性已經讓位于“經驗”,法律不再是整體的,多元論者大行其道,現實主義法學提出的“法律既沒有那么確定又沒有那么明晰”口號幾乎使得法律成為一地碎片[14]187。法律這種分崩離析的圖景引起“規則的懷疑”,面對法律規則的解構,對法律本身“喪失”信心幾乎成為必然[1]19,78。有鑒于此,如何把握和重拾整體之法?
誠如我們所知,20世紀法律的整體性問題也正是規范性的重建,法哲學領域內更是如此。在實證主義內部存在哈特對這一問題的反思,在政治哲學層面羅爾斯通過“實踐性反思”來建立當代的規范性,在現象學領域通過“意向的就是規范的”這一論題而展開討論,德沃金通過“帝國”式的神話所包涵的“正確答案”命題來維系法律的規范性和整體性。當然,在《法律與宗教》中,伯爾曼也試圖面對這個問題,他正是通過法律與宗教的聯系來揭示法律的整體性問題,這也是對“工具論”的挑戰[1]17。
哈特在其根本觀念上捍衛了法律實證主義的基本命題,認為關于法律的“事實命題”、“因襲命題”和“分離命題”是實證主義的關鍵[15]593;但哈特反對奧斯丁“主權者命令”的事實性描述,而且他用“規則事實”替代了“主權者命令”的事實,并企圖用“最低限度內容的自然法”賦予“習慣命題”以規范性[16]193。這些工作旨在通過“法律是第一性規則和第二性規則的結合”這一論題,來重塑關于實證主義的“整體的法”的形象[16]79。但哈特認為法律可能出現漏洞,提出需要法官進行“縫中立法”的觀點,實際上使法律的不確定性得以借此展開,如同一扇“凱卡波爾塔之門”,法律的整體性又將面對法官恣意的危險[16]7。在整體中留下一道無法愈合的傷口,無異于使整體不復存在,似乎也與法律實證主義“基于個人自由的政治共同體不受他人任意的威脅”的宏愿背道而馳。如若從哈特的語言哲學背景來探究,哈特實則是在反對“私人語言”的同時又贊同了“私人語言”,這是哈特理論中的悖論。盡管后繼者力圖挽回哈特學說的敗局,但哈特關于法律整體性的努力從根本上說是失敗的,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實證主義自身難以完成這一任務①。
在解構主義大行其道的20世紀下半葉,羅爾斯以憂思而決絕的情懷與態度扛起了重構規范性的重擔。這決不意味著羅爾斯是無知的——沒有意識到在功利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內外夾擊下重新選擇思考規范的整體性建構問題會面臨多大的質疑與困難;恰恰相反,他正視了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失敗與規范性問題被瓦解的現狀。于是,謹慎的羅爾斯敏銳地選擇了一條回到反思的理性主義道路,康德對于規范性的建構方案成了他最重要的思想來源之一。首先,羅爾斯同意將康德的“道德人”作為其論證的起點,理性的預設將使得個體具備自我選擇與道德行為的能力;其次,羅爾斯原創性地為這種道德主體加上了“無知之幕”的限制,屏蔽掉了社會偶然性因素對于各方主體之偏好的影響,用預設各方在群體生活中的理性選擇代替了古典自然法理論中由對上帝的信念所保證的規范義務,同時拒絕了功利主義以目的來評價行為之正當性的信條。這樣,羅爾斯最終完成了“原初狀態”下的個體進行自我立法的反思性實踐,并保證他們在一般考慮的基礎上得出普遍性的正義原則,以實現對于整體性規范的建構。這種基于反思性的規范建構與思想實驗,從“弱前提”出發,卻可以得出“強結論”,為可接受的正義原則提供可信賴的證明。在此,正義原則之正當,源于“原初狀態”下的個體對“作為公平的正義”的一種普遍共識與彼此同意,而法律的整體性在此作為規范性問題的一部分,也經由正義原則而得以保全[17]91-124。于是,整體性問題在此實現了復活。
如果說羅爾斯是從政治哲學與倫理學的視角進行整體性論證,那么德沃金則致力于構建一個純粹的“法律帝國”以統合法律的整體性。德沃金最早對這一問題的探索體現在其成名作《認真對待權利》中,“正確答案命題”就是其“整體性”法律觀念的基本觀點,他指出,“正確答案命題”本身是一種“前后一致方式的陳述”,并認為“正確答案命題的神話,不僅頑強,而且成功,這種頑強和成功可以證明這并不神秘”[18]290。在隨后的《法律帝國》里,德沃金用“章回小說”和“法官赫拉克勒斯”重新回應了這一問題。德沃金一直致力于提供一種融貫的理解,將“正確答案命題”與規范性問題相聯系,并建構一套對于法律詮釋的整體性論證[19]63。盡管德沃金對于法律帝國的構想同樣是基于反思性實踐,但與羅爾斯的“思想試驗”不同,德沃金的方案是“現象學”的,他采取了“朝向事情本身”的策略,直面法律實踐。在實踐中,規范性“被給予”我們,因為“公平與正義的原則提供了共同體法律實踐最佳的建構性解釋”[20]255。
伯爾曼同樣在直面整體性這個令人糾結與不安的話題。他采用歷史主義的方法,將法律與宗教做類比,初看起來,或許這種分析方法有些牽強,但其論證過程卻是令人震撼的。伯爾曼堅信,法律的純粹國家化很可能將導致其規范性的喪失,西方歷史上每一次革命的過程都是法律的宗教性逐漸被消解的過程,與世俗化相伴隨的是法律神圣性的消褪,權威逐漸被瓦解。事實證明,在法律實證主義甚囂塵上的20世紀,這一問題更加突出,法律幾乎被徹底世俗化,“沒有信仰的法律褪化為僵死的教條”[1]12。于是,伯爾曼面臨著同樣的時代性難題:我們如何走向未來?他從宗教和法律的相似性中得出,法律自身需要保持一種適度的神秘,以維系社會對其規范性權威的一種虔誠。法律是整體的,其規范性的來源使其獲得整體性的保證。與此同時,伯爾曼也試圖通過這種觀念激發公眾對于法律的忠誠,因為“確保遵從規則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和歸屬感,遠較強制力更為重要”[1]17。在此,伯爾曼的觀念是整體的,不論對“法律”一詞作何理解,這都是一個不能進行拆分的概念,因為其目標就在于重塑法律的整體性,并將規范性作為法律整體的基石。由此,在“法律必須被信仰”當中所談及的“法律”是作為整體的法律,并且伯爾曼試圖解決的問題也是“整體性危機”。宗教的關鍵在于信仰,而將法律與宗教做類比后,伯爾曼的方案在于使法律獲得宗教性的高貴,由此對于整體的法而言,論及的也只能是“信仰”。現今由“be believed in”展開的論爭,就伯爾曼的本意而言只能是信仰。
在論及此一話題之時,范進學教授認為伯爾曼視野中的法律“有五種觀念”,因而將伯爾曼總結為“綜合法學”,并指出“法律信仰”是需要區分“法律為何”才能論述的,最終得出“法律信仰”的提法其實不是伯爾曼的觀念[6]。依筆者之見,伯爾曼實際并未區分各種關于“法律”的概念,因為整體性要求我們不能再去進行這樣的區分,即使進行區分也不能將這些不同的概念完全分離開來,因為這一切都在整體之中,而“完整性所需要的視野,這一視野必定超越了現在威脅著要毀滅我們的種種分裂”[1]7,這是伯爾曼論及法律信仰的關鍵所在。由此,伯爾曼指出法律信仰并不值得懷疑,他正是想通過這一論題來直面法律的整體性。其實,糾纏于伯爾曼是否提出“法律信仰”并不是最主要的,這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在于:他試圖通過“信仰”來挽救法律的整體性是否值得?這一問題無疑更具有學術上的價值,用法律的宗教性來維系整體性的觀念的做法是否可能比規范性論證更有意義呢?換言之,我們更應關注的是伯爾曼理論的優缺點,而非他是否談及了法律“信仰”抑或“信任”。
二 有“法律信仰”意味著什么
如前所述,通過歷史性的分析,伯爾曼試圖為20世紀的法律整體性危機提供“信仰”這一藥方,但其效果究竟如何?對此可以循著他的思路來發現問題的根本。在將法律與宗教進行類比后,伯爾曼給出一個新的洞見:“只有在法律通過其儀式與傳統、權威與普遍性觸發并喚起他們對整個生活的意識、對終極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識的時候,人們才會產生這樣的感覺。”[1]35換言之,整體性的法的重生意味著其需要具有宗教的形式甚至實質。可以看出,伯爾曼所論及的“法律信仰”,固然在某種程度上與“宗教信仰”相似,然而這種相似性的觀念意味著什么?對此可能需要將論述稍微拉遠一些。
在今天,“法”被寫進了法典,“美”被用以各式各樣的表演,宗教經驗往往被認為是一系列的意識,人們很容易“技術性”地或“科學化”地認為自己正在經歷人生的神秘,而事實上所完成的是通過技術使自己與真實相分離。在技術世界不斷強化的知識獲得過程中,蘇格拉底式的無知與自省被探知和征服自然世界的雄心所取代,當人們覺得自身對世界的把握是不言而喻的時候,實則只是一種傲慢。伯爾曼多次批評這種傲慢,比如“從事法律的人……不關心終極目的,一味任用理智的怪物”[1]18-24。在法學領域,早期的實證主義者比如邊沁,后來的現實主義者比如霍姆斯,也是這種傲慢的典型。邊沁對法律的“計算”顯得過于樂觀,他試圖通過功利的計算來得到“法律”,乃至于完成一部“完整法典”[21]304-308。與此相對,宗教本身需要完成的第一步則是人承認自身的有限性,從而超越此前看待世界的方式,而對超驗的實在保持謙卑。
宗教信仰的產生,在于對自身置于超自然的在場中的感覺,亦即感覺到自身對超自然事物的依賴[22]10。神秘之物向我們呈現自身,隨之附帶起神秘感的涌現。無論具有何種對神秘事物的信仰,這種超自然的在場,都將呈現為某種可訴諸“神圣”來描述的事物[22]135。而“神圣”事物所引起的“贊美與敬畏”,將可能統合實際經驗中無盡的多樣性。事實上,這就是為何邏輯的源頭不是邏輯的,規范的源頭也不是理性的產物,法律的源頭(有效性)本身也不是基于理性或是事實。在康德凝望沉思于“頭頂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之時,其中的體驗或許也不乏某種神秘,其原因正在于,如果嘗試用理性去應對自然或自由,那人們將一無所獲[23]220。同樣,按照維特根斯坦的觀點,“神秘之物自身自我顯現”,這種神秘本身是“不可言說”的[24]219。這位20世紀的哲學家因此要求“要登上高處之后,把梯子丟掉”,“必須超越這些命題,然后才會正確地看待世界”,這里的超越意味著對事實的超越[24]105。宗教信仰本身被這種神秘感所統領,20世紀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蒂里希曾經這樣做出總結:“信仰不是對某種不確定事物在理論上的肯定,而是對超越日常經驗事物的生存性接受。”“這種不確定事物的存在超越了任何‘存在’的事物,而且任何‘在者’都參與到它。”[25]154由此看來,有宗教信仰意味著我們對超驗事物的敬畏,由此秉持某種終極性的觀念。
這里馬上會產生的疑問是,如果信仰的對象是神秘的,那么信仰如何存在?20世紀的思想家們通過“象征”理論來對此予以說明。象征是指某種可以將我們引向神秘之物的客體,其不同于“標志”:標志僅僅指向客體,象征則超越客體。蒂里希曾經這樣做出論述:“象征式的語言可以獨自表達最終事物,信仰的語言是象征式的語言。”[26]45為著友誼而在朋友之間互相饋贈的紀念品,盡管價值可能微不足道,如若遺失,可能也不會影響與朋友的關系,但作為象征,其重要性往往也是不言而喻的。象征密切關系著我們對超自然實在的經驗能力,宗教本身也就是某種象征,關聯到我們對超越之物的體驗。
上述離題之語旨在說明,基于對個體自身認識的局限性,對神秘事物理應懷有敬畏。信仰完全是一種“內在”的體驗,它超越了理論推理與科學知識的“外向性”態度。有了這樣的認識后,便可著眼于“法律信仰”意味著什么這一問題的思考和討論。如果沿用前述關于象征與標志的區分,我們就可以追問,究竟應該把法律作為純粹的客體還是作為象征?如若當作客體,那便是實然論題;如果是象征,那么意味著法律除了對外在行為進行規制外,還在于對某種價值性的主張和要求,這恰恰是伯爾曼在《法律與宗教》中力圖展現的主旨[1]20-22。
相應地,對于法律的概念而言,伯爾曼持有這樣的看法:“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規則,它是在進行立法、判決、執法和立約的活生生的人,它是分配權利與義務,并據以解決紛爭,創造合作關系的活生生的程序。宗教也不只是一套信條和儀式,它是對人生的終極意義和目標表現出共同關切的活生生的人。”[1]11法律自身既然具有超越性,而我們也可以從傳統中去理解這種超越。法律不是“實然”的規定,不是“客體”本身,而是具有某種終極意義的“象征”,通過這種象征的意義,客觀性、正義、公正等價值才有容身之地。由此可見,伯爾曼旨在通過“法律信仰”來解決整體性危機,法律本身則作為“象征”,有信仰意味著我們把法律視為“內在的”或“自身的”規則,法律既是客觀性的存在,同時又是超越性的存在。此前危機的原因,恐怕就是因為人們“錯誤假定,法律是外在于人的,并非他全部存在的一部分,它與愛,與信仰和恩典無關”[1]92。換言之,有法律信仰意味著我們要向經驗性的法律開放,而且需在直面自身的局限性的同時看到超越的法。
由此可見,伯爾曼以“法律信仰”來克服整體性問題,用超越來統攝法律的事實與實踐,這是將規范性訴諸于信仰的方案。從中我們也需要明確,這一目標顯然是不能通過“法律信任”來完成的。因為信任本身是某種經驗性的而非超越的判斷,信任至多解決守法問題,卻與整體性問題的路徑大相徑庭。伯爾曼的工作實則是在追根溯源的意義上對問題進行的思考,要求從超越中看到法律的整體性。如其所言:“人類隨時隨地都要面對未知的未來,為此,他需要對超越其自身的真理的信仰,否則,社會將式微,將衰朽,將永劫不返。”[1]38這里所說的“超越”是對經驗的超越,最終將指向某種永恒的力量。在多樣性中迷失的我們,將可能借助這種力量獲得整體。
實際上,盡管其本人未必同意,但伯爾曼的理論不完全是論證,某種程度上說倒更像是在運用某種修辭術。他以“法律信仰”致力于法律整體性的努力,同樣可以被理解為是對規范性的訴求,這種努力毫不猶豫地觸及法律最終極也最無道理可講的源頭,而在他看來也就是回歸西方法律的宗教性傳統。伯爾曼在著作中這樣看待規范性和整體性之間的關聯:“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飛躍,我們才能使法律的理想與原則具有普遍性。”[1]30在此,有法律信仰更意味著法律在獲得某種宗教化的神圣力量之后,以整體的方式展現自身。同樣,在個別實在法可能出現與整體性不兼容的時候,我們可以基于整體去對它進行否定,也就是“規則須維護法律最一般的原則”[1]75。
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如果要從非整體的觀念去理解伯爾曼在《法律與宗教》中的觀念,恐怕會出現誤讀。實在法和高級法的分野不適合伯爾曼論及的“法律信仰”,“整體的”才是他問題的關鍵。伯爾曼的進路不同于羅爾斯訴諸理性反思來把握整體性的方式,也不同于德沃金通過反思性實踐去尋求整體性的方式,而是將未知和無知、個體的有限和要面對的無限以及歷史和當下直接呈現出來,從而讓人們獲得對整體的法的虔誠。從這個角度看,伯爾曼具有強烈的存在哲學氣質,他的確也數次以這樣的方式闡釋問題,而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這句:“不再是主體反對客體,而是主體與客體交互作用;不再是意識反對存在,而是意識與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對情感,或者理性反對激情,而是整體的人在思考和感受。”[1]105雖然伯爾曼對羅爾斯的論述頗有微詞[1]195,但筆者并不打算對他們的理論進行比較,而只想再一次指出:伯爾曼的確在談“信仰”,不能用“信奉”或“信任”取代它,他用規范性的觀念在看待法律,我們不能認為他還在分析邏輯的框架中。
三 “法律信仰”作為中國問題
如范文所述,國內在論及法律信仰時,確有將其中之“法律”一詞作實證化理解的傾向。當法律完全被實證化之后,法律信仰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這是因為完全的實證化不能給任何超越留下空間。現階段我們根本無法完成“法律信仰”的構建問題,沒有敬畏和徹底的無神化使得信仰本身只能增加“滑稽感”和“幽默感”[2]。
國內學界對“法律信仰”這個命題的批評,似乎不約而同地集中于其本身作為一個“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概念”這一焦點上[27]206。這固有其根據,但是漏掉了同樣具有根本意味的問題:伯爾曼力圖回答的問題是否具有普遍性?如果伯爾曼提出的問題有意義,甚至對于我們自身的法治實踐有意義,那么盡管其方案相較中國國情而言缺乏針對性,但并不意味著問題本身不值得更深層次的探究。實際上,對于我們自身法律的規范性和整體性而言,伯爾曼的問題是有意義的。盡管在他看來,整體性危機的確是西方的危機,但整體性問題與規范性問題是緊密相連的,難道在我們自身的法律實踐事業中就沒有規范性問題和整體性問題嗎?只要法律或者規則存在,這個問題恐怕便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就法律及其約束力的來源這些關鍵的法理學問題而言,如果繼續沿用強制論的觀點,那么同樣明確的一點就是,一種強制力的有效性在缺乏規范性證成的情況下只會是暫時或短暫的,并且強制的后果只能是反強制,由此伯爾曼才說:“法律只在受到信仰,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強力制裁的時候,才是有效的……法律不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還是生活終極目的和意義的一部分。”[1]17-18如果僅僅把法律視為一系列的規則,那么同樣可能的一點就是,我們遲早會迷失在無數碎片化規則的海洋中,因此伯爾曼才批評說:“法律主要不是法規或者適用這些法規于案件的法律觀點的匯編,不是對如何把法規應用于案件的各種方法加以分析的博學論著和文章的匯集。這些都是專家們頭腦中法律的殘跡……”[1]66
毫不夸張地說,除非拒絕法理學,否則這些問題將會被一直追問和思考。對于現代中國而言,法律的規范性問題需要直面和回應法之為法的原因,規范性不僅作為法律有效性的保證,也與整體性問題的意義相關。當今學界對“法律信仰”和“法律信任”的爭論,幾乎都忽視了伯爾曼的問題,而將其答案與中國現實狀況進行比較,這是令人遺憾的事情。其實,“信任”或“相信”固然有其優點,但本身并不解決規范性和整體性問題,信任是一種互信機制,是“人對他人或者制度普遍存在的一種相信而敢于托付,并通過行動體現出來的具有確定性的意識活動”,而非某種“象征”式的超越[28]。由此,盡管范文在最后部分力圖說服我們用“信任”替代“信仰”,但這兩個命題本身是在解決不同維度的問題,則是不容置疑的。我們無法通過互信機制帶來規范性,也無法通過信任而獲得自我認同,信任也不產生超越性的“終極關懷”。伯爾曼訴諸信仰的解決方案,算是西方法學史上解決整體性危機的可能出路。如果我們拋棄其問題本身,僅就伯爾曼給出的答案予以論爭,實則是一種類似于一葉障目的以偏概全。我們更應關注的是伯爾曼提出的這個宜于深思的問題,而不是簡單地移植和檢驗其教條式的答案。伯爾曼的方案可能存在問題,但這不能算是問題的關鍵。
今天,重新審視法律的規范性問題至關重要。然而,當下的中國面對著更復雜的狀態,試圖將我們自身的規范性問題嵌套進西方理論中的做法無異于緣木求魚。與此相對,國內學界也一直在進行著探索規范性來源的嘗試。比如,有學者追溯我們可能展開的規范性探討的起點,也有學者直接將這一問題訴諸“本土資源”,還有學者要求我們“對生活于其間的社會秩序展開思考和反思”②。在閱讀伯爾曼的時候,我們看到他通過“法律信仰”來完成統合性的努力,我們自身又何嘗不是在進行這樣的努力?從這一點而言,伯爾曼的問題與我們的問題具有某種統一性,但我們的歷史不同于西方的歷史,這注定統合性的努力可能需要選擇其他道路。
其實,只要我們注意到整體性危機與20世紀出現的法律的規范性問題相聯系,我們就不會對伯爾曼的論題產生誤解。在我們的時代,缺乏敬畏與信仰幾乎意味著我們在尋求自身的意義上產生困惑,這不是西方才有的困惑,我們也面臨這樣的困惑。在建立規則的同時,如何注意到規則本身可能具有的超越,不在規則的世界里迷失我們自身,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任務。我們在參詳西方論著的同時,不能只看到論據是否契合中國的國情,我們更應該回到問題本身,這難道不正是法理學應有的態度嗎?
注釋:
①按維特根斯坦的觀點,私人語言不能在語言游戲中表達,排除私人語言是語言游戲這個概念本身的封閉性造成的。從哲學史來看,這一排除則繼續著從“我”到“我們”的轉向。從語用學的角度看,由于“使用”決定“意義”,那么就不可能私人地“使用”語言。關于維特根斯坦的論證,參見: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 tr. by G. E. M. Anscomb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9. p.61, 71, 76, 79, 91. 法律實證主義后有科爾曼所持的“包容性”實證主義理論(inclusive positivism),力圖從中走出一條道路,但這條道路實則已經走到了實證主義的對立面。科爾曼的觀點,見:Jules Coleman.ThePracticeofPrincip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德沃金對科爾曼的批評,見:Ronald Dworkin.JusticeinRob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89.
②起點型的研究往往將論題鋪陳于“我們可能展開現代性的起點”這一問題之上,國內此方面論述頗多,從中國某種特定思潮的轉變入手,探尋我們規范性可能發軔的起點。其中,汪太賢先生的著作是非常有分量的作品。(參見:汪太賢《從治民到民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蘇力先生是“本土資源論”的代表,其實很多人都誤以為蘇力是“后現代”或者“地方性知識”論題的代表,這是一種誤解,因為蘇力的目標旨在“揭穿靠不住的保證,打消虛假的預期”,實際上,他認為“創造不僅是必須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們把蘇力作這樣的解讀,顯然積極得多。“對生活于其間的社會秩序展開思考和反思”是鄧正來先生在《中國法學向何處去》當中的話語。在多年前,許多人都評價過這本書,非常可惜的是“反思性實踐”的觀念依然沒有深入人心,這本是20世紀之后的基本學術規范;更為可惜的是鄧先生的“反思性實踐”的論點當年鮮有評論。(參見: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1]伯爾曼.法律與宗教[M].梁治平,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2]張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J].政法論壇,2006,(3).
[3]范愉.法律信仰批判[J].現代法學,2008,(1).
[4]劉小平,楊金丹.中國法律信仰論的內在悖論及其超越[J].法商研究,2014,(2).
[5]劉焯.“信仰法律”的提法有違法理[J].法學,2006,(6).
[6]范進學.“法律信仰”:一個被過度誤解的神話——重讀伯爾曼《法律與宗教》[J].政法論壇,2012,(2).
[7]伯爾曼.法律與革命[M].賀衛方,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8]休謨.人性論(下冊)[M].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9]BENTHAM J.OfLawsinGeneral[M].London: Athlone Press,1970.
[10]AUSTIN J.TheProvinceofJurisprudenceDetermine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11]COLEMAN J. Rules and Social Facts[J].HarvardJournalofLawandPublicPolicy,1991,14,(3):703-726.
[12]HOLMES O W. Natural Law[J].HarvardLawReview,1918,32,(1):40-44.
[13]HOLMES O W.TheCommonLaw[M].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4]HORWITZ M J.TheTransformationofAmericanLaw, 1870-1960——The Crisis of Legal Orthodox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5]HART H L A. 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J].HarvardLawReview,1958,71(4):593-629.
[16]HART H L A.TheConceptofLaw[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4.
[17]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18]DWORKIN R.TakingRightsSeriously[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9]ENDICOTT T.VaguenessinLaw[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0]DWORKIN R.Law’sEmpir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21]SCHOFIELD P.UtilityandDemocracy:ThePoliticalThoughtofJeremyBentham[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2]魯道夫奧托.論神圣[M].成窮,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23]康德.實踐理性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4]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M].賀邵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5]蒂里希.存在的勇氣[M].成窮,等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
[26]TILLICH P.DynamicsofFaith[M].New York: Harper & Row,1957.
[27]張永和.信仰與權威:詛咒(賭咒)、發誓與法律之比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8]彭泗清.關系與信任研究[M]//中國社會學年鑒(1995-199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