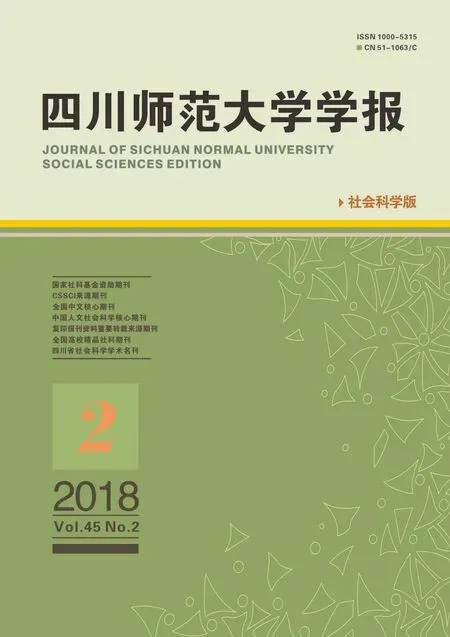《天子游獵賦》的文本書寫、知識來源與思想傳播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從口傳、甲骨、金石、簡帛到紙張、電子載體,只要具備了聲音、文字、圖像的任何一種形式,就會將讀者納入其所要表述的文本世界,最終使得后世研究者糾結于故事真偽、文字異同等問題,而較少關注在此基礎之上形成、存在于文本之外的“文化”、“文明”層次的事情。本文主要談兩個問題:第一,文本之“內”的文字抄撰與流變;第二,文本之外的“文化”、“文明”的形成與傳播。
漢初賦作,在文本形成過程中,會涉及到文本書寫、文本改編以及賦家的知識來源、賦作體現的思想傳遞問題。本文即以《史記》記載的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為例,展開討論。需要說明的是,關于司馬相如此賦,《史記》、《漢書》的記載明確稱為游梁時的“子虛之賦”與后來專門獻給漢武帝的“天子游獵賦”(《漢書》稱為“天子游獵之賦”),《文選》析為《子虛賦》、《上林賦》兩篇。為方便研究,今從《史記》、《漢書》舊題,統一稱此賦為《天子游獵賦》。
一 文本之“內”:作品的多次改編與加工
一部(篇)文學作品自其產生進入流傳渠道,其文字并非完全固定下來一字不易,而是有可能發生各種各樣的改編、加工或重寫。這個工作的實施者,可能是作者本人,也可能是其同時代或后世之人。這是古今文學作品的一個普遍規律。現以《史記》所載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為例進行說明。
第一,同時代人改。
《史記》、《漢書》、《文選》對此賦題名、分篇之差異性載錄,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即《史記》、《漢書》收錄的此篇《天子游獵賦》完全可以分為兩篇獨立定名。問題是,被《文選》分出來的《子虛賦》,與司馬相如游梁時的《子虛之賦》是一種什么關系?劉躍進先生以為,司馬相如游梁時的《子虛賦》,是《天子游獵賦》的初稿;《上林賦》即在此基礎上加工潤色而成,故可稱為《子虛上林賦》[1]72。此說有合理之處。
據此賦內容,可知以下四點。其一,從主旨上看,司馬相如游梁之《子虛之賦》,主要談諸侯園囿;他為漢武帝所寫的《天子游獵賦》,以“天子”事上為中心。《史記》、《漢書》所記此賦,上半部分談楚、齊諸侯田獵事,下半部分談天子游獵事,確實符合司馬相如所言“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之言[2]3640。其二,從內容上看,司馬相如本來所言之“為天子游獵賦”,其內容實際上包括天子、諸侯游獵事,并非單純的“天子游獵”。此據司馬遷所言“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2]3640,“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及子虛言楚云夢所有甚眾”[2]3689可知。其三,從篇章上看,最初司馬相如的《天子游獵賦》,實際上包括司馬相如游梁時的《子虛之賦》全篇(即后來《文選》定名的《子虛賦》,但內容并非司馬相如最初的全文),以及他后來續寫、《文選》定名的《上林賦》。也就是說,司馬相如的《天子游獵賦》,實際上是在他游梁所作之《子虛賦》基礎上續寫的。其四,《史記》、《漢書》所錄《天子游獵賦》,亦非司馬相如最初原文,而是司馬遷根據時代需要進行了刪汰。所以他說:“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云夢所有甚眾,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2]3689司馬遷所“刪”者,當為那些“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子虛言楚云夢所有甚眾”之“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的內容。然而,《索隱》引顏游秦之說,司馬遷所言“刪要”的意思,乃是“不取其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于正道耳”[2]3689。顏師古從之,謂:“非謂削除其詞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剟,失其意矣。”[3]2576大、小顏之說,僅為推測,其實并無版本依據。據司馬遷“刪取其要”之意,筆者以為,司馬遷收此賦時,當因其篇幅過大,已經有所刪削。
由此我們認識到,司馬相如的《天子游獵賦》,在同時代因為時代觀念問題,“非義理所尚”,已經被其他收錄者所刪汰。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最早的《天子游獵賦》,即《史記》所載之文,刪汰之前的全文究竟什么規模,因資料缺乏,已經無法得知。
第二,東漢班固及其此前人改。
《史記》形成之后,其版本文字多有變化,其中的《天子游獵賦》亦受到影響。有些文字變化,顯然是班固《漢書》之前的事。而班固收錄此文,或又有改易;至唐顏師古注《漢書》,則又有變化。
例一:
《史記》: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出田。[2]3641
《漢書》: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3]2534
《文選》(胡刻本,后同):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4]119
《史記》:“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出畋。”其中“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五臣注本《文選》同《史記》[5]卷四。《漢書》、李善注本《文選》作“悉發車騎與使者”。李善注《文選》曰:“本或云‘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非也。”[4]119李善注《文選》,多據《漢書》正文字,此處所言“本或云”,顯然針對的是當時所見其他版本之《文選》,而非《史記》中的賦文。據此可知,李善《文選》注本文字,乃據《漢書》(或與《漢書》文字相同的其他文本),無他本《文選》“悉發”下“境內之士備”、“車騎”下“之眾”數字,且李善注并未參用《史記》所載之賦文。《漢書》與《史記》錄此賦之文字差異,應該是班固或此前人刪改所致。
例二:
《史記》:仆樂齊王……[2]3641
《漢書》:仆樂王……[3]2534
《文選》:仆樂齊王……[4]119
此處《史記》、《文選》同,《漢書》異于二者。五臣注本同李善注本。這說明《文選》版本并未完全采用《漢書》文本的文字。如果《史記》文本的文字并非唐人所改,則《漢書》表述與《史記》的差異,必為班固或其前人所改。
例三:
《史記》: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2]3642
《漢書》: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3]2535
《文選》: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4]120
《史記》所言“蕙圃衡蘭,芷若射干”,《文選》五臣注本同《史記》[5]卷四;《漢書》、《文選》作“蕙圃,衡蘭芷若”。李善注本從《漢書》說,而五臣注本所用文字與《漢書》不同,證明當時對此有不同說法。梁玉繩以為《史記》“射干”為流俗所增;而又引《學林》之說,以為“此段皆四字一句,于文則順,于韻則葉,《漢書》去之,遂不成句法”[6]1414。據《文選》五臣注本有“射干”推測,《史記》文本必非后人妄增;又據《漢書》所載《天子游獵賦》此句前、后文“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昆吾”,“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阤靡”,“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3]2535,皆四字句看,《史記》有“射干”為是。《史記》與《漢書》比較,前者為“古”,后者為“今”,李善注本從《漢書》,不從《史記》,是厚今薄古。據此推測,《漢書》闕“射干”,當為班固或其后人所刪。
第三,東漢至唐歷代讀者所改。
東漢以后,尤其是唐人注《史記》、《漢書》、《文選》,多信《漢書》之說,而對《史記》中的《天子游獵賦》文字多有改易。這一點,梁玉繩《史記志疑》、王念孫《讀書雜志》皆有考證。
例一:
《史記》:射麋腳麟。[2]3641
《漢書》:射麋格麟。[3]2534
《文選》:射麋腳麟。[4]119
按:《史記》、《文選》“腳”,《漢書》作“格”。顏師古注《漢書》曰:“格字或作腳,言持引其腳也。”[3]2535這說明顏師古看到的《漢書》文本有作“腳”的情況。梁玉繩懷疑《史記》文字未必是當時原文,亦或后人改易,故以為當從《漢書》顏師古校定之文[6]1414。然從顏師古看到當時《漢書》文本有“腳”者看,《史記》文字未必經人改易,不過顏師古采取了其中的一種說法而已。由此可知,《漢書》文本中的《天子游獵賦》之“格”字,必班固之后、顏師古之前人所改。
例二:
《史記》: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2]3642
《漢書》: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3]2534
《文選》: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4]119
按:《史記》“惡”,《漢書》作“烏”,《文選》作“焉”。“惡”,疑《史記》本如此。《史記·蘇秦列傳》有“惡足以為塞”[2]2752,知《史記》有此用法。
“澤”下,《史記》有“者”字,《漢書》、《文選》無,而五臣注本有“者”字[5]卷四。五臣注本的說法未知何據,然由此知《文選》李善注本從《漢書》本。據常理,《史記》文本不可能據五臣注本回改文字,則《史記》有“者”字是。《漢書》文字乃班固或其后人改,唐人從之;與五臣注本文字不同的李善注本,其說或亦有所據。
例三:
《史記》:諸蔗猼且。[2]3642
《漢書》:諸柘巴且。[3]2535
《文選》:諸柘巴苴。[4]120
“諸蔗”,甘蔗;“猼且”或“巴且”,芭蕉。此處乃讀音不同所致,疑“猼”乃西漢時期西南方人讀音;“巴”乃東漢以后北方人讀音。梁玉繩以為《漢書》、《文選》之文乃后人妄改[6]1414。
以上諸例說明,一篇作品,乃至一部作品在形成之后,其文字必然經過同時代人、后世歷代整理者的多次改易。其中的原因非常復雜,不一而足。但這足以使我們認識到,文本之“內”的抄撰、流變情況,非常復雜。我們在進入文本,研究其中的版本文字差異之時,有時候只能根據個人學力、學識做出一個符合個人學術觀點的判斷,但這并非一定就是最佳定案,只能算是一個符合研究者本人或者其所在時代學術認識的結論。就此而言,古書版本校勘,是一項非常艱辛而困難重重的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時候不得不需要跳出“文本”,考察文本之“外”的學術情形:即文本形成之后,在接受與傳播領域帶來的文化、文明交流。
二 文本之“外”:作為語言交流中介的作品
據稱揚雄有一部小學著作《方言》,介紹了漢代不同地域對同一事物的不同稱呼。此書一個特點,就是將漢代東南西北不同地區的方言納入進來,近似于一部字典。多數文字,有利于用來解讀漢賦作品。
事實上,漢賦作品,大多使用了各地方言。例如《漢書》所載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中,有“下屬江河”,注引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3]2536司馬相如此賦中,從南方的楚使子虛口中道出北方之語,與其說是子虛通北語,毋寧說是漢初賦作中已經有南北方言融合的趨勢,因此文穎稱“詩賦通方言”。
按照史書記載,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作于游梁之時,后來的《上林賦》作于長安,但二者不僅皆有漢代各地方言,而且多有域外之語。尤其是《上林賦》,作為皇家園林,體現了當時東南西北、域內域外廣泛的聯系,故《文選》注引晉灼之語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系于一也。”[4]126
(一)域內
司馬相如此賦中的某些稱謂,體現了域內四方的密切聯系。
1.境內四方結合之語
(1)《史記》:魚 亙魚 瞢螹離。[2]3658
《漢書》作“魚 亙魚 瞢漸離”[3]2548,《文選》作“魚 亙魚 瞢漸離”[4]124。
《史記正義》引李奇曰:“周洛曰鮪,蜀曰魚 亙魚 瞢。出鞏山穴中,三月溯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為龍矣。”[2]2662
“魚 亙魚 瞢”,乃北方之無是公,將南方蜀地之方言用于北方。
(2)盧橘夏孰,黃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樸,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郁棣,榙木 沓荔枝,羅乎后宮,列乎北園。[2]3671
《漢書》、《文選》文字與此稍異。
“盧橘夏孰”,《文選》注引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4]126箕山,今河南登封、山東鄄城各有箕山,知此說屬于北方無疑。
“黃甘橙楱”,《文選》注引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楱,亦橘之類也。”[4]126引張揖曰:“楱,小橘也,出武陵。”[4]126武陵在長江以南。
“枇杷”,《文選》注引張揖曰:“枇杷,似斛樹,長葉,子如杏。”[4]126南北地區皆有。
“楟奈”,《史記索隱》引張揖曰:“楟奈,山梨也。”[2]3672引司馬彪云:“上黨謂之楟奈。”[2]3672知此為北方之物。
“梬棗楊梅”,《文選》注引張揖曰:“楊梅,其實似縠子而有核,其味酸,出江南也。”[4]126知此為江南之物。
“櫻桃蒲陶”,“蒲陶”,即今之葡萄,原產于西域,一般認為張騫出使西域后傳入中國[7]45,但或者也有其他更早的傳入渠道。
“榙遝荔枝”,《文選》作“答遝離支”[4]126,《文選》注引張揖曰:“答遝,似李,出蜀。”[4]126引晉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粗,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4]126二者皆南方之物。
在此,司馬相如是將南方之物與北方之物、西南之物與東南之物甚至域外之物并列言之。司馬相如賦作于北方,除了說明梁園確實有此類植物,還說明南方對此類植物的稱呼亦被北方熟知。這說明,司馬相如赴梁學賦以及后來作賦,不僅僅使用了他較為熟悉的蜀地方言,而且大量使用了當時中原、西北、江南地區熟悉的事物。
2.方言進入官方語言系統
(1)《史記》:行乎洲淤之浦。[2]3658
《文選》同《史記》,《漢書》“洲”作“州”[3]2458。
揚雄《方言》:“水中可居為洲。三輔謂之淤,蜀漢謂之嬖。”[8]78
司馬相如此處將“洲淤”連言,是合方言為新詞。如果將“洲”視作官話,那么三輔之“淤”與之結合,無疑是靠近京城的三輔方言有進入官話的趨勢。
(二)域外、域內結合之物
此處所言“域外”,主要指的是漢王朝統治區域以外的地區。
(1)《史記》:檗離朱楊。[2]3643
《文選》注:“張揖曰:檗,皮可染者。離,山梨也。郭璞曰:朱楊,赤莖柳也。善曰:蓋山之國,東有樹,赤皮干,名曰朱木楊柳也。”[4]120
《文選考異》:“注‘善曰蓋山之國東有樹’,袁本、茶陵本‘蓋’上有‘有’字,無‘東’字。案:二本是也。此所引《大荒西經》文,依善例‘曰’下當有‘山海經曰’四字,二本仍皆脫。”[4]866今《山海經·大荒西經》:“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支干,青葉,名曰朱木。”[9]413“朱木”后無“楊柳”二字。據文穎注,疑《山海經》舊文當作“朱楊”二字,“木”為“楊”之誤,“柳”為衍文。
據司馬相如賦,“朱楊”當為南方植物,而《山海經》則曰《大荒西經》之“蓋山之國”有此木。“蓋山之國”雖不明具體位置,相對于漢王朝而言,或本為域外之物。
此以域外、域內之語混用。
(2)《史記》: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2]3643
《文選》:“郭璞曰:‘蟃蜒,大獸,似貍,長百尋。貙,似貍而大。犴,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蟃,音萬。’善曰:《山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又曰:‘幽都之山,其上有玄豹。’郭璞曰:‘黑豹也。’”[4]120此處所言“白虎玄豹”,皆見于《山海經》,前者出《西山經》,后者出《海內經》。“鳥鼠同穴之山”,在邽山以西二百二十里處,《山海經》說:“渭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9]64此地即秦漢之首陽,西戎所居之地。“幽都之山”,在“北海之內”,《山海經》說:“黑水出焉。”[9]462疑在先秦時期小月氏國境內。
此上屬于將域外之語用于域內。
(3)《史記》:獸則牜 庸旄貘犛。[2]3667
《漢書》作“其獸則庸旄貘犛”[3]2556,《文選》作“其獸則 犭 庸旄貘牦”[4]125。
《史記索隱》引張揖曰:“旄,旄牛,狀如牛而四節生毛。貘,白豹也,似熊,庳腳銳頭,骨無髓,食銅鐵。音陌。犛音貍,又音茅,或以為貓牛。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毛可為拂是也。”[2]3668
《漢書》顏師古注:“庸牛即今之犎牛也。旄牛即今所謂偏牛者也。犛牛即今之貓牛者也。”[3]2556
“庸”,《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虜魄、璧流離。”[3]3884-3885“封牛”,即“犎牛”,知此當主要為域外之物。此以域外之物作為域內之語。
“旄牛”,顏師古以為是“偏牛”,即黃牛與牦牛雜交所產之牛。主要產于藏區,屬漢王朝統治區外之物。
“貘”,《說文解字》:“貘,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10]457知此乃蜀地之物。
“犛”,顏師古以為“今之貓牛”,同今之牦牛,“徼外”,即塞外、邊外,知其亦漢王朝統治區外之物。
在此,司馬相如將漢代蜀地及其與之接壤的吐蕃之物寫入北方皇家園林賦中,體現了南北、東西、域內外密切的經濟聯系。而域外、域內四方之物進入漢賦作品,則又具有體現文化傳播的意義。
三 《天子游獵賦》的知識來源與思想傳播
如果按照《文選》分篇法,可以將《史記》中的《天子游獵賦》之上、下部分,分別稱為《子虛賦》與《上林賦》。二者關于校獵的描寫,卻有雷同之處。
《子虛賦》子虛之言:
其上則有赤猿蠷蝚,鹓雛孔鸞,騰遠射干。……于是乃相與獠于蕙圃,媻珊勃窣上金堤,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鴐鵝,雙鸧下,玄鶴加。[2]3643-3653
《上林賦》無是公之言:
然后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飚,乘虛無,與神俱,轔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鸃,拂鹥鳥,捎鳳皇,捷鴛雛,掩焦明。[2]3681
“翡翠”,據顏師古說,乃紅羽、青羽之鳥[3]2534。
“孔鸞”,《史記集解》引郭璞曰:“孔,孔雀也。鸞,鸞鳥也。”[2]3648
“鵕鸃”,《漢書音義》以為似鳳;司馬彪以為即山雞[2]3681。
“焦明”,《史記索隱》引張揖說,此乃似鳳之西方之鳥[2]3681。
這段材料較有意思,所以列出來比較一下。子虛言“鹓雛孔鸞”,無是公即言“遒孔鸞”、“捷鴛雛”;子虛言“揜翡翠”,無是公即言“掩焦明”;子虛言“射鵕鸃”,無是公即言“促鵕鸃”。
這段相似度頗高的文字表述,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本來就是不同時期的二文拼接而成的。同時,我們也認識到,此類異方珍奇,多非司馬相如親見之物,而是他在為文需要情況下的虛構之物。
但是,這種“事物虛構”,必然也有一定的“實物”做參照。從其學賦的背景看,應該有多重的知識來源。
首先,《天子游獵賦》中保存有大量蜀地事物,顯然這些詞匯來自他本人在蜀地時的學習與見聞。司馬相如為蜀郡成都人,《史記》記載他:“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2]3637《史記索隱》稱:“文翁遣相如受七經。”[2]3638這些記載,足以說明司馬相如早年在蜀郡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其次,《史記》又記載,“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2]3637。可以說,司馬相如免官赴梁,遭受了一定的經濟、政治損失,卻為其學習辭賦寫作提供了很好的條件。梁王卒時,“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但他卻是“以貲為郎”。他離開京城赴梁,主要是為了學習辭賦,所以《史記》說他離開的原因之一是“會景帝不好辭賦”[2]3637。問題是,司馬相如赴梁,對其學習辭賦有何意義?由此處記載分析,可知兩點:第一,司馬相如從游“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為其了解東方齊地、江南吳地的語言奠定了基礎;第二,司馬相如的《子虛之賦》是在“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之后的產物,這說明他在梁地的這段時間基本上掌握了辭賦寫作的技巧,并為其撰寫辭賦儲備了素材。
最后,司馬相如之所以辭官赴梁,是因為梁地有不亞于京城的一切條件。據《漢書》記載:梁孝王藩國“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于京師”,“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3]2208,2209,這或者是司馬相如勇于辭官的外因。即如對學習辭賦較為有益的自然景物而言,梁孝王園囿絕對不亞于皇帝園囿。《漢書》記載梁孝王“筑東苑,方三百余里”[3]2208,其中珍奇動植物亦或不亞于京師,這也是司馬相如能夠熟知諸多動植物的重要原因。
解決了以上問題,我們就能明白,為何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包含著域內四方、四夷甚至域外等眾多事物。這在思想、文化傳播上給我們如下啟示。
第一,漢初文化、文明的傳播,與經濟傳播的速度一樣,是非常迅速的。雖然有人考證,葡萄是張騫之后傳入中國,但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提及葡萄,說明葡萄的傳入可能不止西域一條途徑,與蜀地接壤的西南方向也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傳入渠道。這樣的話,作為經濟作物傳入的葡萄,進入漢初賦家作品,則具有了東西方思想、中外文明交流的意義。
第二,西漢統一之后,中國內地四方的語言、文字、文化的傳播同樣迅速。秦統一雖然短暫,但文字的統一,為內地人民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至漢初,這種交流的成果之一,就是各地方言或進入官方語言系統,或雖保留著本地方言稱謂,但已經為各地人民所熟知。身在梁地的司馬相如,非常嫻熟自如地使用南北方言,即說明了這個問題。
由此我們想到一個問題:漢初賦作,之所以受到歡迎,除了能夠體現漢王朝思想、文化的統一,還有利于上層貴族和各地人民了解其他地區珍奇異物和語言習慣,滿足了人們對知識的學習欲望。
第三,進一步分析,從《天子游獵賦》體現的語言文字與事物的交流看,早期中國與域外文明交流的發達程度可能遠超我們今天的想象。有人認為,商代鬼方、周代犬戎的駕馬御車,就與中亞草原上的卡拉蘇克人密切相關;今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出土有卡拉蘇克晚期青銅器,說明可能有融入周文化的卡拉蘇克人文明[11]48。這是一種非常大膽的推斷。如果此說成立,那么,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司馬相如時代漢王朝與中亞、南亞、西亞甚至西歐、北非存在著一定的文化、文明交流。
總之,一個文本形成之后,學術研究者關注的是如何商榷真偽,而普通民眾關注的則是該文本所承載的文化思想及其社會價值。就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而言,后世文獻學家關注的是其文本文字的正誤,而文本閱讀者則從中看到了知識的學習與思想的傳遞。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如何實現從史料(文獻)進入文本,繼而跳出文本,觀察史料(文獻)在文化、文明交流過程中產生的思想內涵,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可以說,清代乾嘉考據學派之前的中國學術,極少考慮文本內部存在的各種復雜性問題。即如明人印書多改字,并非他們無知,而是他們更看重文本承載的義理,而非單個文字的正訛。唐宋以前的經學、文學、史學,無不如此。這一點,需要我們在開展學術研究的時候,除了關注文本之內的“文字”,還要關注文本之外的“義理”。古代中國對文本的觀念,并非后世乾嘉學派或疑古學派那般較真文字之真偽,而是更關注“義理”層面的傳統建構問題。
[1]劉躍進.秦漢文史論叢[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2]司馬遷.史記[M].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
[3]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4]蕭統.文選[M].北京:中華書局,1977.
[5]五臣注文選[M].影印本.臺北: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1981.
[6]梁玉繩.史記志疑[M].北京:中華書局,1981.
[7]〔美〕勞費爾.中國伊朗編[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8]周祖謨.方言校箋[M].北京:中華書局,1993.
[9]袁珂.山海經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0]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1]林梅村.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