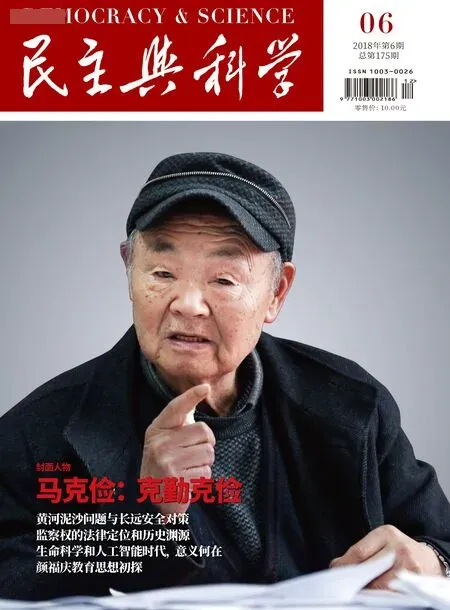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與水資源可持續利用
◎ 沈彥俊
隨著自然環境的變化和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黃河流域的生態環境也正經歷著巨大的變化,水資源、水環境、水生態問題和各種矛盾日益突出。從流域整體來看,上游植被退化、中游水沙銳減、下游用水緊張、河口三角洲退縮等,成為黃河流域面臨的新問題,對流域的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提出新的挑戰。以下從氣候和社會經濟變化兩個方面出發,基于流域水循環和生態水文學原理,對黃河流域面臨的主要生態環境問題進行粗線條的梳理和解讀,以求為該流域的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路徑選擇提供參考。
一、黃河流域水土資源概況及近期氣候變化背景
由于河水泥沙含量大,黃河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改道。黃河東出洛陽后,下游河道發生大幅度擺動,沖擊形成華北平原,入海口位置北至天津,南達連云港以南。黃河流域的多年平均降水量為450毫米,多年平均徑流量560億立方米,年輸沙量16億噸。由于水資源管理粗放,在上世紀末期曾經歷多次斷流,1997年下游最長斷流日數曾高達226天。
黃河流域的總人口約為1.13億,有效灌溉面積751萬公頃。目前,流域糧食產量占我國糧食總產量的11%,對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起到重要作用。隨著經濟發展,流域取用水量也發生巨大增長,據《黃河流域水資源公報》顯示,偏豐水的2003年(降水距平+24%),流域的總取水量430億立方米,其中地表水為300億立方米,總耗水量為336億立方米,地表水消耗243億立方米;平水年的2013年(降水距平+8%),總取水量增長到530億立方米,地表水為404億立方米,總耗水量為430億立方米,地表水消耗330億立方米。取水量和耗水量都有顯著增長,為流域水資源的管理和生態環境保護帶來較大挑戰。
黃河流域地跨多個氣候區,處于青藏高原的源流區,受氣候變化影響顯著。半個多世紀以來,以增溫和降水增多為特征的氣候變化使源流區冰凍圈發生巨大變化,主要表現為冰川融水增多和凍土層融化加速。伴隨增溫的影響,該區域雖然在局部地區出現沙化現象,但整體上植被生長趨好、耗水增多,因而源流區產水量呈現減少趨勢。蘭州以下的上游地區,灌溉農業發達,水電和灌溉的發展對黃河水資源影響增大,主要體現在河流水文受閘壩調節和農業灌溉的影響上,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灌區節水與水鹽平衡的矛盾。自頭道拐到花園口的中游黃土高原地區是黃河泥沙最主要的來源區,過去40多年的水土流失治理和大小型水庫建設,對水量和泥沙都起到極大的削減與攔截作用。花園口以下的下游地區,黃河來水量極小,主要起到將水沙輸移入海和為下游引黃灌區提供灌溉水源的作用。相關的科學研究表明,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對黃河水文水資源影響的貢獻率在上、中、下游有顯著的不同。在上游地區,氣候變化影響占主導作用,貢獻率可達75%以上;在中游地區,氣候變化的影響降為40%;而在下游地區,則主要受人類活動的影響,氣候變化的影響僅為1%左右。
近期,在社會經濟取用水量快速增加的同時,黃河徑流量和輸沙量都呈顯著減少趨勢。目前,黃河的年輸沙量僅3億噸左右。黃河最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是源流區脆弱的生態及其退化風險、上游灌區節水與水鹽平衡的矛盾、中游嚴重的水土流失和下游不斷抬升的河床。快速增長的社會經濟需水以及水沙情勢的變化,對黃河流域的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提出更多新的挑戰。
二、黃河中游的水沙變化及其未來趨勢
過去40年間,國家在黃河中游地區實施了前所未有的水土流失治理工程,遙感監測結果顯示,潼關以上的渭河流域林草覆蓋度自1978年以來顯著增加。2010年前后,黃河水利委員會對黃土高原50余處地點進行無人機拍攝,相比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航拍照片,植被覆蓋度大幅度增加,曾經的荒山荒坡都被繁茂的植被覆蓋。坡耕地的梯田化、護坡工程和大量不同規模的淤地壩等水保措施都發揮了顯著的水土保持效應。以陜西省綏德縣韭園溝為例,1984年,兩道淤地壩都蓄積徑流,呈現中型塘壩的景觀;而2010年,則成為完全淤滿的壩地,呈現一片農田景象,周邊山坡的植被也很繁茂。黃土高原發生的這些植被變化顯示生態明顯好轉,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獲得了顯著的保水保沙效果。科學觀測數據也表明,當小流域林草覆蓋度增加時,地表徑流量呈現明顯的減小趨勢,而地下徑流則隨植被覆蓋增加而增加,一定時期內河流的總徑流量會呈現減小趨勢;而侵蝕產沙指數則隨著地表植被覆蓋度的增加呈更劇烈的減少。
除水土保持措施發揮的生態效應外,疊加上近20多年來社會經濟發生的巨大變化,如鄉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和農村能源從薪柴轉變為煤炭等因素,曾經的薪柴砍伐和坡地耕種等人類活動大量減少,這些都使植被覆蓋發生明顯好轉。此外,黃土高原地區在過去30多年間的年降水量也呈現不顯著的降低趨勢,對該區域產流和產沙的減少也有一定影響。
對于未來黃河中游地區的水沙情勢,我們可以參考Kuczera曲線進行簡單分析預測。生態水文學家Kuczera曾以1939年澳大利亞森林大火后墨爾本附近8個小流域為例,分析了徑流對植被恢復過程的響應,發現桉樹再生25~30年時流域產水量減少50%左右,約在40年后達到最小徑流量,之后產水量才緩慢恢復到火災前水平,這個時間跨度長達80~100年。這是生態水文學中一個著名的關于植被生長發育影響流域產流量的例子。該觀測流域火災前的平均徑流深是883毫米,屬于濕潤氣候條件,而黃土高原地區的徑流深均低于200毫米,屬半干旱到半濕潤氣候區,植被生長緩慢。據此推測,這種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水土保持工程和2000年前后開始的退耕還林還草工程,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達到植被的最大生物量。因此,隨著植被的進一步恢復生長,至少在未來10~20年內,黃土高原的產流量和產沙量仍會繼續減小。

保德縣佃則梁村(1984—2010)

綏德縣韭園溝(1984—2010)
(航拍照片來自:董保華、殷鶴仙、廖義偉、劉曉燕)
根據上述分析可見,中游地區整體上植被明顯好轉,面源侵蝕大幅度減輕,重力侵蝕也在減弱,徑流量和產沙量在近期一段時間仍會大概率地繼續減少。這些變化一方面會使下游水資源量減少,影響到豫魯兩省的社會經濟用水,造成下游引黃灌區農業用水的緊缺,可能會對國家糧食安全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河流輸沙量進一步下降,入海泥沙量減少,對三角洲和河口地區的生態將造成負面影響,并且將使下游河床進一步被沖刷侵蝕,增加下游引黃灌區的取水成本。
三、黃河上游灌區的節水和水鹽平衡問題
在中游產水減少的大背景下,通過上游灌區節水來增加流域可利用水資源量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途徑。黃河上游地區除青海的一些小型灌區外,主要有寧夏灌區和河套灌區,按照“八七”分水方案,目前寧夏每年的用水指標為40億立方米,內蒙古的用水指標為58.6億立方米,均為凈耗用水量。兩個區的農業灌溉均占總用水量的80%以上,灌溉定額大,具有較大的節水潛力。然而,由于節水灌溉技術和信息化管理尚不完備,節水和排鹽缺乏科學有效的技術手段和管理途徑,目前該區域農業節水潛力的進一步挖掘面臨較大困難。
以河套灌區為例,該灌區地處半干旱與干旱區交接地帶,年降水量僅186厘米,若無灌溉將是一派荒漠景象。由于黃河水的及時灌溉,目前該灌區已是我國第三大灌區,成為我國西部地區最大的綠洲之一,農作物總播種面積超過1000萬畝,以種植食葵、小麥和玉米為主。河套灌區從磴口縣的三盛公水利樞紐取水,通過幾條干渠進入農田,灌區排水經北部的總排渠匯入烏梁素海,經過濕地的凈化后排入黃河。
河套灌區的節水需要整體考慮節水與生態的問題,主要是水鹽平衡問題。1997年黃河下游發生最長時間和最長河段的斷流后,自1998年實行黃河水量統一調度,嚴格執行“八七”分水方案。河套灌區實施了一系列節水改造措施,包括干渠和支渠的渠道襯砌、水價改革、水權轉換等,取得了較好的節水效果。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從1986年的0.305提高到2012年的0.409;與此同時,高耗水的小麥種植面積從1997年的379萬畝縮減到2013年的63萬畝,葵花和玉米的種植面積大幅增加;通過渠道改造和種植結構調整,河套灌區的單位面積灌溉量從1990年代末的每公頃11000立方米下降到目前的約7000余立方米。但另一方面,河套灌區的灌溉面積也伴隨著節水的提升快速增加,因此,灌區總的引水量并未明顯減少。
伴隨節水而來的是鹽分累積問題,這也成為灌區可持續發展的一大隱憂。目前,灌區年引黃水量為50億立方米,按照取水口的平均鹽分含量每升0.5 克計算,每年輸入灌區的鹽分為250萬噸;年均排水量3億立方米,排水平均鹽度每升4.0克,則年排入烏梁素海的鹽分總量為120萬噸,因此,每年約有130萬噸的鹽分累積在灌區內。這些鹽分或儲存在灌區的深層土壤、地下水中,或富集在區內微地形較高的荒丘地帶,對灌區土壤生產力的可持續性和生態安全造成極大威脅。究其根源,在于對灌區水循環和水鹽平衡缺乏整體認識,對生態系統響應節水的機理認識不足,對農業-水-生態的協同發展和優化管理缺乏系統管理等。
四、黃河流域水資源可持續利用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對策建議
針對以上分析和認識,對黃河流域水資源可持續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提出如下幾條建議:
1.面對流域整體缺水形勢和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需求,應將節水優先作為流域水土資源綜合治理的最基本原則。流域的生態保護與可持續發展需從全局和長遠出發,考慮不同區段的水生態功能和生產功能,合理制定水管理政策。如源流區借助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契機,將區內牧民進行異地搬遷安置,降低三江源區的畜牧業生產功能,僅保留少量的畜牧業以維護當地的傳統文化和畜牧業景觀,使該區域的生態植被盡快恢復,發揮高原水塔的生態功能;上游灌區進一步大力推行節水農業,考慮水、沙、鹽的變化規律,采取跨季節和年際的綜合調控,生長季采取工程和農藝的節水技術大力節水,非生長季,充分發揮好秋灌的生態作用,進行灌區洗鹽,以維持灌區水鹽平衡和可持續的生產力。
2.對于中游地區,黃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和生態治理需要考慮其長期效應。黃土高原目前的植被情況總體上是好轉的,根據生態水文學原理的預測,短期(10~20年)內產水量和產沙量仍會進一步減少。一方面,應充分研究論證,評估水沙雙減對黃河下游及河口地區的綜合影響,合理制定應對策略;另一方面,中游黃土溝壑區建設的大量淤地壩因農村青壯勞動力的外遷,大多疏于管理,應建立管理和維護機制,以防范在極端降雨時發生垮塌和大面積土沙流出的風險。
3.應盡快改革流域水量分配制度,探索動態的分水協商機制,建立科學的生態補償和水權轉讓制度,實現全流域水資源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最大化。
4.綜合來看,目前對黃河流域水沙和水鹽問題的認識仍有局限性,支撐重大政策的科學和理論依據不足,尤其是在涉及一些長期效應的預測方面缺乏科學的數據支撐。建議國家加大對黃河流域水-沙-鹽傳輸轉化規律和水文-農業-生態協同發展理論方面的科學研究投入,提升對流域水沙關系、水沙與河道和河口生態安全的關系、灌區節水-生產力-水鹽平衡等關系的科學認識,為更科學合理地進行流域綜合管理和實現生態文明發展路徑提供理論保證。
(致謝:黃河水利委員會劉曉燕副總工,內蒙古農業大學張圣微、屈振江、史海濱教授,中科院地理所李發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