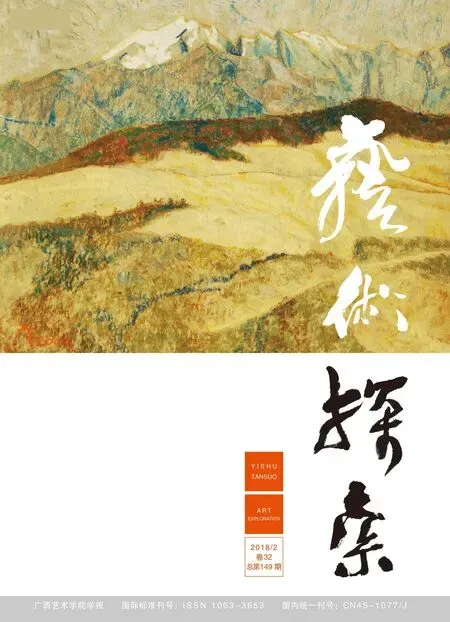圖畫與觀念
——關(guān)于邁克爾·巴克森德爾《意圖的模式》的幾個問題
戴 丹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 美術(shù)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0013)
邁克爾·巴克森德爾(Michael Baxandall,1933~2008年,圖1)被譽為20世紀(jì)最偉大的藝術(shù)史家之一。他的研究呈現(xiàn)出跨學(xué)科性,突破了藝術(shù)家傳記、形式分析、圖像學(xué)以及德語國家藝術(shù)史研究方法的傳統(tǒng),創(chuàng)造性地以語言學(xué)為工具,用情境分析法來研究文藝復(fù)興時期的公眾智性活動與繪畫風(fēng)格之間的關(guān)系,因此巴克森德爾有時候被歸為“傳統(tǒng)藝術(shù)史派”,有時候又被歸為“新藝術(shù)史派”。他的研究不僅在藝術(shù)史領(lǐng)域,還在社會學(xué)、視覺神經(jīng)生理學(xué)等其他領(lǐng)域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
巴克森德爾1933年生于英國威爾士的加的夫城(Cardiff),早年在劍橋大學(xué)追隨著名文學(xué)評論家利維斯(F.R.Leavis,1895~1978年)學(xué)習(xí)英語文學(xué),這段學(xué)習(xí)經(jīng)歷對他以后的藝術(shù)史研究方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1955年到意大利帕維亞大學(xué)學(xué)習(xí)藝術(shù)史,之后前往德國慕尼黑大學(xué),選修了新維也納藝術(shù)史學(xué)派代表人物漢斯·澤德爾邁爾(Hans Sedlmayr,1896~1984年)的“結(jié)構(gòu)分析法”課程。1958年返回倫敦,進(jìn)入瓦爾堡研究院的圖像部工作。1961年進(jìn)入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的建筑與雕塑部工作。1965年又回到瓦爾堡研究院,擔(dān)任文藝復(fù)興研究講師,之后接替貢布里希(E.H.Gombrich,1909~2001年)擔(dān)任古典傳統(tǒng)史教授。1974年起擔(dān)任牛津大學(xué)斯萊德美術(shù)講座教授。1980年以后受邀到美國學(xué)界開展教學(xué)活動,擔(dān)任康奈爾大學(xué)和加州大學(xué)伯克利分校的藝術(shù)史教授。1991年當(dāng)選為美國藝術(shù)和科學(xué)研究院院士。
巴克森德爾于1985年發(fā)表的專著《意圖的模式》[1](圖2)是關(guān)于藝術(shù)史研究方法的經(jīng)典之作,該書一經(jīng)出版立即成為西方各個大學(xué)藝術(shù)史學(xué)科的必讀書目。瑪格麗特·伊弗森(Margaret Iversen)曾指出,巴克森德爾的每一本著作在方法論層面都極富創(chuàng)新性,對藝術(shù)史學(xué)科貢獻(xiàn)巨大,而《意圖的模式》是第一本專門圍繞藝術(shù)史研究方法展開討論的專著。[2]71
一、藝術(shù)史界的一場討論
20世紀(jì)70年代初,歐美藝術(shù)史界出現(xiàn)了一種奇怪的現(xiàn)象,許多藝術(shù)史家自責(zé)藝術(shù)史研究“理論不完備”,這引發(fā)了一系列針對藝術(shù)史理論和方法論的討論。美國《新文學(xué)史》(New Literary History)雜志于1972年第3卷第3期設(shè)立“文學(xué)與藝術(shù)史”專題,為這場討論提供了一個公共平臺。巴克森德爾于1979年在該雜志發(fā)表論文《藝術(shù)史的語言》[3]453-465,對這場持續(xù)了將近10年的討論作了回應(yīng)。其后,巴克森德爾又對該論文進(jìn)行了修改和進(jìn)一步擴展,他于1982年4月在加州大學(xué)伯克利分校舉辦的尤娜人文學(xué)科系列講座(Una’s Lectures)上所做的演講便是由這篇論文發(fā)展而來,該講稿后經(jīng)修訂于1985年以專著形式出版,書名為《意圖的模式》。

圖1 邁克爾·巴克森德爾教授(1933~2008年),1989年11月,攝影:Max Whitaker
這場討論出現(xiàn)了三種代表性觀點。第一種觀點來自于庫爾特·福斯特(Kurt W.Forster),他指出當(dāng)時藝術(shù)史家每天的工作都圍繞以下三個基本方面進(jìn)行:風(fēng)格史(形式分析)、藝術(shù)家傳記和圖像學(xué)。[4]459-470風(fēng)格、傳記研究需要大量的比較,然而關(guān)于風(fēng)格與風(fēng)格、藝術(shù)家與藝術(shù)家之間的比較,容易產(chǎn)生無休止、無結(jié)果的爭論。學(xué)界通常假設(shè)形式分析法或風(fēng)格史研究應(yīng)該擺脫價值偏向和歷史哲學(xué),然而福斯特認(rèn)為風(fēng)格史研究實際并不能擺脫這兩方面。所有的風(fēng)格理論都利用一種發(fā)展的模式或者通過一種純粹的形式模式變化取代歷史爭論。事實上,風(fēng)格特征通常都會帶有社會因素,如果風(fēng)格特征變成一系列被無休止地描述而非被解釋的材料時,立即就成了純粹的美學(xué)現(xiàn)象。藝術(shù)家接受訓(xùn)練,藝術(shù)家作坊的內(nèi)部組織以及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技術(shù)過程,這些都使得一種藝術(shù)與其他藝術(shù),與藝術(shù)品的社會組織以及創(chuàng)作條件建立了關(guān)系。福斯特對形式分析法進(jìn)行了批評,他認(rèn)為藝術(shù)不能脫離歷史,藝術(shù)品的普遍意義應(yīng)該存在于歷史之中,一旦將藝術(shù)與社會政治脫離,勢必會阻礙批判性的思考以及對藝術(shù)的理解。福斯特特別指出,博物館中展示的藝術(shù)品處于一種與歷史隔絕、價值中立和無意義的空間狀態(tài)中。
福斯特認(rèn)為藝術(shù)史受到了觀念史的同化,以及以犧牲電影和招貼畫這些次要藝術(shù)類型為代價而集中于研究高雅藝術(shù),在他看來這些次要藝術(shù)比那些大師名作更能反映社會情境。他還指出,藝術(shù)史家對自己的先入之見及其社會根源并未察覺,也尚未探索出一種真正的社會歷史研究方法。充分理解古代藝術(shù)品的唯一手段是一種雙重批判,一方面是對維系著藝術(shù)品的創(chuàng)造和使用的思想體系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對當(dāng)前將藝術(shù)品轉(zhuǎn)變?yōu)橐环N消費權(quán)力等級和說教物品的文化興趣的批判。在他看來,藝術(shù)史作為一門學(xué)術(shù)學(xué)科在過去幾十年所獲得的相對獨立性正逐漸轉(zhuǎn)變?yōu)樽陨戆l(fā)展的限制因素。
第二種觀點來自于詹姆斯·阿克曼(James S.Ackerman),他指出,藝術(shù)史學(xué)科給人一種虛假的成熟印象———通過對風(fēng)格進(jìn)化模式的分析展現(xiàn)藝術(shù)品的歷史連續(xù)性以及通過圖像學(xué)分析展現(xiàn)象征圖像的演變。[5]315-330盡管諸如手法主義、巴洛克等風(fēng)格類型以及那些古代象征圖像的演變特征,對于文學(xué)史家、音樂史家的研究都有所幫助,但是藝術(shù)史學(xué)科在過去一段時間內(nèi)并未出現(xiàn)其他的研究方法。與文學(xué)研究一樣,藝術(shù)史家更偏愛作歷史文獻(xiàn)研究而非批評,其中一個原因是藝術(shù)史家研究的對象是物質(zhì)性的藝術(shù)品而非語言性的文本,將物質(zhì)性的藝術(shù)品轉(zhuǎn)化為語詞難度更大且容易出問題。
阿克曼認(rèn)為藝術(shù)史學(xué)科問題的根源存在于一種混雜的哲學(xué)基礎(chǔ)中,藝術(shù)史家甚至無法去運用一些哲學(xué)觀念,當(dāng)時美國大部分藝術(shù)史家和批評家的哲學(xué)知識都比較欠缺。藝術(shù)史家把他們的研究方法建立在19世紀(jì)源于科學(xué)經(jīng)驗主義的實證主義傳統(tǒng)之上。實證主義可以為在一種科學(xué)文化中的藝術(shù)研究提供理論根據(jù),盡管所有的努力都是要獲得一種客觀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體系要求否定和回避文化價值和個人價值,但是藝術(shù)品恰恰又包含了這些價值。沒有價值判斷,藝術(shù)研究就不可能展開。在選定一個研究對象之前,必須要確定該對象是否值得研究,而這個確定過程又是與事前描述和理解該對象相關(guān)聯(lián)的。這些判斷都是至關(guān)重要的,藝術(shù)史家決定研究這位畫家而非另一位畫家,實際上已經(jīng)在即將展開的批評或歷史解釋中帶入了最基本和最有意義的思維活動,將普遍的自然觀念和藝術(shù)功能運用到其所要研究的對象之中。藝術(shù)史家并非隨意地挑選研究對象,選擇哪個研究對象實際已經(jīng)暗示了藝術(shù)史家對藝術(shù)價值所做的劃分和價值取向。價值并非為藝術(shù)史家所使用,而是由藝術(shù)品本身以某些方式傳達(dá)出來。不同于科學(xué)領(lǐng)域,藝術(shù)領(lǐng)域的客觀性是一個模糊的標(biāo)準(zhǔn),如果在藝術(shù)領(lǐng)域使用一些科學(xué)領(lǐng)域中的客觀陳述的話,就無法理解過去的一件藝術(shù)品及其情境,藝術(shù)史家必須把對該藝術(shù)作品的了解與自身經(jīng)驗以及同時代人的經(jīng)驗相聯(lián)系。
在阿克曼看來,藝術(shù)史家已經(jīng)荒誕地把文藝復(fù)興時期的新柏拉圖主義理論遺留下來的一種無意識價值體系帶入了其中。拒絕公開、批判地處理價值問題,導(dǎo)致藝術(shù)史家在形式與內(nèi)容、社會的與美學(xué)的、歷史與批評之間難以抉擇。在啟蒙運動及其產(chǎn)生的社會革命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藝術(shù)史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是基于基督教和新柏拉圖思想的先驗價值的,即將藝術(shù)置于一個脫離人類日常生活的抽象領(lǐng)域內(nèi)。在藝術(shù)史領(lǐng)域,形式與內(nèi)容的隔離導(dǎo)致了學(xué)科的專門化,出現(xiàn)了通過判斷一件特殊藝術(shù)品的形式風(fēng)格特征來斷定其出現(xiàn)時間的鑒定學(xué),以及解釋藝術(shù)品中象征圖像的性質(zhì)、起源的圖像學(xué),在阿克曼看來,只有將這兩者有效地結(jié)合起來才能形成卓越的研究。
阿克曼指出,藝術(shù)史家應(yīng)該摒棄將構(gòu)成我們基本價值的傳統(tǒng)進(jìn)行非理性拼貼的做法,而使用與自己的實際思考相對應(yīng)的自覺清晰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在解釋過程中恢復(fù)歷史與批評話語以及形式與內(nèi)容之間的平衡。可以根據(jù)一些所謂“人文價值的觀念”去評估藝術(shù),“人文價值的觀念”不能直接用來判斷藝術(shù)品的價值,因為在當(dāng)今社會,這些藝術(shù)品的價值是基于社會的習(xí)俗、實踐,并非基于一種結(jié)構(gòu)清晰的神學(xué)或哲學(xué)體系而產(chǎn)生的。藝術(shù)史家的評判體系原則上是一種開放的價值體系,其作用是在傳統(tǒng)理想標(biāo)準(zhǔn)與進(jìn)步的社會實踐之間作調(diào)節(jié),因此評判藝術(shù)品的價值是在傳統(tǒng)的自然概念、藝術(shù)意圖和當(dāng)代的藝術(shù)實踐之間作調(diào)節(jié)。

圖2 《意圖的模式》封面
第三種觀點來自戴維·羅森德(David Rosand),他一直在思考如何以現(xiàn)有的眼光去看待過去的藝術(shù)這個問題。[6]現(xiàn)有的價值影響著從事古代藝術(shù)研究的藝術(shù)史家,但在當(dāng)時存在著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即藝術(shù)史與藝術(shù)批評兩個領(lǐng)域之間幾乎沒有任何交流互動。藝術(shù)史和藝術(shù)批評關(guān)注兩個完全不同的領(lǐng)域,前者公正客觀,后者主觀且略帶偏見,兩者邊界分明,互不相干。然而藝術(shù)史家和藝術(shù)批評家共享一個標(biāo)準(zhǔn),即都根據(jù)歷史標(biāo)準(zhǔn)衡量藝術(shù)的價值,歷史成為了衡量藝術(shù)品美學(xué)意義和藝術(shù)功能的根本手段。藝術(shù)品可以是被欣賞和被闡釋的對象,如果放在社會語境中,可以被視為其制作者對某個觀點的表達(dá)或者對公眾的一個反應(yīng),但是,不論是形式評論還是社會評論,藝術(shù)都是通過歷史而產(chǎn)生意義的。
羅森德對形式分析、圖像學(xué)解釋等傳統(tǒng)藝術(shù)史研究方法進(jìn)行了批判,他認(rèn)為這些方法只注重研究諸如文化習(xí)俗、社會情境這些藝術(shù)品的外部因素,并不能真正研究藝術(shù)品內(nèi)在固有的交流機能和視覺機能。他認(rèn)為只有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1904~2007年)和貢布里希的研究最接近藝術(shù)品的內(nèi)部機能,兩人引入了知覺心理學(xué)方法,但這似乎又會轉(zhuǎn)移讀者的注意力,使他們不把藝術(shù)品作為一個整體的表達(dá)結(jié)構(gòu)。①Rudolf Arnheim,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4;E.H.Gombrich,Art and Illusion,New York:Phaidon Press,1960.
藝術(shù)史研究經(jīng)常會在形式與內(nèi)容、風(fēng)格史與圖像學(xué)之間作區(qū)分,其實這樣的區(qū)分顯然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形式與內(nèi)容都存在于風(fēng)格規(guī)律之中。羅森德引入了文學(xué)批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模式。他指出“模式”概念也適用于視覺藝術(shù),它的有效性不僅能夠提供一種區(qū)分形式習(xí)慣與表達(dá)習(xí)慣的方法,對于觀者而言是文化假設(shè)與期待之間的區(qū)分,而且更加精確地闡述了藝術(shù)品本身的存在情境,即圖像的意圖以及實現(xiàn)這些意圖的方式。將“模式”概念引入到藝術(shù)批評中,能夠避免形式—內(nèi)容這個過于簡單化的二元對立。根據(jù)“模式”概念,一幅圖像既不僅是其表面所展現(xiàn)的內(nèi)容,也不僅是其象征的內(nèi)容,而是既有表面展現(xiàn)的內(nèi)容又有背后隱含的某種意義。
除此之外,羅森德指出藝術(shù)史家還要掌握閱讀圖像的能力。圖像跟語言一樣,有其自身的語詞、語法和句法結(jié)構(gòu),一幅圖像的意義,本質(zhì)上存在于圖像結(jié)構(gòu)中,至少是由結(jié)構(gòu)來傳達(dá)。研究藝術(shù)不僅僅依靠外在的觀看,更需要閱讀圖像本身的結(jié)構(gòu),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圖像的形式及其背后的意義。
二、藝術(shù)史的語言
巴克森德爾于1979年在《新文學(xué)》雜志第10卷第3期發(fā)表了《藝術(shù)史的語言》一文,針對這場持續(xù)了將近10年的討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巴克森德爾開篇即表明自己不想加入這場討論,反對某些藝術(shù)史家專斷式的言論,他認(rèn)為需要存在各種各樣不同類型的藝術(shù)史家,而不是只推崇某個學(xué)派或者某種方法論。當(dāng)出現(xiàn)某些藝術(shù)史家告誡其他藝術(shù)史家應(yīng)該如何去做的時候,那些告誡正表明了前者當(dāng)時的學(xué)術(shù)興趣。在他看來,這場討論之所以持續(xù)時間如此之久,爭論如此激烈,主要歸因于藝術(shù)史家對于什么是“理論”存在著一些誤解。[3]454
巴克森德爾指出,從起源來看,藝術(shù)史不像文學(xué)批評那樣有著深厚古老的根基,藝術(shù)史家從一開始就處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對于藝術(shù)史學(xué)科,巴克森德爾最擔(dān)心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將語言和藝術(shù)品的視覺特征進(jìn)行匹配;二是如何闡釋藝術(shù)品的視覺特征與其歷史情境之間的關(guān)系。[3]455
視覺性是視覺藝術(shù)的特性。藝術(shù)史家特有的才能之一便是尋找和使用語詞描述藝術(shù)品的形狀、色彩和結(jié)構(gòu)等特征。語詞的直接描述功能是有限的,無法涵蓋藝術(shù)品所有的視覺特征。當(dāng)人們?nèi)ソ忉屢环鶊D畫時,其實并非是在解釋圖畫本身,而是在對關(guān)于這幅圖畫的相關(guān)評論作解釋,從某種程度而言,只有把圖畫放在語詞描述或詳述之中,思考之后才能對其作出解釋。[1]1巴克森德爾例舉了公元4世紀(jì)時古希臘人利本紐斯(Libanius,314~394年)對安條克(Antioch)議會廳內(nèi)的一幅畫所作的一段描述,[1]2這種描述方法便是古希臘修辭中經(jīng)常使用的藝格敷詞(Ekphrasis)。利本紐斯試圖通過語詞詳盡描述畫面中的內(nèi)容,以期讓那些并未見過此畫的聽眾能夠在頭腦中再現(xiàn)畫面內(nèi)容。然而實際情況是,盡管他對畫面作了詳細(xì)描述,聽眾仍舊無法根據(jù)他的描述再現(xiàn)和重構(gòu)這幅圖畫。由于語詞無法精確地表達(dá)色調(diào)、空間、比例以及其他的視覺特征,語言實際上并不能完備地去表述一幅特殊的圖畫,語言只是一種概括歸納性的工具。[1]2
藝術(shù)史家使用的語詞與其說是描述性的,不如說是指示性的。語詞在觀者和視覺藝術(shù)品之間起著指示引導(dǎo)作用,藝術(shù)史家使用語詞引導(dǎo)觀者通過語詞與可見客體之間的一種相互指涉來對經(jīng)驗進(jìn)行細(xì)致、精確的分類。藝術(shù)史家通過語詞引導(dǎo)觀者進(jìn)行觀看,存在著一個前提條件,即觀者對藝術(shù)史家使用的語詞以及被描述的視覺藝術(shù)品有一定的經(jīng)驗認(rèn)知。在對圖畫的視覺特征進(jìn)行直接描述方面,語言的描述能力是相對有限的,然而語言具有指示作用,能引導(dǎo)觀者將圖畫的某些被描述的視覺特征與其自身經(jīng)驗世界或記憶中相類似的其他視覺藝術(shù)品或視覺特征進(jìn)行匹配和比較。換言之,語詞始終在引導(dǎo)著觀者觀看視覺藝術(shù)品并且使其想到其經(jīng)驗世界中與之相關(guān)的信息內(nèi)容。然而每一位觀者的經(jīng)驗領(lǐng)域、認(rèn)知水平、智性世界等各方面都存在著差異,因此根據(jù)一段相同的語詞描述而在各自頭腦中重構(gòu)再現(xiàn)所得的圖畫也會存在差異,這也是利本紐斯的美好愿望落空的主要原因之一。
針對《新文學(xué)史》雜志1972年第3卷第3期設(shè)立的“文學(xué)與藝術(shù)史”專題,巴克森德爾提出,文學(xué)批評是語詞描述語詞,而藝術(shù)史是語詞描述圖像。語詞在一種線性過程中發(fā)展。文學(xué)作品都是語言線性發(fā)展的事物,通常都包含了開頭、發(fā)展和結(jié)尾這樣的過程。然而觀者在觀看一幅繪畫的過程中并不存在這種內(nèi)在的線性發(fā)展過程,觀者并非有規(guī)律地、線性地觀看繪畫作品。一開始觀者先對畫面整體產(chǎn)生一個印象,接著是觀看細(xì)節(jié),注意畫面中的關(guān)系、次序等等,再通過連續(xù)掃視觀看整幅圖畫。觀者的掃視并非簡單的觀看,而是在這個過程中運用了自身的思維,而思維的運用又是建立在語詞、觀念基礎(chǔ)上的。觀看一幅圖畫的過程完全不同于利本紐斯用語詞描述圖畫的過程,觀者掃視畫面的順序同時受到了日常觀看習(xí)慣和畫面中特殊細(xì)節(jié)提示的影響,不能像利本紐斯那樣通過語言的線性發(fā)展控制觀看過程。語詞的線性描述無法與觀看過程在時間維度上進(jìn)行匹配,語詞與文學(xué)文本的發(fā)展可以進(jìn)行匹配:閱讀文本就是一種前進(jìn)發(fā)展的過程,而觀看繪畫是圍繞畫面某些區(qū)域快速跳躍式觀看的過程。[3]459-460語詞描述圖畫,并非是對圖畫本身作了描述和再現(xiàn),更確切地說,是描述和再現(xiàn)了觀者觀看圖畫之后的思維活動。[1]5
由于語詞的直接描述能力相對有限,而且觀畫之后的思維活動都是間接性的,巴克森德爾指出在藝術(shù)史研究中應(yīng)該使用間接性的語詞。他提出了三種間接性語詞:第一種通過隱喻的方法對藝術(shù)品的視覺特征進(jìn)行描述;第二種是對藝術(shù)品產(chǎn)生的原因和情境因素進(jìn)行描述;第三種是對觀者的反應(yīng)進(jìn)行描述。可以把這三種語詞分別稱為:比較的或隱喻的語詞,即比喻詞;原因的或推理的語詞,即原因詞;主體的或自我的語詞,即效果詞。[3]457在藝術(shù)史和藝術(shù)批評中,指示的準(zhǔn)確性主要依靠原因詞;效果詞在形式和本質(zhì)上都是被動的,表示了藝術(shù)品對觀者產(chǎn)生作用的結(jié)果;原因詞在推理行動中起作用,同時,原因詞使得觀者進(jìn)入推理行動中,進(jìn)入重構(gòu)和評估語詞暗示模式的行動中。這三種間接性語詞與圖畫、藝術(shù)家和觀者的關(guān)系如圖3所示。①巴克森德爾在《藝術(shù)史的語言》和《意圖的模式》中分別用兩張圖表來表示間接性語詞與圖畫、藝術(shù)家和觀者之間的關(guān)系,參見:Michael Bax and all,“The Language of Art History”,New Literary History,Vol.10,No.3,Anniversary Issue:I.(Spring,1979),p.458;Michael Bax and all,Patterns of Intention:On the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f Pictures,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p.6.

圖3
圖畫對人所產(chǎn)生的效果,其實是人對圖畫所進(jìn)行的思考、討論等一系列活動的產(chǎn)物。當(dāng)我們試圖對一幅圖畫進(jìn)行歷史解釋時,實際所要做的便是試圖發(fā)展這種思想。[1]6這三種間接性語詞似乎與思考一幅圖畫的三種思維模式是相對應(yīng)的,圖畫不僅僅是一個自然物質(zhì)客體,它還包含了畫家的創(chuàng)作過程以及觀者的接受、反應(yīng)過程。
在藝術(shù)史研究中,藝術(shù)史家并非孤立地使用語詞,而是與描述對象聯(lián)系起來并用。對于這些語詞而言,關(guān)鍵是描述對象必須是可見的或現(xiàn)存的,只有面對實物,語詞才能發(fā)揮最大的作用。如果描述對象是不可見的或者不存在的,那么藝術(shù)史家利用語詞進(jìn)行的描述,對于讀者而言并不能達(dá)到預(yù)期的效果,讀者在其自身的經(jīng)驗世界中并不能找到相關(guān)的信息與語詞描述進(jìn)行匹配,因此語詞無論在描述還是在解釋方面都是無力的。巴克森德爾指出,藝術(shù)史在最近五百年內(nèi)發(fā)生了巨大變化,16世紀(jì)瓦薩里的著作描述的都是不可見的視覺藝術(shù)品,而這些視覺藝術(shù)品在讀者的經(jīng)驗世界中并未存在過,因此讀者無法很好地理解瓦薩里的解釋。18世紀(jì),萊辛對拉奧孔群像進(jìn)行了描述。讀者對這件藝術(shù)品并不陌生,至少都見過拉奧孔群像的復(fù)制品,因此能夠很好地理解萊辛的論述。19世紀(jì)的書籍,有了版畫作插圖。再發(fā)展到后來,從沃爾夫林開始,他在演講中甚至開始使用黑白投影儀。[1]8-9只有通過圖像的使用,藝術(shù)史家的文字闡釋才能更好地被觀者理解。
三、視覺觀念與圖畫風(fēng)格
任何一件視覺藝術(shù)品并不僅僅是自然物質(zhì)客體,而是存在于由人類語言建構(gòu)的世界中,因此當(dāng)藝術(shù)史家試圖用語詞去描述一幅圖畫時,語詞并非指向圖畫本身,而是指向圖畫對觀者引起的效果和反應(yīng),語詞并不能精確表述圖畫的視覺特征,只能引起觀者的經(jīng)驗聯(lián)想。實際上,語詞既不能再現(xiàn)圖畫本身又不能再現(xiàn)觀看過程,而是再現(xiàn)了觀者觀看圖畫之后的思維過程。換言之,藝術(shù)史家面對的是圖畫與觀念之間的關(guān)系。
在上文已經(jīng)談到,巴克森德爾對藝術(shù)史學(xué)科存在著兩個方面的擔(dān)憂,這兩個方面是彼此相關(guān)而非孤立的,從某種程度而言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這個問題便是圖畫與觀念的問題。更確切地說,巴克森德爾試圖探索圖畫的視覺特征與其所處文化中由語言建構(gòu)的智性系統(tǒng)之間的關(guān)系。
智性系統(tǒng)包括一系列事物,藝術(shù)也在內(nèi),畫家創(chuàng)作繪畫作品的行為并不一定不如哲學(xué)家或科學(xué)家的思想。一幅圖畫中思想的表達(dá)更像一個過程,即在以圖畫為媒介進(jìn)行的創(chuàng)作活動中,關(guān)注和解決某個圖畫問題的過程。由于畫家并未在概念層面上對圖畫進(jìn)行標(biāo)注,因此沒有必要把一種繪畫風(fēng)格與哲學(xué)或科學(xué)中概念化的事物聯(lián)系起來。[1]75
在巴克森德爾看來,探索圖畫與觀念的關(guān)系,存在著兩個理由。第一,畫家生活在由觀念系統(tǒng)建構(gòu)的文化中。畫家對某個特定繪畫問題進(jìn)行思考,實際上是在用特定的觀念進(jìn)行思考,觀念對于繪畫創(chuàng)作影響很大。第二,藝術(shù)史家非常關(guān)注繪畫形式與思想形式之間的關(guān)系。這背后的根源相當(dāng)復(fù)雜,即把人類文化和人類思想視為一個整體,承認(rèn)畫家的智性思維是嚴(yán)謹(jǐn)?shù)模牙L畫置于由人類的語詞和觀念建構(gòu)的領(lǐng)域內(nèi)。[1]75
為了探索圖畫與觀念之間的關(guān)系,巴克森德爾把研究對象聚焦在了18世紀(jì)法國畫家讓-巴蒂斯特-西蒙-夏爾丹(Jean-Baptiste-Siméon Chardin,1699~1779年)的繪畫作品與當(dāng)時法國社會中普遍盛行的經(jīng)驗主義觀念、視覺理論之間的關(guān)系上。
夏爾丹創(chuàng)作于1735年的《飲茶的婦女》(圖4)中,畫面的某些局部被畫得特別清晰而某些局部比較模糊,比如茶壺、手和手臂這個平面就特別清晰,除此之外還有特殊的明暗處理。這些視覺特征并非僅僅反映夏爾丹的個人風(fēng)格特征和藝術(shù)手法那么簡單,在巴克森德爾看來,這背后隱含了畫家的某些特殊意圖以及當(dāng)時整個法國社會大眾的智性系統(tǒng)和觀念活動。
盡管當(dāng)時像丹尼斯·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年)這樣的藝術(shù)批評家為夏爾丹的繪畫作品寫了大量評論文章,試圖探討來自其他領(lǐng)域的思想在夏爾丹繪畫意圖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在巴克森德爾看來,那些沙龍批評家的嘗試都是無益的。巴克森德爾指出,藝術(shù)批評并非是純粹用語詞記錄人們觀看繪畫的活動,藝術(shù)批評更多地是一種文學(xué)體裁,顯然與人們?nèi)绾斡^看繪畫相關(guān),但是受到了文學(xué)化傳統(tǒng)和模式的制約。[1]75藝術(shù)批評過度程式化和規(guī)范化,令人難以接受,18世紀(jì)這批沙龍批評家的評論文章便屬于此類。于是巴克森德爾舍棄了沙龍批評家的評論文章,在18世紀(jì)其他領(lǐng)域內(nèi)與視覺相關(guān)的文獻(xiàn)中尋找夏爾丹作品中局部視覺清晰所隱含的意圖。
夏爾丹繪畫作品局部視覺清晰度的背后所隱藏的是一部智力史的發(fā)展,與18世紀(jì)的視覺科學(xué)、醫(yī)學(xué)等領(lǐng)域的研究緊密相關(guān)。“視覺清晰度”是一個專有術(shù)語,包括視覺調(diào)節(jié)和視覺銳度兩部分內(nèi)容。眼睛為了聚焦于位于不同距離的前景客體而改變自身形狀,這便是視覺調(diào)節(jié),與縱深方向的清晰度相關(guān)。銳度特指視網(wǎng)膜上不同部位感覺反應(yīng)的不同程度,與視野的清晰度相關(guān)。[1]81早在17世紀(jì),已經(jīng)有相關(guān)學(xué)者開始研究視覺調(diào)節(jié),并且搞清楚了與調(diào)節(jié)相關(guān)的眼球的大概結(jié)構(gòu)。在夏爾丹所處的時代,牛頓的學(xué)生詹姆斯·朱林(James Jurin,1684~1750年)是當(dāng)時視覺調(diào)節(jié)研究方面最有影響的權(quán)威專家,他把視覺清晰度分為完全清晰、不清晰和完全模糊三個等級。完全清晰存在一個范圍,超過這個范圍的話,視覺就會進(jìn)入不清晰狀態(tài)。處于不清晰狀態(tài)的物體會感覺偏大,物體中心部分與其余部分相比顯得特別突出,同時會出現(xiàn)半影,并且伴有色偏。

圖4 夏爾丹《飲茶的婦女》,1735年,81cm x 99 cm,現(xiàn)藏于格拉斯哥大學(xué)亨特美術(shù)館
當(dāng)時關(guān)于視覺銳度的研究都基于17世紀(jì)對屈光學(xué)和視網(wǎng)膜結(jié)構(gòu)的研究,這方面的權(quán)威是彼得·坎珀(Pieter Camper,1722~1789年)和塞巴斯蒂安·勒克萊克(Sébastien Le Clerc,1637~1714年)。坎珀總結(jié)了埃德姆·馬略特(Edme Mariotte,1620~1684年)、菲利普·德·拉海爾(Philippe de La Hire,1640~1718年)、威廉·布里格斯(William Briggs,1642~1704年)和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年)等人的視覺理論,提出視網(wǎng)膜中部敏銳的原因是中央凹敏感性和邊緣散光兩個方面。視網(wǎng)膜上的各個部分并不具有相同的敏感性,靠近連接點的視神經(jīng)部位最敏感。正因此,人們在觀看事物時需要轉(zhuǎn)動眼睛以便讓圖像落在這個點上,同樣在繪畫中,只有某些局部應(yīng)該被畫得明亮和清晰。坎珀提出這一論點有一個前提條件,即承認(rèn)繪畫不是再現(xiàn)自然客體而是再現(xiàn)人類對客體的視知覺過程。畫面的局部清晰體現(xiàn)了人類感知自然物是有選擇性的注視行為,被注視的部分是清晰的,未被注視的部分是模糊的。坎珀的博士論文(1746年)在論述人們?nèi)绾斡^看時指出,物色彩、清晰度都隨著人與物距離的增加而遞減。勒克萊克進(jìn)一步提出了觀看過程中的注視行為,即人們在觀看一個范圍較大的事物時,看到的所有局部并非都是清晰的,只能獲得一個大概印象,只有通過注視行為,才能逐一看清某些局部細(xì)節(jié),獲得清晰感。他還為畫家撰寫了實用幾何學(xué)方面的著作,其中描述和圖解了視覺銳度的事實、清晰視覺的中心軸等等。拉海爾指出,不同的光線條件對繪畫的色彩、色調(diào)和明暗關(guān)系都會產(chǎn)生影響,比如在弱光條件下,藍(lán)色會變得更加亮一些。
巴克森德爾正是通過18世紀(jì)法國的朱林、坎珀和勒克萊克等人的視覺理論,解釋了跟他們同處一個時代的夏爾丹的《飲茶的婦女》這幅繪畫作品。依據(jù)這些視覺理論,我們就不難理解畫家在處理畫面時,為何要把某些局部畫得變形,某些局部畫得特別清晰,而其他部分畫得相對模糊。茶壺、手和手臂部分被畫得特別清晰,與當(dāng)時視知覺理論中關(guān)于視覺調(diào)節(jié)與注視行為的觀念相關(guān)。18世紀(jì)的法國,社會大眾對于視覺科學(xué)抱有濃厚興趣,經(jīng)常會談?wù)撓嚓P(guān)話題,當(dāng)時這些視覺科學(xué)家的理論成果和觀念多多少少也影響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像夏爾丹這樣的畫家,繪畫創(chuàng)作便是與視覺打交道,因此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他們必定會考慮當(dāng)時那些最新的視覺理論和觀念。對于當(dāng)時的觀者而言,通過日常生活中學(xué)到的視覺理論和觀念,也能更好地讀解同時代那些畫家繪畫作品中的特殊意圖。
包括夏爾丹在內(nèi)的這批18世紀(jì)法國畫家的繪畫作品,不同于文藝復(fù)興時期畫家利用透視技巧模仿自然的繪畫作品。從某種程度而言,18世紀(jì)的畫家并非是對自然客體作單純地模仿再現(xiàn),而是在再現(xiàn)觀看過程中人的視覺變化產(chǎn)生的視覺效果,因此更具“真實性”。
四、巴克森德爾研究方法的理論來源
巴克森德爾對18世紀(jì)法國視覺理論資料的引用,以及他本人多次提出的通過還原客觀情境的方法來研究處于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中的視覺藝術(shù),從根本而言,是在探討現(xiàn)象絕對論和文化相對論的問題。對于這個話題的探討,更多的來自于20世紀(jì)西方的人類學(xué)和心理學(xué)界。據(jù)巴克森德爾自己的回憶,在20世紀(jì)70年代他經(jīng)常和一批結(jié)構(gòu)人類學(xué)家進(jìn)行討論,他所提出的諸如“時代之眼”“認(rèn)知風(fēng)格”等觀念均受到當(dāng)時人類學(xué)研究成果的啟發(fā),其中美國人類學(xué)家梅爾維爾·赫斯科維茲(Melville J.Herskovits,1895~1963年)對他的影響最大。[7]8
現(xiàn)象絕對論是指一種普遍存在以及易引起誤解的幼稚的意識經(jīng)驗(conscious experience),即認(rèn)為世界正如其所呈現(xiàn)的那樣。正常的觀者天真地假定世界正如他們所看到的那樣,不加批判地接受感知到的現(xiàn)象,不承認(rèn)其視知覺受到間接的推理體系調(diào)節(jié),假設(shè)視覺現(xiàn)象是直接地、即刻地、不經(jīng)調(diào)節(jié)地獲得的,我們把這種觀點稱為現(xiàn)象絕對論(Phenomenal Absolutism)。[8]4-5現(xiàn)象絕對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觀者假設(shè)其他所有觀者都像他本人那樣感知周圍環(huán)境狀況,如果產(chǎn)生不同的反應(yīng)是由于不合常理的任性而非不同的感知內(nèi)容所致。
柏拉圖在《理想國》第七卷《論影子和真實》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9]230-233
在一個地下洞穴內(nèi)住著一群人,有一條長長的且與洞穴等寬的通道通向外界,光線沿著通道可以照進(jìn)洞內(nèi)。那群人從小就住在里面,他們的雙腿和脖子都被鐵鏈鎖著,因此無法動彈也無法轉(zhuǎn)頭環(huán)顧四周,只能向前看洞穴的后壁。在那群人背后遠(yuǎn)處高些的地方燃燒著一團火,在火光和這群被囚禁的人之間有一條凸起的路。沿著這條路筑有一堵矮墻,這墻就像牽線木偶戲演員面前的一個屏障,他們把木偶舉到屏障上進(jìn)行表演。
一些人舉著各種器皿以及用木頭、石頭和各種材料制作的假人假獸沿著那堵墻走……洞穴內(nèi)的那些人除了能看到因為火光而投射到洞穴后壁上的影子外無法看到其他的事物……如果那些人能彼此交流,他們必定認(rèn)為他們所看到的影子就是真實的事物……對于這些人而言,真實無非就是那些影子。
假設(shè)有一天其中一個人被松了綁,被迫立即站起來環(huán)視四周,看著那堆火并向著那個方向走過去,他將感到非常痛苦,并且由于眼花繚亂而無法看清那些原本只能看見其影子的真實事物。假設(shè)此時有人對他說他以前看到的一切只是一種錯覺,而現(xiàn)在他正接近著真實并且他的眼睛被迫看向了更加真實的存在,看得更加清晰,他會怎樣回答呢?如果再有人把那些從矮墻上經(jīng)過的東西一一指給他看,并且要求他為之命名,他將不知所措。他必定認(rèn)為以前看到的影子比現(xiàn)在看到的東西更加真實。
我們再來假設(shè),他被硬拉著走上一條崎嶇的坡道,直到走出洞穴看見太陽,他會感到痛苦并且憤怒。當(dāng)他來到陽光下,他會感到昏眩并且無法看到任何被稱為真實的事物……最后他能觀看到太陽本身,認(rèn)為正是太陽造成了四季交替和年歲周期,并主宰著視覺世界的所有事物……
我們必須把這個故事看作一個比喻,洞穴如同視覺世界,火光如同太陽的力量。如果你把里面的人上升到地面的過程解釋為靈魂上升到智力世界的話,你就沒有誤解我。
在柏拉圖看來,人類在視覺世界中無法認(rèn)知真實的事物,換言之,人類通過眼睛看到的圖像只是一種錯覺而已,真實世界并非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人類只有通過知識才能準(zhǔn)確地認(rèn)知真實世界。柏拉圖在此有力地批判了現(xiàn)象絕對論。
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和喬治·貝克萊(George Berkeley,1685~1753年)也對此進(jìn)行了批判,洛克說道:
(人將兩只手放入)同一種水,在同一時刻可能一只手會產(chǎn)生冷的感覺,另一只手會產(chǎn)生熱的感覺,然而如果這些感覺真的因為水而產(chǎn)生的話,同一種水在同一時刻是不可能既是熱的又是冷的。[10]122
貝克萊描寫了海勒斯(Hylas)與費洛諾斯(Philonous)之間這樣的一段對話:
費:認(rèn)為同一種事物同時是冷的又是熱的,這不是極其荒謬的嗎?
海:是的。
費:假設(shè)此刻你的一只手是熱的,另一只手是冷的,立刻同時伸入一盆不熱不冷的水中,難道不是一只手感覺水冷,另一只手感覺水熱嗎?
海:是的。
費:因此我們不應(yīng)該按照你的原則,認(rèn)為水同時是冷的又是熱的嗎?照你所承認(rèn)的,這不該被認(rèn)為是一種荒謬嗎?
海:我承認(rèn)似乎是這樣。[11]107
洛克和貝克萊用了相似的例子說明人類通過觸覺而感知到的諸如冷和熱這樣的知覺并不能絕對地反映出水的“真實性質(zhì)”,沒有絕對的冷,也沒有絕對的熱,人類直接感知到的自然現(xiàn)象是相對的。換言之,人類通過知覺認(rèn)知世界所獲得的不是“真實”,而是一種“錯覺”,人類生活在由觀念構(gòu)成的世界中,區(qū)別于真實存在的世界,也就是說世界以兩種形態(tài)存在,即由人類語言建構(gòu)的觀念世界和客觀存在的自然世界。現(xiàn)代解剖學(xué)和視覺心理學(xué)支持柏拉圖的觀點,盡管我們似乎以直接的客觀確定性來觀看外在客體,事實上我們是像洞穴中的囚徒那樣在觀看,從客體的影子和反射中作推論。
為了驗證人類知覺的現(xiàn)象絕對論,20世紀(jì)初期的心理學(xué)家做了大量實驗,比如美國心理學(xué)家所羅門·埃利奧特·阿施(Solomon Eliot Asch,1907~1996年)做了這樣一個經(jīng)典實驗:“把某個人關(guān)在一個黑暗的房間內(nèi),他只能看到一個被照亮的大方框的輪廓以及方框內(nèi)的一個光點,當(dāng)移動方框,那個人反而會感覺光點在移動,他會非常準(zhǔn)確但不是絕對地感知到光點和方框之間的相對運動。”[12]58之所以會產(chǎn)生這種效應(yīng),是由于人們無意識地預(yù)設(shè)了視覺環(huán)境中的大部分較大體積的物體是靜止的,體積比較小的物體發(fā)生了移動。經(jīng)驗的“客觀性”和視知覺的確定性不僅僅是產(chǎn)生錯誤的向?qū)В硗膺€掩蓋了它們所依賴的比較推理。[8]6
人類不僅在對客觀自然世界的感知過程中會陷入到現(xiàn)象絕對論中,而且在研究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文化現(xiàn)象時也會陷入現(xiàn)象絕對論,藝術(shù)史研究也不例外,許多研究者會根據(jù)自身所處的文化體系價值標(biāo)準(zhǔn)去衡量、評判其他文化的價值,這種天真的態(tài)度被稱作“本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①W.G.Sumner,Folkways,Boston:Ginn,1906;M.J.Herskov its,Man and His Works,New York:Knopf,1948;O.Klineberg,The Human Dimens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4.然而“本族中心主義”有許多附加意思,在此它可以被界定為這樣一種觀點,即某人所處族群的習(xí)俗、價值被無意識地用來作為所有判斷的標(biāo)準(zhǔn),作為萬事萬物的中心,其他族群及其習(xí)俗都相應(yīng)地被排除。[13]13
為了理解這種本族中心主義,我們必須理解文化同化(Enculturation)的過程。[14]39所有社會性動物,包括人在內(nèi),都會經(jīng)歷一個使自己的行為適應(yīng)其社會同類行為的學(xué)習(xí)過程,這個過程包括了沖突與合作。除了社會性動物共有的這種社會化過程之外,人類還經(jīng)歷了文化同化過程,由此進(jìn)入到了某一文化中。除了行為標(biāo)準(zhǔn)和社會規(guī)范的有效約束之外,一種更為細(xì)微的、無意識的觀察學(xué)習(xí)過程,在人類群體的行動中不斷起著作用。文化同化經(jīng)驗的一個特征是個人度過一生仍舊無法意識到對他而言很“自然”的個人習(xí)慣是如何從學(xué)習(xí)過程中產(chǎn)生,在這個學(xué)習(xí)過程中他沒有機會做出選擇性的反應(yīng)。通過對比那些不愿接受文化同化的“反叛者”,我們便能輕易發(fā)現(xiàn)那些正經(jīng)歷文化同化過程的個人被同化后所出現(xiàn)的效果和所產(chǎn)生的影響。[8]10
比如,一旦兒童學(xué)會了語言,他對世界的大部分認(rèn)知都是通過周圍其他人已經(jīng)觀察和學(xué)習(xí)到的內(nèi)容來獲取的,甚至他對物質(zhì)客體的認(rèn)知也是建立在他人的經(jīng)驗之上。因為這類不可見但受到文化類別嚴(yán)格限定的知識對于最終認(rèn)知的形成起著重要作用。正如我們無法對所有波段的光波都能做出反應(yīng),我們的眼睛在視覺中排除和忽略了部分頻譜波段,同樣,我們也無法意識到我們自己的文化所排除或忽略的其他經(jīng)驗類別、評估體系和行為模式。脫離其他文化,最徹底地被自己的文化同化的人在塑造自己的過程中最意識不到自己的文化及其作用。
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是探討價值在文化中的本質(zhì)及作用這一問題的一種方法。文化相對論的基本原則是各種判斷均以經(jīng)驗為基礎(chǔ),每個個體根據(jù)其自己所適應(yīng)的某種文化來解釋經(jīng)驗。甚至物理世界的真相都是通過文化同化來辨別的,以至于對時間、距離、重量、尺寸和其他“現(xiàn)實”的感知都是由一個群體的習(xí)俗決定的。構(gòu)成一個特殊社會的人的行為和思維習(xí)慣模式的總和便是文化。[15]351
觀念究竟如何影響人類接近物理世界,赫斯科維茲以下例說明。居住在美國西南部的印第安人根據(jù)六個而非四個基本方位思考,在東、南、西、北之外,他們還增加了“上”和“下”。從這點看,宇宙是三維的,這些印第安人完全是接近自然的。而在我們的文化中,甚至在飛機導(dǎo)航儀器中,會把方向和高度分開。我們在兩個不同的平面上運用這些方位:一個是水平的,比如我們正朝東北方向行駛;一個是垂直的,比如我們正在8 000米的高度巡航。
判斷來源于經(jīng)驗,這一原則有一個心理學(xué)基礎(chǔ)。穆扎菲爾·謝里夫(Muzafer Sherif,1906~1988年)做了這樣一個實驗,把實驗對象安置在一間暗房中,房間內(nèi)有一個暗光源,當(dāng)開關(guān)被按下后光源時亮?xí)r滅。一些實驗對象被帶入這個房間,首先是作為單獨的個人,之后是作為一個小組中的成員,后者在單獨被實驗之前已經(jīng)對小組群體情況熟悉了。盡管光源是固定的,實驗對象在這個房間里是感知不到運動的,因為房間太暗了,他無法根據(jù)固定的點來判斷移動。每個實驗對象的判斷,清楚地說明了當(dāng)沒有客觀標(biāo)準(zhǔn)可參考時,個體主觀地建立了一個范圍,在這個范圍中的一個點(一個標(biāo)準(zhǔn)或規(guī)范)都是為個體所特有。重復(fù)實驗,這個范圍也被重新建立。在小組群體的實驗中,每個個體通過光源對運動范圍做出判斷,各個實驗對象之間對光源判斷的差異并不大。每個小組建立了一個為其所特有的標(biāo)準(zhǔn)規(guī)范,參與實驗的小組個體成員會根據(jù)他之前從小組中獲得的范圍和標(biāo)準(zhǔn)來感知周圍情況。
在這些結(jié)果以及其他相關(guān)心理學(xué)實驗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來的規(guī)范,諸如模式化概念、流行時尚、慣例、風(fēng)俗、價值,這些已經(jīng)確立的社會規(guī)范的心理學(xué)基礎(chǔ)是個體之間互動的共同框架結(jié)構(gòu)。一旦這些結(jié)構(gòu)在個體之間建立和融合,它們便作為重要決定因素決定或影響個體與其即將面臨的情境之間的互動。[16]92-106
阿爾弗列德·歐文·哈洛威爾(Alfred Irving Hallowell,1892~1974年)從跨文化因素的角度擴充了謝里夫的觀點,強調(diào)文化對知覺過程的影響。他認(rèn)為,就任何一個作為整體的生物體而言,一個持續(xù)調(diào)整適應(yīng)過程的基本必要功能之一便是知覺……因此對我們?nèi)祟惾后w而言,在充分理解、解釋或預(yù)測那些對某些行動達(dá)成共識的個體行為的過程中,我們在一個社會中已經(jīng)習(xí)得和獲得的經(jīng)驗是非常重要的。[17]166-167
我們也許會問:文化相對論意味著所有的道德價值體系,所有的對與錯觀念都建立在一種變化中,所以就不需要道德、正當(dāng)行為和倫理規(guī)范?赫斯科維茲指出,由于文化相對論是一種哲學(xué)概念,承認(rèn)由各個社會建立的價值控制著他們各自的生活并且理解他們各自的價值,盡管各個社會建立的價值可能各不相同。在思考文化相對論時,將殊相和共相相區(qū)分是很有必要的。殊相是固定的,就研究的習(xí)俗而言,殊相是沒有變化的。另一方面,共相是指那些從所有自然或文化世界現(xiàn)象的變化范圍中提取的共性。不存在絕對的價值、道德、時間、空間的標(biāo)準(zhǔn),并不意味著這些(不同形式的)標(biāo)準(zhǔn)不構(gòu)成人類文化中的共相。[15]364
在思考文化相對論時,赫斯科維茲提出必須承認(rèn)它有三個不同方面,即一方面是方法論的,一方面是哲學(xué)的,一方面是實踐的。在大部分討論中,這都被忽視了。作為方法,文化相對論圍繞著科學(xué)的原則,在研究一種文化時,人們力求盡可能地實現(xiàn)一種客觀性,對其研究對象的行為模式不作評判或者并不試圖改變它們。相反,人們根據(jù)其所研究的文化中已經(jīng)確立的關(guān)系來理解、認(rèn)可研究對象的行為,并且對預(yù)先形成的解釋框架不作評論。文化相對論作為哲學(xué)理論,除關(guān)注文化價值的本質(zhì)之外,還關(guān)注文化同化過程能產(chǎn)生思想、行動這種認(rèn)識論的隱含意義。實踐方面包括了將產(chǎn)生于這種方法的哲學(xué)原則運用到更為廣泛的跨文化領(lǐng)域研究中。[15]365
不難看出,巴克森德爾的研究便是基于赫斯科維茲所提倡的這種文化相對論之上的。無論是對文藝復(fù)興時期意大利繪畫還是對18世紀(jì)法國夏爾丹繪畫的研究,巴克森德爾都是客觀地還原到當(dāng)初的情境中,根據(jù)當(dāng)時社會中普遍流傳的語言習(xí)慣、批評術(shù)語、思想觀念和社會活動來解釋那些特有的繪畫風(fēng)格是如何形成的。
參考文獻(xiàn):
[1]Michael Baxandal.Patterns of intention:on the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f pictures[M].New Haven,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2]Margaret Iversen.Review:patterns of intention[J].Oxford art journal.1986,9(2).
[3]Michael Baxandall.The language of art history[J].New literary history.1979,10(3).
[4]Kurt W.Forster.Critical history of art,or transfiguration of values[J].New literary history.1972,3(3).
[5]James S.Ackerman.Toward a new social theory of art[J].New Literary history.1973,4(2).
[6]David Rosand.Art history and criticism:the past as present[J].New literary history.1974,5(3).
[7]Allan Langdale.Interview with Michael Baxandall,3rdand 4thFebruary 1994,Berkeley,CA[J].Journal of art historiography,2009(1).
[8]MarshallH.Segall,DonaldT.Campbell,MelvilleJ.Herskovits.Theinfluence of culture on visual perception[M].Indianapolis:Bobbs-Merrill Company,1966.
[9]Plato.Republic[M]//柏拉圖,著.本杰明·喬伊特,譯評.柏拉圖著作集3.英文本.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8.
[10]John 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M].Pennsylvani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99.
[11]Three dialogues between hylas and philonous[M]//Geroge Berkeley.The works of George Berkeley Vol.1.London:J.F.Dove,1820.
[12]S.E.Asch.Social psychology[M].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52.
[13]W.G.Sumner.Folkways[M].Boston:Ginn,1906.
[14]M.J.Herskovits.Man and his works[M].New York:Knopf,1948.
[15]Melville J.Herskovits.Cultural anthropology:an abridged revision of man and his works[M].New York:Alfred A.Knopf,1960.
[16]M.Sherif.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norms[M].New York: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1936.
[17]A.I.Hallo well.Cultural factors in the structuralization of perception[M]//John H.Rohrer,ed..Social psychology at the crossroads.New York:Harper&Brothers,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