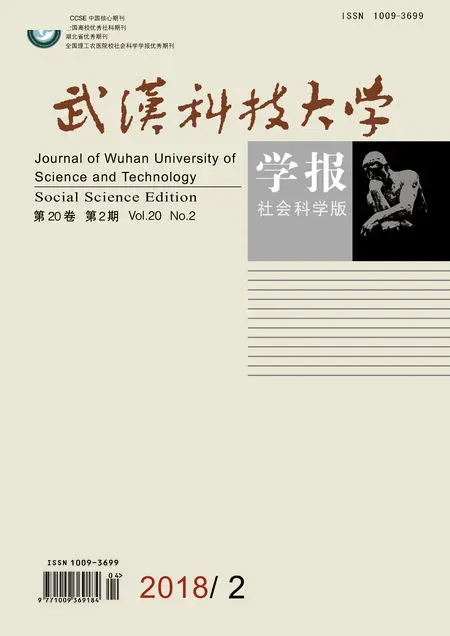論莊子思想中的“天人之際”
張 洪 興
(東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天人關系是中國古代思想家著力解決的根本問題之一。中國人往往主張天人合一,以天來證人,以人來證天,在天人境界中感悟社會與人生。莊子作為道家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有關天人關系的論述是道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厘清其內涵、特點,對于體察道家思想乃至于理解中國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關于天道與人道
天人觀念的生成與中國人的生活環境、生活習性息息相關。我們知道,中國文化建立在東亞大陸農耕文明基礎之上,而農耕文明的特點,要求勞作者根據天時和自然運行的規則來精耕細作,否則,違背天時(自然),農作物就會欠收甚至顆粒無收。所以,天與人相合,或者說天人合一,是一種自然而然產生出來的觀念,它最初是勞作者為達到農作物豐產、豐收的一種主觀意愿、主觀追求,進而抽象、升華為哲學層次的天人觀念、天人關系,成為中國古代哲學研究的至高命題,貫穿于整個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史。張懷承等在《簡析天人合德的理論意蘊》一文中說“天人之辨內涵著兩種最基本的學說,即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而以天人合一為主流,這是中國傳統哲學在天人關系上的基本觀點和特點”[1],情況大致如此。

道家天人關系也包括天人相合、天人相分兩個方面,但內容與儒家明顯不同。在道家思想體系中,道是本體,是至高的存在,它統攝著人、地、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人、地、天都要遵循著自然的法則,所以它們或相合或相分,有著自己的運行規律。老子作為道家學派的創始人,一方面積極肯定天道,《老子》一書中“天”出現29次,除指無意志無道德屬性的自然之天外,大都與天道有關,賦予天道一些基本特點,如退讓①、不爭②、無私③、公正④等;另一方面反思人道,人道常作為天道的對立面出現,如《老子》第七十七章中說的“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就是一例。總體來看,道家天人關系更加關注天道、人道之間不協調、矛盾的一面,基本的傾向是尊天而卑人,以實現人道的自然與無為。許春華認為,“老子以獨特的‘天人合道’答案開辟了道家學派,它一方面向上將道提升為存在本體與價值本體的統一體,另一方面向下翻轉為天道、地道、人道的整體性與統一性,整體性是指天、地、人涵納于道體之下,天道、地道和人道原則是其體現;統一性則指自然、無為原則貫徹天道、地道和人道過程始終”[2]。
二、無以人滅天
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則,莊子高度關注天人關系。莊子明確指出了天道與人道的不同,《莊子·在宥》篇中說:“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在莊子看來,天道與人道是無為與有為的關系,是主(君)與臣的關系,相去甚遠。基于這樣的認識,莊子最早提出了天與人孰勝的問題,《莊子·大宗師》中說“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明確告誡人不能與天對立,天與人處于不同的層次、不同的境界,天與人不相勝。同時,莊子也反對把天與人分割開來,因為“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莊子·達生》)、“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莊子·天道》),人應該與天為一。
因為天道與人道的不同,莊子要求要“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強調“不以人助天”(《莊子·大宗師》)、“無以人滅天”(《莊子·秋水》)。在《莊子·秋水》篇中有河伯與北海若的對話,在回答河伯“何謂天?何謂人?”時,北海若說:“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北海若在這里簡單作了個比喻,牛馬長著四個蹄子,是與生俱來的,是自然而然的,這就是天;而為了約束、限制馬和牛,給馬帶上馬絡頭,給牛鼻穿上鼻環,這就是人為。莊子的“無以人滅天”就是效法天道,順天道而行,不以人為損害天性。具體說來,就是要去駢、去驕、去知(智)、去才(材)、去情、去“我”,等等。
去駢。《莊子·駢拇》篇,以駢拇、枝指、附贅、縣疣為喻,批判儒家仁義之弊,強調道德之純真。所謂駢拇,即大腳趾與第二趾粘連,比正常人少一個腳趾;所謂枝指,指一只手有六個指頭,比正常人多一個手指;所謂附贅,指人身體上多長出來的肉;所謂縣疣則指人身體上長出來的小瘤子。我們知道,儒家認為仁義是人內在的本性,視仁義為道德理想。但莊子認為,所謂仁義不過是人本性之外的“駢拇”“枝指”“附贅”“縣疣”,使“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而“失其性命之情”,直至身殉其中而仍自以為聰明,比如伯夷,為名死于首陽之下,和盜跖并無不同。而如離朱、師曠、曾史、楊墨,“皆多駢旁枝之道”,都不是天下正途。
去驕。本著道家柔順、低下的原則,莊子強烈批判“驕”,要求去驕。《莊子·達生》篇中有“紀渻子養斗雞”的寓言,紀渻子養斗雞經歷了幾個過程,剛開始斗雞“虛驕而恃氣”,接著“猶應向景”“疾視而盛氣”,最后如“木雞”時才算成功。紀氏養斗雞的過程就是一個“去驕”的過程。《莊子·列御寇》篇中講了孔子七世祖正考父的故事:“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于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這則故事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去驕”的重要性。正考父第一次被任命為士的時候,謙虛地曲著背;第二次被任命為大夫的時候,恭敬地彎下腰;第三次被任命為卿時,身體伏近于地面,順著墻根行走。人們如果都像正考父這樣,就沒有人敢不遵守法度了。而一般世俗之人,第一次被任命時,就會自高自大;第二次被任命時,就會在車上忘形地舞蹈;第三次被任命時,就會直呼伯父和叔父的名字,這樣只會給自己帶來災難。
去知(智)。道家思想中有反智傾向,余英時稱之為“超越的反智論”[3],這一方面老⑤、莊一脈相承。為什么莊子要求去知(智)呢?在他看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莊子·養生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知識是無限的,以有限的人生追求無限的知識正如夸父逐日一樣,徒勞無功;再者,“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莊子·齊物論》),人各有其“成心”,很難有一定的是非標準。《莊子》書中,惠施可以說是一位智的典型。他學富五車、善辯多才,卻不能合道,只能內勞其神,外勞其形,“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莊子·天下》),最后只落得個“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莊子·德充符》)、“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莊子·天下》)的可悲結果。《莊子·繕性》篇中,莊子多次提到知的問題,如“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強調不用巧辯來修飾智慧,不用智慧使天下人受窮累,不用心智使自己內德受損傷⑥。
去才(材)。同去知相聯系,莊子還強調去才(材)。因為在莊子看來,人在某一方面的智力、才藝會“胥易技系,勞形怵心”(《莊子·應帝王》),甚至會給其帶來殺身之禍。《莊子·人間世》中,有幾個關于樹木材與不材的寓言,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匠石之齊”的寓言。在匠石眼中,櫟社樹“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毫無用處,是不材之“散木”;結果櫟社樹托夢,痛斥匠石,闡述了無用之用的道理。《山木》篇中有“莊子行于山中”的寓言:大木因其不材得終天年,而大雁卻因不能鳴(不才)而被殺,世事吊詭,所以莊子認為最佳的方式是處于材與不材之間,既不鋒芒畢露,又不一無所是,這與老子所謂“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老子·39章)有異曲同工之妙。
去情。在《莊子·德充符》中,莊子與惠子討論了人之有情、無情的問題。莊子主張無情,卻遭到惠子的詰難。在惠子看來,人的情感是人的根本屬性,沒有情感,就不能稱之為人。但莊子在解釋其無情論時,強調“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以不“內傷其身”“益生”為根本。也就是說,人不應被內心的欲望、情感所左右,導致身心的不適。在《莊子·在宥》篇中,莊子進一步解釋了有關情的問題,他說:“人大喜邪,毗于陽;大怒邪,毗于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于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后有盜跖、曾、史之行。”人的大喜、大悲會使人陰陽不調,進而傷害“人之形”,所以要去欲去情。
去“我”。每個人、每個團體、每個族群乃至于整個人類往往以自我為中心,以自己的“成心”、自己的立場考慮和處理問題,于是就容易造成狹隘、偏頗、自私甚至罪惡。我們上文討論的駢、驕、知(智)、才(材)、情都與“我”有關;若沒有“我”,就不可能有“以人助天”“以人滅天”的問題。莊子很清楚“我”的局限,《莊子·齊物論》篇中說:“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不論是聰明還是愚笨,人都很難逃出自己的“成心”。莊子批判“成心”,最典型的是《莊子·至樂》篇中“魯侯養鳥”的寓言。魯侯因為喜歡海鳥,為它奏樂,給它酒喝,喂它豬肉、牛肉、羊肉,結果海鳥卻一口肉也不敢吃,一口酒也不會喝,三天后就死掉了。莊子在該寓言中指出了“以己養養鳥”與“以鳥養養鳥”的區別,所謂以己養養鳥,就是以自己的喜好來養鳥,以人助天;以鳥養養鳥,就是按照鳥的本性來養鳥,不以人助天,不以人滅天。鳥本來“棲之深林,游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鰍鰷”,這是它的自然本性,魯侯違反它的本性,只能落個可笑的下場。為去“我”去“成心”,《莊子·齊物論》開篇,南郭子綦在回答顏成子游“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的問題時,提出了“吾喪我”方法,并以此希望聞聽“天籟”之音。
莊子“不以人助天”“無以人滅天”的方法還有去泰、去奢等。所謂去泰、去奢,即不追求“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莊子·至樂》)的安逸舒適生活,拋棄所謂的榮華富貴,因為“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莊子·大宗師》)。《莊子·天地》篇中,莊子提出了五種“失性”的原因:“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莊子批判五色、五聲、五臭、五味以及“趣舍滑心”對人本性的傷害,也是對泰、奢等生活欲望的批判。
三、以天合天
莊子強調天與人的不同、天與人的分際,好像天與人是一種對立的關系,人在天面前無能為力,毫無作為。其實,在莊子的思想世界里,天與人是一種辯證的關系,莊子反對人為做作,要求人類無欲無為,其最終目的卻是在“天”原則下,以天合天,實現與儒家天人合一不同層面的道家的“天人合一”。
為做到以天合天,莊子在要求去駢、去知、去才(材)、去情的同時,還提出了委和、委順、委形以至委蛻等相關論點。在《莊子·知北游》篇中,丞在回答舜提出的“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的問題時說:“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這里接連出現了委形、委和、委順、委蛻的說法。委即托付之意,委形即托付形體,委和即托付天地之和氣,委順即托付自然之氣,委蛻即托付蛻變的生機。莊子以人的形體、性命乃至子孫都不能私有為喻,說明人只有委順自然,實現與自然、與道的合一。
莊子以天合天、實現天人合一的主要方法包括親自然、齊萬物、合技藝、養心性、同物化等五個方面。
親自然。人類生活在地球上,生活在自然界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每個思想家都會考慮的問題。與西方“人是萬物的靈長”“人是萬物的尺度”等觀念不同,中國人親近自然,中國文化堅持天人合一的觀念。在道家看來,人只是“域中四大”(《老子·25章》)之一,人在自然中生存,感受生命,完成生老病死的過程。莊子一方面細致入微地觀察自然,另一方面也把自己融入自然之中,感悟自然真諦,充滿了對自然的熱愛。《莊子》中有多處有關自然的描述。“春雨日時,草木怒生”(《莊子·外物》),僅僅八個字,就給我們鋪展了一幅生氣盎然的春之圖畫。自然界是美好的,與自然界和諧共生的人也是快樂而有靈性的,“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莊子·知北游》),在山林皋壤之間徘徊游弋,這種與自然合一的樂趣是符合人的天性的。“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勝”(《莊子·外物》),山林草木可以悅人之情性,一個“善”字,體現出莊子對自然化育人類、洗滌人類性靈的認識。莊子的“逍遙游”也是在天地之間、在自然界中完成的。《莊子·逍遙游》篇中,鯤鵬摶扶搖而上九萬里,蜩、鸴鳩、斥鴳各安其性,此謂物之逍遙;在篇末,莊子描繪了一番悠然自得的景象,人可以在“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這是人的逍遙。《莊子》中多次出現“游”的概念,如“游乎天地之一氣”(《莊子·大宗師》) 、“浮游乎萬物之祖”(《莊子·山木》),人的“逍遙游”與天地自然是密不可分、有機融合在一起的。
齊萬物。齊物論是莊子最為奇異的、最有魅力的思想,雖有“齊物之論”與“齊同物論”之爭,但二者并不相妨。在筆者看來,“齊同物論”之旨歸即萬物齊同,亦即“齊物之論”,側重點都是一個“齊”字。從學理來看,莊子雖承繼老子學說,認為道是本體,是萬物之母;但他同時強調,道“在屎溺”(《莊子·知北游》),而“德兼于道”(《莊子·天地》),萬事萬物不管如何卑微都有道、有德,從這一方面講,萬物就具有了齊同、平等的可能。《莊子·齊物論》篇中,莊子認為,因為“一曲之士”各有其成心,播弄是非,所以莊子要從道出發,希望去“我”(“吾喪我”),從而泯滅是非,物我兩忘。這就要求摒棄個人中心主義,摒棄個人主觀立場。在《莊子·逍遙游》篇中,莊子刻畫了藐姑射神人的形象,其主要的特點就是“旁礴萬物以為一”。“旁礴”者,混同也,齊同也,混同萬物為一體,在天與人之間,人才會不狹隘、不偏頗、不自私、不冒進、不亂為、不為惡。所以,莊子從“道”出發,認為世間一切矛盾對立的雙方,諸如生與死、貴與賤、榮與辱、成與毀、小與大、壽與夭、然與不然、可與不可等等,都是沒有差別的,各家各派不如物我兩忘,不言不辯,超然于是非之外。
合技藝。在《莊子》中,有一類寓言需要引起我們特別的關注,這就是《莊子·養生主》篇中“庖丁解牛”、《莊子·天道》篇中“輪扁斫輪”、《莊子·達生》篇中“佝僂者承蜩”“紀渻子養斗雞”“呂梁丈夫蹈水”“梓慶為鐻”等,這些人的共同之處在于都有神乎其神的技藝,其中以“庖丁解牛”最為經典。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時,“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解牛的動作像是在舞蹈,讓人賞心悅目。接下來,庖丁為文惠君講述了自己技藝修進的過程,且現在已達到了“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境界。庖丁的神技即是他的道,他的人與道高度地融合在一起。其他,如輪扁斫輪是“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乎其間”,佝僂丈人承蜩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梓慶為鐻達到了“以天合天”的境界。庖丁等人的技藝與機械力不同,機械力屬于以人助天的內容;而庖丁等人的技藝,是心與身的交融,達到了人技合一的境界。與之相反,《莊子》中還有一些違反天理天性的百工技人,包括伯樂、壽陵余子、朱評漫等,莊子對他們予以諷刺和批判。如壽陵余子,出自《莊子·秋水》篇“邯鄲學步”的寓言,他學步邯鄲,只落得個“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的可笑下場。人生天地之間,為糊口為養家為發展為國家,人總要在工作中體現其存在,對工作精益求精,像庖丁一樣達到某種境界,其本身即是體道、悟道、得道的過程。
養心性。莊子雖尊天卑人,但提倡通過心性修養,防止人的異化,回歸人的本然,從而達到合天體道的境界。莊子列出了很多種修心養性的方法,如心齋。《莊子·人間世》篇中莊子借孔子之口提出了“心齋”的概念,其主要特征是“虛而待物”,即專一自己的心志,用心靈去體會,用氣去感應,虛空容納萬物,在虛靜的心境中才能體會到道的妙處。再如坐忘。《莊子·大宗師》篇中寫了顏回體道的過程,他先是“忘仁義”,進而“忘禮樂”,后來達到“坐忘”的境界。所謂坐忘,即是“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忘記了自己的形體四肢,忘記了自己的聰明才智,體悟冥冥之中的大道。在通過心齋、坐忘等修養心性的同時,莊子還批判成心、機心。在《莊子·天地》篇中寫子貢過漢陰時,見一丈人正抱甕而出灌。子貢想教丈人用槔(機械)灌圃,沒想到招來丈人的強烈不滿:“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這讓子貢很慚愧,不能應對。在丈人看來,有機械必有機事,有機事則必有機心,而機心會破壞人的純樸本性,讓人心神不定。其實,莊子修養心性的目的(包括批判成心與機心)是去除心性中人為的做作與矯飾,還歸人本性本然之“天”。
同物化。《莊子·齊物論》中有“莊周化蝶”的寓言:“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在莊子描繪的景象中,莊周與蝴蝶物我不分,其樂融融;莊子禁不住問,是莊周夢化了蝴蝶呢,還是蝴蝶夢化了莊周?物我的錯位、齊同是道家天人合一體道方式之一。這里,莊周化蝶、蝶化莊周是在一個特定的虛設的環境里實現的,是在莊子的夢里完成的,莊子把夢渾同為實際的人生,說到底,所謂物化實際上是一種渾沌狀態。物與我同,夢與醒同,生命在這種體道境界里相互轉化、流逝或者是達到永恒。《莊子·齊物論》篇在提出“吾喪我”、批判“成心”、泯滅是非、消解辯爭之后,以“莊周化蝶”的寓言作結,混同物我,無非在強調“道通為一”。莊子還把物化同死亡聯系在一起,如《莊子·天道》篇中說“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又如《莊子·刻意》篇中說“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生命、天行、物化、死亡聯系在一起,就成為一個自然的過程,生死一之,物化同之。
總之,對于天人關系而言,莊子首先強調天與人、天道與人道的不同,尊天而卑人;在此前提下,莊子要求加強人道修養,通過去駢、去驕、去知(智)、去才(材)、去情、去“我”等方式,做到親自然、齊萬物、合技藝、養心性、同物化,以期會通天人,以人合天、以天合天,并進而達到道家天人合道的境界。
注釋:
①《老子·9章》:“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②《老子·73章》:“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③《老子·7章》:“天長地久。天地所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④《老子·77章》:“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
⑤《道德經》中,對知識和智慧否定、批判的言論很多,如“智慧出,有大偽”(《道德經·18章》),“絕圣棄智,民利百倍”(《道德經·19章》),“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道德經·57章》),“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道德經·65章》)。
⑥莊子對知(智)的態度也是有變化的。《莊子·繕性》篇中還提出了“以恬養知”的問題,說“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認為恬靜可以涵養智慧,智慧可以涵養恬靜,二者交相涵養,道德就會從自然本性中產生出來。這里則對智慧給予了肯定。
[1]張懷承,賀韌.簡析天人合德的理論意蘊[J].倫理學研究.2004(6):46-50.
[2]許春華.天人合道——老子天道、地道、人道思想的整體性與統一性[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6):51-56.
[3]余英時.余英時文集:第二卷[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