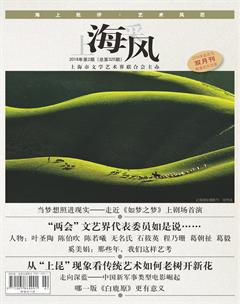陳伯吹點燃美麗的良知之燈
馬信芳
位于延安西路64號的上海市少年宮建筑始建于1924年,它是英籍猶太人嘉道理爵士的私宅,外表極為壯觀,內裝修更為豪華,主客廳直通二層,全部用意大利進口大理石裝修,進入大廳猶如置身于一幢大理石宮殿,于是又被譽為“大理石大廈”。1953年后歸宋慶齡創建的中國福利會少年宮使用,自此,這里成了孩子們的樂園。
市少年宮:聽大師講《一只想飛的貓》
筆者十分幸運,兒時曾為滬上南區某小學少先隊大隊長,故有機會被送往市少宮“進修”。正是在這所大理石宮殿里,我遇到過兩位大師,一位是大畫家華三川,他年輕當學徒時,還偷著學畫。當他向我們展示了自己為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所作的插圖時,我們驚呆了。后來我們特地去買了他繪制的連環畫《交通站的故事》,看了又看,奉為至寶。另一位就是兒童文學大師陳伯吹。來之前,老師就告訴我們,陳伯吹受家里條件限制,小時候只讀過三年初中。那天,我們是拿著他寫的童話《一只想飛的貓》來聽他講課的。陳先生一身中山裝,老教師的模樣,和藹可親。雖然我們當時已經是六年級了,但關于創作卻是一無所知,只知道他將那只“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個耗子”的貓描繪得活靈活現,把那只驕傲自大、目空一切、自吹自擂的“想飛的貓”表現得淋漓盡致。我們仿佛在這只頑皮的貓身上看到了我們周圍有些兒童的淘氣性格和微妙心理。
后來,我們知道了,這是陳伯吹先生的代表作。《一只想飛的貓》發表于1955年,是他針對建國初期某些嬌生慣養的兒童驕傲自大、好逸惡勞等缺點而創作的諷刺故事。作品輕松幽默,充滿喜劇色彩,讓一只不切實際地一心想飛而終于摔了跟頭的貓來告訴我們如何做個好孩子。
那天,陳伯吹先生還介紹了自己的經歷。
他是上海寶山縣人,1906年出生于寶山的羅店鎮。他的小學時代是在寶山縣立羅陽小學(今羅店小學)度過的。之后又在寶山縣甲種師范講習所(相當于今天的初中)念了3年書,畢業后分配到楊行鄉朱家宅第六國民學校當教員。
當他17歲時,陳伯吹作出了決定他一生命運的重大抉擇。這是1923年,他開始了兒童文學寫作,寫出了第一部中篇小說《模范學生》(后來改名為《學校生活記》)。兩年后,1925年2月,他被調到縣立淞陽小學(今寶山實驗小學)任國語和算術教員,同時擔任初級部主任,兼任三四年級班主任。
這時的上海,已經是一座散發著現代氣息的大都會,為許多青年文學家所傾慕。1929年,陳伯吹來到大上海,時年23歲。他先是在上海私立幼稚師范學校當地理課教師。這時他感到知識不夠用了,不滿足自己僅有的那點學歷,于是報名參加大夏大學高等師范專修班的考試,最終被錄取了。這樣,上午他在幼師學校給學生上課,月薪只有14元;下午就到大夏大學當學生聽課;到了晚上,就躲在幼師所在地檳榔路(今安遠路)潘園的一間只有5平方米的宿舍里,徹夜筆耕。用今天的話說,他是半工半讀。
顯然讀書不易,使他更加勤奮。同時,他想寫更多的作品。期間,他奮筆創作了中篇小說《華家的兒子》《火線下的孩子》等作品,并出版了兩本童話名篇《阿麗思小姐》和《波羅喬少爺》。
從1934年起,陳伯吹轉行當起兒童書局的編輯部主任,主編《兒童雜志》《兒童常識畫報》《小小畫報》三種雜志,同時還和兒童書局的同事一起,編輯了一套有兩百本之多的《兒童半角叢書》,以及一套一百二十本的《我們的中心活動叢書》等。在忙碌而沉重的編輯工作的同時,他又在1940年至1941年間攻讀了大夏大學教育學院的課業,終于獲得教育學學士學位。
陳伯吹先生還告訴我們,他一生中還有件難忘的事。那是1936年的一天,他曾在上海內山書店見過魯迅先生一面,親聆過這位文學大師的教誨。“我跟魯迅先生的會面是偶然的、短暫的,但是先生的容貌常常出現在我的腦子里。魯迅先生是真心誠意地關心下一代,真心誠意地為下一代服務的。”所以他說,后來他為什么那么關心少年兒童,重視少兒讀物,某種原因是與魯迅先生的教誨分不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讓陳伯吹真切感到,中國兒童文學的春天來到了。所以,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了新生的共和國的教育和文學事業中。這時候,他仍然擔任著中華書局的《小朋友》雜志主編,同時還被大夏大學、圣約翰大學、震旦女子文學院等聘為兼職教授。他在這些大學里開設了“教材教學法”“兒童文學”等課程。他知道,教育與兒童成長密不可分。
1952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少年兒童出版社宣告成立,陳伯吹被任命為副社長。1954年10月,他被調往北京,擔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兼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1957年5月,他又被調到中國作家協會成為一名專業作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讓陳伯吹精神煥發,他不僅為孩子們寫出了許多美麗的童話、詩歌和小說,如短篇小說集《中國鐵木兒》《飛虎隊和野豬隊》,童話集《幻想張著彩色的翅膀》,散文集《從山岡上跑下來的小孩兒》等等,還經常到中小學校、青少年宮與孩子們座談、交朋友,參加少先隊員們的夏令營和冬令營,與國內外許多少年兒童建立起真摯的友誼,經常通信往來。
后來我才知道,正是他愛孩子們,與他們交往,使他對兒童十分了解。他從與孩子們的交流中,知道了他們最需要什么,從而不斷完善自己的作品,由此想到作為一個兒童文學作家的責任心和使命感。他認為,無論是童話,還是其他樣式的兒童文學作品,都應該善于引導孩子們向前看和向上看,都應該“像老師般地關心教育的影響”,同時又絕不“疾言厲色地揚起戒尺來教育讀者”。到了晚年,陳伯吹還多次引述魯迅先生的那段“與幼小者”的名言:“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陳伯吹在一篇文章里這樣寫道:“作為從事兒童文學的作家們,就是該有這樣高尚的心態、堅定的毅力、勇往直前的氣魄,為指向少年兒童光明幸福的去處而靡寒靡暑地不遺余力。”多么真摯誠懇的肺腑之言,令人肅然起敬。
正是懷著“為小孩子寫大文學”的執著愿望,他筆耕不輟,創作了大量的兒童文學作品,出版了百余種著作。從1988年少兒社出版的《陳伯吹文集》中就可看出,陳伯吹是兒童文學創作的多面手,小說、童話、散文、詩歌、科學文藝、寓言等各種體裁,他樣樣精通,樣樣都寫得很出色。
陳伯吹還是我國兒童文學翻譯的先驅。從1930年出版譯著《小山上的風波》起,他一生翻譯了數十種世界兒童文學名著,包括影響很大的《綠野仙蹤》《小夏蒂》《普希金童話》《出賣心的人》《吉訶德先生的冒險故事》《黑箭》等。這些譯著不僅為孩子們提供了精美的精神食糧,豐富了他們的閱讀天地,也使其他作家們開闊了眼界和思路,促進了我國兒童文學創作的發展。
陳伯吹同時還是兒童文學理論家。他一直致力于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自1932年發表《兒童故事研究》,1935年發表《兒童文學研究》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卓有見識的兒童文學新觀念、新思維,極大地豐富和促進了中國兒童文學的理論建設。他的《兒童文學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論述兒童文學的專著。之后他又相繼出版了《作家與兒童文學》和《漫談兒童電影戲劇與教育》等。他提出的著名的“童心論”對兒童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閔行文化館:親為讀書活動頒獎
上世紀80年代,市文聯時常組織文藝家下工廠到農村演出。話劇表演藝術家喬奇、電影表演藝術家秦怡、配音演員喬榛等成為文聯的老義工。喬老爺(喬奇愛稱)由此與我成了忘年交。有天,我來到枕流公寓探望他。交談中,其愛人、著名電影演員孫景路老師笑著問我,小馬,最近在忙啥?我和盤托出:“我對口負責的閔行區讀書評獎,下周一有個頒獎活動,原本想請《文學報》主編杜老(杜宣)和峻青老師去頒獎,怎奈兩位周一例會,去不得。”孫老師見我有點不安,便建議不妨請請陳伯吹先生。“陳伯老?”(“文革”后,大家開始這樣稱呼他)“是啊。”孫老師介紹說,“他是兒童文學大家,又是上海市作家協會的副主席。行嗎?”我的眼睛不由一亮,請得動他嗎?我不由懷疑起來。孫老師真是熱心,說:“我來試試。”說著拿起電話便聯系。一會兒就說定了。孫老師笑著說:“我倆是政協委員,周一上午市里有個討論。你的活動在下午,不影響。吃過午飯你到北京路政協來接我們。我陪陳老,我也去。”當時,孫景路老師演的《喜盈門》正在熱映。一下去了兩個文化名人,我太高興了。
去閔行的路上,我笑著問陳伯老:“您老還認識我嗎?我曾當過你的小學生。”陳伯吹不由一愣,一副認真的模樣看著我,搖搖頭。我忙把當年在少年宮聽課的事說了。陳伯吹笑了,說:“是啊,當時少年宮我去了好多次。我喜歡和小朋友在一起。”
面對慈祥的老人,腦海里存在的一個疑問不由冒了出來,便直言相問:“陳伯老,你的名字有點特別,為什么叫……”陳伯吹笑了:“是不是有個‘吹字?”一旁的孫老師也湊上前來:“哎,這‘吹字,有什么講頭?”陳伯吹慢慢道來:“是啊,很多朋友都問過我。好,我說給你們聽。”他微笑著給我們解釋說,他的學名原叫“汝塤”,后來念書時,有位先生見了這個名字,說與其叫“汝塤”,不如用“伯吹”二字更有意思。原來,這“伯吹”出自《詩經·小雅》中的《何人斯》一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伯氏”指兄長、哥哥。他正是家中長兄。于是,他用“陳伯吹”作為自己的筆名,1926年,他在兒童刊物上首次發表作品,就署名“陳伯吹”。用著,叫著,這個筆名便沿用下來,而原來的名字“汝塤”,大家竟忘了。
車上,陳伯吹還告訴我們,他另有一個筆名叫“夏雷”,源自他的乳名“雷寶”。他是農歷六月二十四日生的,依照家鄉寶山的習俗,這一天是“雷公”的生日,所以長輩給他取名“雷寶”。后來他就給自己取了“夏雷”這個筆名。由這個筆名后來又衍生出另一個筆名“夏日葵”。陳伯吹在給一些報紙寫雜文時,常用它們。
那天頒獎大會,不用說,十分成功。因為請到了陳伯吹這樣的前輩作家,還有孫景路老師的捧場,讀者們都欣喜無比。特別是席間,陳伯吹一番語重心長的話語更讓讀者受益匪淺。他親切地告訴大家,做什么事一要方向對,二要堅持。
原來,陳伯吹剛開始寫作,當時為了掙錢養家,他什么題材都寫。他根據自己失戀的經歷寫過一個中篇小說《畸形的愛》,接著又把這段經歷寫成了長詩《誓言》,投給當時有名的文學雜志《小說月報》。該刊主編、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現代作家鄭振鐸讀后卻給了他一個忠告。因為鄭振鐸做過《兒童世界》主編,熟悉陳伯吹的“強項”在哪里。他從陳伯吹的職業優勢和創作專長考慮,勸他揚長避短,專攻兒童文學,那樣前途會更廣闊。陳伯吹聽后欣然接受了。他由衷地說,鄭振鐸先生這個忠告決定了我以后的人生方向。我真的要感謝他。
陳伯吹誠如美國詩人弗羅斯特所言“當我選擇了人跡稀少的那一條,從此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他心無旁騖地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全部精力,與兒童和兒童文學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在其91年的人生中,有74年為兒童、為孩子辛勤耕耘。“文革”結束后,已然70高齡的他毅然重拾創作筆耕不止,創作了《摘顆星星下來》《童話城的節日》《海堤上遇見一群水孩子》《好駱駝尋寶記》等兒童作品。這是一代兒童文學大師對幼小者的牽引與愛護,是一棵年老的大樹對身邊的小花小草的默默的關注與祝福。
南昌路寓所:自制“翻面”信封
陳伯吹住在瑞金路南昌路轉角處。房里除了書,家具極其簡陋。我當時住在西藏路南陽橋,穿過馬路,沿著一大會址所在的興業路一直往西走,就是南昌路。陳伯老十分客氣,認識了他后,他不時邀請我去玩。我不忍心打擾老人,所以前后只去過兩次,還有一次是接他去寶鋼講課。
有次到他家,他給任溶溶的信正寫完。只見他隨手從書桌上一疊舊信封中取出一個,將它撕開,翻了個面,然后用糨糊重新黏上,成為一個“新信封”。我十分奇怪,堂堂的上海少兒出版社的副社長,拿一個信封還不是輕而易舉的事,為何要如此,未免太小氣了。陳伯老似乎看出點什么,便說,這不是蠻好的嗎?那么好的牛皮信封,用一次怪可惜的。
后來,我知道,凡是私人信件,他不用公家信封。這方面,老人就是這么固執。
當時,我還不認識任溶溶先生。多年后,在孫毅老師的引薦下,來到任老的府上,交談中,我又提到了這件事,任老感慨萬千。
陳伯吹一生儉樸,平時節衣縮食,粗茶淡飯,絕不追求額外的物質享受。作家、評論家樊發稼曾回憶說,他第一次到陳伯老家,是在一個上午,到達時陳伯老正在用早餐。他簡單的早餐給樊發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碗薄薄的大米稀飯,半個咸鴨蛋和幾根咸菜絲兒。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一貫省吃儉用的長者、大師,卻在1981年春天,把他個人一生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55000元,慷慨捐出,設立了“兒童文學園丁獎”(后來為了感念他,1988年,改名為“陳伯吹兒童文學獎”),作為兒童文學評獎的基金,存入國家銀行,以每年的利息獎掖一些優秀作品,旨在激勵大家為孩子們創作出更多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
1989年,老人曾給當時在中國作家協會主持兒童文學委員會工作的文學評論家束沛德寫信說:“……我的捐款,受通貨膨脹的影響,愈來愈貶值……1980年我的捐款幾乎可以在上海購三幢房子,如今則半幢也買不到了,令人氣短!……”束沛德后來回憶說:“當時我讀著這封信,不禁潸然淚下。陳伯老為了鼓勵優秀創作,獎掖文學新人,真是愁白了頭、操碎了心啊!
同樣的話,我從中國作協副主席葉辛那里也聽到過。葉辛曾多次當過陳伯吹兒童文學獎的頒獎嘉賓。他說,上世紀90年代初,兒童文學獎的頒獎放在一個普通小學校里頒發,陳伯老私下對他說,一半是方便頒獎,一半是節省場地費用,那個小學校的校長在那次頒獎活動中給予了資助。陳伯老對他講:“剛開始拿出來的時候,這筆錢還是錢,現在我也感覺到這個獎金低了,現在募集錢很難。”
所幸的是,這項評獎在有關部門的幫助支持下一直正常運轉、如期舉行。
2003年,第20屆陳伯吹兒童文學獎首次頒發“杰出貢獻獎”。82歲的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家任溶溶先生獲得殊榮。當年頒獎會上,這位真誠、單純得像一個小孩子般的老作家坐在臺上還未開口,竟先嗚嗚地哭出了聲。全場來賓頓時愣住了。不過任老很快就從激動的情緒中恢復過來,他說:“我實在是太喜愛兒童文學了,這次得獎是我一生最大的榮譽。我現在還是那么喜歡寫兒童文學……”最后,說到動情處,任老把千言萬語變成了一句話:“兒童文學萬歲!萬萬歲!”
在任溶溶先生的感動與感激里,還包含著他對“陳伯吹兒童文學獎”的創立者、前輩作家陳伯吹先生的景仰與感念。我不知他此時此刻是否想到了那個陳伯吹親糊的“以舊變新”的信封。
1994年,兒童文學理論家梅子涵教授在當年《陳伯吹兒童文學獎獲獎作品集》里,曾由衷地寫下了這么幾句話:“謝謝敬愛的陳伯吹先生。是他設立了這個獎項。……我對他老人家只說謝謝怎么夠!在中國的兒童文學中,陳伯老是個偉大的人!”這些話,其實也代表了中國所有為兒童寫作的人的景仰與感激。
欣喜的是,為了進一步擴大影響,推動中國乃至世界兒童文學的發展做出貢獻,使這個獎項立足于新的平臺,2014年起,陳伯吹兒童文學基金專業委員會、上海市新聞出版局、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政府三方共同舉辦此獎,并將其列為“上海國際童書展”的獎項,正式更名為“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作為我國目前連續運作時間最長和獲獎作家最多的文學獎項之一,“升級”后的陳伯吹兒童文學獎影響更為深遠。
除了傾其所有設立了“陳伯吹兒童文學獎”,陳伯吹在晚年所做的另一個“吐哺”工作,就是如當年魯迅先生在世時一樣,點燃自己的膏血,為文學青年們照亮前路。他以耄耋高齡,為眾多的兒童文學新人閱讀稿子、點評習作、撰寫序言、函來信往,從不厭煩,甚至親自抄寫和推薦稿子。據統計,那些年凡是有青年作者請陳伯老為自己的書作序,他總是有求必應。自1977年到1997年他人生最后的20年中,他為人寫序竟達200多篇,光序跋集子就出了4本。
1997年11月6日,一代兒童文學宗師陳伯吹,在上海華東醫院仙逝,享年91歲。去世前他還在竭力完成最后一件事,那就是將自己一生積攢的全部藏書捐贈給浦東新區籌建中的一座兒童圖書館。如今,這座圖書館被命名為“陳伯吹兒童圖書館”。
春蠶吐絲,老燕銜泥。人的生命固然脆弱,但書比人長壽。陳伯老生前從來不曾以名人自居,總是謙遜地稱自己是“中國兒童文學大軍中的一個小兵丁”。一個善良、樸素、純凈和閃光的生命,在一種形式下像燃盡的蠟燭一樣熄滅了,但我們要說,他的作品被永存了下來。陳伯吹為孩子們點燃美麗的良知之燈將永不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