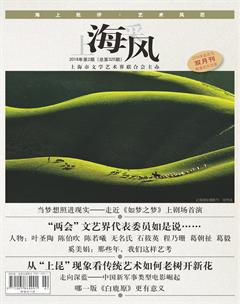那些年,我們這樣藝考
編者按:
又是一年藝考大幕拉開了。幾十年來,藝考一直是懷著藝術理想的中學生們通往繆斯圣殿的重要關隘。現(xiàn)在活躍在各種舞臺、影視領域的藝術家們,大多是從這個關隘險徑中走過來的。表演藝術家奚美娟是在“文革”后期上海戲劇學院恢復藝考后的第一屆考生,不妨聽聽她當年的藝考經歷——
“就跟著大家稀里糊涂地去了”
我是在1973年2月參加上海戲劇學院的招生考試的。那是“文革”后期的第一次招生。那年我18周歲,一個月前剛剛從上海浦東楊高中學畢業(yè),被分配到楊思公社蕩里大隊第三生產小隊插隊務農。我就讀的楊高中學坐落在浦東楊高南路邊上,因此而得名,此校后被并入上海浦東新區(qū)的楊思中學。
我的中小學時期,大部分是在“文革”的背景下度過的。所以在進入上海戲劇學院前,我從沒看過一臺話劇,也不知話劇為何物,但我從小對文學作品有感覺,才務農一個月,我就被組織上安排到川沙縣縣城里參加“土記者”學習班。這是一種集中學習的形式,吃住都在縣城里。有一天晚飯后,我們全體學員都接到通知,要我們晚上到縣招待所食堂集合,參加由上海戲劇學院和上海電影制片廠組成的聯(lián)合招生。記憶中我當時對此事沒有特別的興奮,只覺得很好奇,就跟著大家稀里糊涂地去了。
“我才知道了自己姓氏的標準讀音”
到了那里,招生組的幾十位老師已經坐成一排在等候考生。我們后來才聽說,“文革”中全國高校都停辦了,到了1973年,有關方面決定全國四所藝術院校率先恢復招生,這四所藝術院校分別是:上海戲劇學院、上海音樂學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上海就把當時的川沙縣作為招生試點。就這樣,我們這些被認為五官端正、愛好文藝的年輕人懵懵懂懂地在他們對面坐下,先由招生工作負責人介紹情況,隨后,老師們讓我們十個人為一組,跟著音樂節(jié)奏走路。大家覺得又好奇又好玩。當然,現(xiàn)在我們知道這是一種測試樂感與肢體協(xié)調能力的方法。接著,又讓大家做了一些簡單的形體動作還唱了歌。做完這些之后,就開始坐下來聊天。老師們都坐到我們身邊,很親切。有一位名叫朱鳳嵐的老師,特別有興趣地走到我身邊問這問那,她問了我的姓名,我原來按照上海本地人的發(fā)音,“奚”發(fā)音為“伊”,老師沒有聽懂,要我寫下來,然后她告訴我:“奚”這個字和“西”諧音,不是發(fā)“伊”的音。朱老師的點撥,我才知道了自己姓氏的標準讀音。
那天初試結束后,又有人過來說招待所里還住著上海音樂學院的招生老師,想讓我們過去聊聊。于是,我們其中的幾個人又被叫去和音樂學院的老師見面。記得有一位是上海音樂學院音聲樂系的溫可錚老師,另一位是大提琴張有勝老師。溫可錚老師讓我們各自唱了一首歌,自己還用渾厚的男低音示范了幾下,我記得他唱的是《深深的海洋》。臨走時他對我說:如果他們那里不錄取,就來考我們音樂學院吧。多年后的有一天,我已是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一名演員,在上海蘭馨劇場演出話劇《最后一幕》,散場后在劇場前臺遇到溫可錚老師,他居然還認得我,親切地對我說:“沒想到你現(xiàn)在會演戲啦!”想到幾年前招生時的情景,真像在做夢一樣。
“你現(xiàn)在知道什么是小品了吧”
初試結束后,“土記者”學習班也完成了學習任務,我回去繼續(xù)務農。但沒想到,此后多次被叫去復試。其中一次地點在浦東的民生路,原川沙縣洋涇公社文化站內,招生組的張慶芬老師教我做了一個小品,內容是這樣設計的:“我”干了一天農活扛著鋤頭回家,把鋤頭上的土渣清理干凈后豎立靠在了門口的墻上,“我”進家門,有些疲憊,坐下,順手拿起桌上碗中剩下的水喝了一口,稍緩后,拿起水桶到家門口的河邊取水回家倒入水缸里,又坐下來納鞋底。這些內容都是在一個虛設的場景中完成,只有水桶與桌椅是真的。做完這些,正不知道還能做些什么,這時,招生組有老師突然在觀眾席大叫:“豬棚失火啦,豬棚失火啦……”這是原來沒有被設計的內容,我下意識地直起身體,直覺告訴我這應該是在測試我的某種能力,“我”迅速拿起家里的水桶要去“救火”,跑到門口后怕一個水桶不夠,返身回來又帶上洗臉盆,急急忙忙跑了出去。做完這個“小品”,張慶芬老師來到我身邊,興奮地問我:你現(xiàn)在知道什么是“小品”了吧。印象中她那天幾乎沒怎么看別人的表演,一直在和我說著話。結束后走出考場,她還陪我走了一段路。張老師是上海電影制片廠的知名演員,后來并沒有教過我,但我深深記住了她的名字。
就這樣經過反復的考試,最后在川沙縣的幾千名考生中篩選出三男二女五個考生。那時我們這幾個人已是經歷了層層疊疊的多次考試,我一邊考一邊了解到一些專業(yè)知識,如:哪些是標準普通話中的前后鼻音,什么叫“小品”等等。現(xiàn)在回想起來很奇怪,我每次出門去參加考試,都覺得是去玩的,很開心,沒有一絲緊張感,更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人生道路正在發(fā)生重大變化。
“這是我第一次進了上戲校園”
過了一個月左右,我接到招生組的通知,讓我去上海戲劇學院參加一個學習班。到了那里才知道,這次的招生共挑選出了將近60名考生,為了確保考生質量,招生辦決定讓我們這些考生在上海戲劇學院集中住一個星期,進行短期訓練后,排練一臺節(jié)目作匯報演出,待演出結束,才能最后確定其中的45名(實際最后錄取了49名),作為那年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最終錄取的學生。我們那屆表演系學生的名額,原本定的是招六十名,分兩個班。一開始招生組沿用“文革”前的標準,考試過于嚴格,到最后經過層層篩選后,名額沒有招滿,在臨近開學前,又到上海市所屬的黃山茶林場急招了幾位學生。那次招生的嚴格程度,從讓最后入圍的考生集中進行專業(yè)訓練就可見一斑。這在上海戲劇學院的招生史上,應該也是僅有的一次。
為參加最后復試而入住上海戲劇學院,這是我第一次進入上戲校園。那一周除了每天排練,還記得女生宿舍安排了一位女老師陪著住,她是表演系的魏淑閑老師。她白天也參加對我們的業(yè)務排練,還負責我們這批考生的生活事務工作。那段生活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每天晚上臨睡前魏老師都要從家里趕到女生宿舍,在最靠近門口的那張上下鋪的木板床邊,和我們交代幾句話,然后熄燈一起休息。雖然魏淑閑老師后來沒有教過我,但幾十年過去了,我仍然對她那充滿關愛讓人信賴的臉龐有深刻的印象。
“我突然覺得自己就是那個人了”
那次匯報演出中,我被要求扮演一位有經驗的“中年”醫(yī)生,這是我第一次和戲劇人物發(fā)生聯(lián)系,完全沒有經驗又渴望去接近,自己和角色之間的各種差距,強烈地激發(fā)起我的新鮮感與求知欲。我非常非常努力,只要老師有一點啟發(fā),做一點示范,我都能原封不動地去照著做。每天排練結束后,我再把老師白天對我提的要求在腦子里過一遍,在動作上復習一遍,可總還是覺得不盡如人意。到了正式演出時,我被化妝成了一位留著齊耳短發(fā),身穿角色服裝的“中年”醫(yī)生。當我在后臺的鏡子里看到這個形象時,奇跡發(fā)生了,我突然覺得自己就是那個人了。凡老師在排練時要求過的,比如“那個醫(yī)生走路比你自己要穩(wěn)重”,“她說話聲音也沒有青年人的尖脆”等等,一下子我都領悟了。帶著這樣的感受,上臺順利地完成了匯報演出。臺下黑壓壓的一片,據說,上海許多專業(yè)團體的有關人員都來了。畢竟這是“文革”后期上海戲劇學院第一次招生,大家都想來看看這些經過千挑萬挑選來的人,究竟是什么樣的。負責排練這個戲劇小片段的老師叫徐企平。他后來當了我的班主任。
人生多么奇妙,那短短一周的最后復試,竟成了我們這幾十個考生的“命運七日”。此時,藝術之門與命運之門同時向我們敞開了。1973年的9月1日,我正式入學,成了一名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