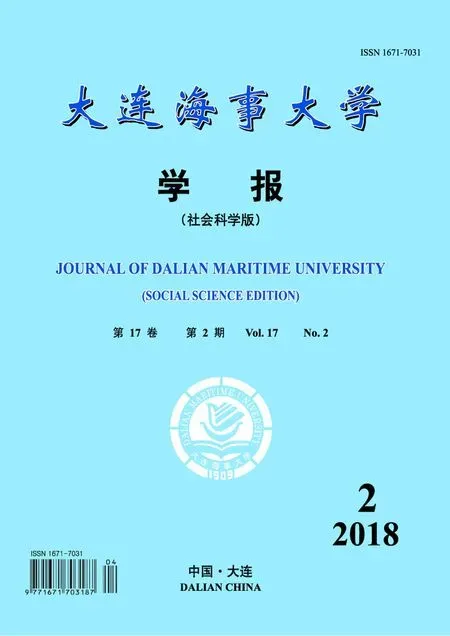從多重世界透鏡解讀納博科夫藝術創作中的邊界主題
崔永光,張藝玲
(大連海洋大學 外國語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3)
美國女作家安扎爾朵(Gloria Anzaldúa)所著的自傳式理論著作《邊界》(Borderlands/LaFrontera:TheNewMestiza, 1987)開啟了美國文學“邊界理論”(border theory)*大衛·約翰遜和斯科特·邁克爾森合著的《邊界理論:文化政治的界限》一書前言(Border Secrets: An Introduction)中將“邊界”劃分為“物理邊界”和“軟邊界”。他們將這一概念擴大到包括心理的、地理的空間,將之擴展成一個融匯人類學、社會學、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后殖民和種族問題的復雜概念。在文學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關注由設置“邊界”而引發的文化邊界的分析。的研究。她在該著作第一版前言中指出:“邊界是兩種或多種不同的文化在地理空間上的交界地。在那里不同種族和階級的人們占據著同一空間,他們之間產生了特殊的影響,空間在不斷縮小。”[1]“邊界”的概念已經超越了物理意義上的概念,延伸到心理學、性別和精神上的邊界,涵蓋著“美國-加拿大邊界、美國地方主義和美國移民的流散經歷”[2]等眾多主題。
享譽世界的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不僅是一位具有獨特寫作風格的小說家,還是一位集翻譯家、文學評論家、詩人、鱗翅目分類專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多面手。他個人生活的現實世界、移民社區與其蝴蝶世界和文本世界既相互獨立,又互相交織作用,構成了其藝術世界中的“多層次、多色彩”的特征。*納博科夫的俄羅斯本土研究學者A. A. 多里寧、列捷尼奧夫等都對納博科夫藝術世界中的多層面進行了分析,總結出作家的世界觀和詩學中的重要特征。因此,納博科夫的創作主題涵蓋著流亡、愛情、追逐人生、死亡、彼岸世界、時間與回憶等多元主題。
納博科夫的藝術世界同樣具有“邊界”主題特征。他早年同家人多次顛沛流離、遠離故國,至死也未返回俄國。對流亡作家而言,流散經歷(diasporic experience)首先意味著地理意義上的“越界”行為。越界表示對以往生活的徹底否棄,對人類尋求幸福、自由的權利的確認,以及對某種理想境界的追求。[3]離開俄國和童年天堂讓納博科夫感受到了種種不適,作家“突然感到了流亡的一切痛苦”[4]289。他的多部小說如《瑪麗》、自傳體回憶錄《說吧,記憶》等都明顯地帶有對俄國豐盈的懷舊情結。流亡的歲月,作家心中懷藏的對過去的思念是對失去的童年的一種極度復雜的感情。[4]69再者,流亡意味著創作語言上的轉向。納博科夫不得不放棄“美妙的、極為豐富和無比溫馨的俄語,轉向二流的英語”[5]14。盡管作家創作出了最為出色的英語小說,然而從俄語到英語寫作的徹底轉向是極為痛苦的,“就像在爆炸中失去了七八根手指,要重新學習拿東西一樣”[556]。面臨著越界的痛楚和語言的分離,納博科夫是幸運的,其創作生涯中的俄文和英語作品同樣出色,是真正的世界文學杰作。
盡管流亡越界的生活和創作語言的轉向使得納博科夫的作品具備“邊界”主題因素,但是其筆下的“邊界”主題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物理邊界”,更多地關注文本作品中的“內部邊界”或是“軟邊界”,諸如美學、科學、心理學、倫理學和形而上學中文化和精神的隱喻意義。流亡者的“越界”行為一方面要面臨孤獨、異化和疏離;另一方面,他們感到一種自由與解放,“打亂了傳統的地域、種族、語言和文化的分界線”[3],在異域尋找豐富的創作素材和靈感,為作家帶來更為廣闊的創作視野。通過納博科夫多重世界的透鏡去解讀其藝術創作中的邊界主題,讀者可以深入地認識作家對現實與幻想、科學與藝術、美學與倫理、詩性與哲性等微妙關系的細微刻畫,了解其小說創作中復雜難解的“中國式套盒”的敘述結構,理解納博科夫豐富的藝術觀和世界觀,進而揭示其藝術創作中潛藏的世界遺產和獨特價值。
一、納博科夫的文本世界:現實的虛幻與虛幻的現實
納博科夫創造的藝術世界可以說是豐富多彩、主題多元,無法用尋常的主題來界定。其豐富的文本世界涵蓋著翻譯、詩歌、小說、文論、傳記、信函等多重文本體裁,塑造了具有“眾多主體形象的藝術世界”,同時也為納博科夫的研究者和讀者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瑪麗》中俄羅斯僑民流亡生活的柏林、《洛麗塔》中的汽車旅館、《普寧》中的美國校園、《微暗的火》中虛構的贊巴拉,以及《阿達》中的反地界等多重文本世界揭示出納博科夫藝術世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各種文本作品之間既完全獨立,又“互相作用著,互為澄清,互相豐富,賦予作家的全部創作一種超結構的特性”[6]374,并暴露出文本之間的互文性特征。這些創作文本反映出納博科夫對認知世界的多種方法的嘗試,折射出“人類意識的復雜規律性問題,對人類生活事件進行主觀解釋的多樣性問題,人類認知的可能性和邊界的問題”[6]374。
納博科夫對世界文學的一大貢獻是他創造的文本世界讓瀕于枯竭邊緣的小說樣式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枯竭文學》(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是美國作家約翰·巴思(John Barth)撰寫的一篇重要論文。他提出這一文學的顯著特征是這一類型的作家幾乎不可能寫出原創性,或者是任何原創性的文學作品。一些作家將文學已經枯竭的痛苦假設用作新的文學作品的創作主題。除了代表作《洛麗塔》之外,《微暗的火》《勞拉的原型》《阿達》等作品形式獨特,在當時文學枯竭論與小說危機表征下發出了最強音。納博科夫的真正意圖是消除成見,打破僵化思維,“開拓小說領域的‘反地球’(《阿達》中的場景)與生機盎然的‘未知領域’,從而恢復與培育小說藝術的無限生機與自身的內在活力”[7]。可以說,正是因為喬伊斯、博爾赫斯、昆德拉、納博科夫、福克納等20世紀現代實驗派作家的存在,“小說的可能性的地平線在20世紀一下子延伸得很遠,至今可能還沒有人能完全看到它的邊際,這就給小說家和讀者都留下了異常廣闊的空間和令人激動的前景”[8]。可以說,納博科夫對20世紀小說藝術形式的可能性做出了創造性拓展,小說的邊界延伸到詩歌、評論、傳記、回憶錄等“雜糅性”(hybridity)的多元創作體裁。
納博科夫首先是一位舉世公認的文體學家,其復雜的敘事結構、眾多的文學典故、多樣的制謎游戲等高超的藝術手法讓這個聲譽名副其實。同博爾赫斯一樣,納博科夫的小說文本同樣使用“中國式套盒”(Chinese boxes)的技法,以期消除傳統意義上的真實與想象領域的差別。在《透明》中,虛構世界和小說家創作的作品之間的邊界不斷變化。在《洛麗塔》和《阿達》中,納博科夫通過聲稱虛構的編輯凌駕于劇本之上,努力去描繪一幅幅畫中畫。[9]細讀《洛麗塔》可以看出,該小說帶有戲擬文本體裁的特點。它是一部傳記、偵探故事、浪漫小說、道路小說,“同時也是一部非正派小說,是一部由一系列文學典故和許多具有嘲諷意義的名字組成的元小說”[10]。小說不僅具有獨到的技巧構思,還刻畫了主人公在世界中的心理掙扎,折射出作家藝術創作中的道德力量和倫理內涵。
《洛麗塔》中充滿懺悔之意的亨伯特找到已經結婚懷孕的洛麗塔時,依然會充滿柔情地對她癡迷眷戀。洛麗塔拒絕了亨伯特的請求,亨伯特悲傷離去,殺死了奎爾蒂。去世前不久,他在獄中寫下了最后的幾句話:“我現在想到歐洲野牛和天使,想到顏料持久的秘密,想到預言性的十四行詩,想到藝術的庇護所。這就是你和我可以共享的唯一不朽的事物,我的洛麗塔。”[11]同主人公洛麗塔一樣,小說《洛麗塔》終究成為藝術與道德完美結合的文本典范,不僅具有特異的創作風格和敘事技巧,其藝術價值的背后還閃爍著道德的光芒。
在納博科夫的小說中,《微暗的火》是運用“中國式套盒”手法最為巧妙的一部長篇英文小說。小說一經出版,立刻駁斥了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出現的小說形式危機的論調。奇特的文本結構、曲折的故事情節、復雜的迷宮敘事成就了“20世紀偉大的藝術作品之一”的口碑。然而,閱讀這樣一部帶有后現代文學特征的實驗主義小說,需要有創造力和想象力的反復讀者。他曾大聲疾呼道:“給我具有創造性的讀者,這個故事是給他們寫的。”*納博科夫在其《文學講稿》中專門有一篇題為“優秀讀者與優秀作家”的文章,列舉出“優秀讀者十大條件”,同時提出,“一個優秀讀者,一個成熟的讀者,一個思路活潑、追求新意的讀者只能是一個‘反復讀者’”。因此,對于納博科夫的小說,要求讀者反復地閱讀和揣摩,才能理解其深層次的文本結構和審美狂喜。梅紹武先生在《微暗的火》一書譯后記中談到納博科夫對自己心目中的讀者要求甚高:他們必須具有豐富的文學修養,精通多種語文,又得是個頭等詩人和福爾摩斯,還需要有豐富的想象力和特強的記憶力。納博科夫的意圖是邀請讀者與其一起踏上發現之旅,感受細讀文本的獎賞與狂喜。納博科夫不僅繼承和發揚了喬伊斯的互文性、戲仿等創作手法,還糅納了碎片拼貼、元敘述、解構和接受美學等諸多實驗主義技法。
后現代文學文本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不確定性,是開放性的。首先,《微暗的火》的文本結構呈現多層次性的套盒結構特征。最外一層是作家納博科夫,其創作靈感明顯地來源于翻譯普希金的詩作《葉普蓋尼·奧涅金》。接著是小說《微暗的火》包含著真實與想象的分界線。第三層是波特金(Botkin),故事中隱藏的敘述者。而波特金使用的化名金波特(Kinbot)是文本第四層。接著是評注和索引,講述了贊巴拉(Zembla)和其國王的故事。而金波特模糊了下一層結構,約翰·謝德(John Shade)的詩歌“微暗的火”。文本最后一層是謝德,他屬于詩歌的內部世界,因為他撰寫了一部揭示其生活的自傳體作品。[9]敘事結構的多層次性模糊了現實與想象的界限,內部文本中是金波特對謝德的詩篇“微暗的火”的第一層次的解讀,而呈現給讀者的外部文本是經過金波特闡釋的文本。那么,讀者提出的疑問是:誰是文本中可靠的敘事者(reliable narrator)?該詩篇的主題究竟是關于謝德的傳記,還是依據金波特的生活創作而成,引發了讀者的多元化闡釋。在詩歌的評注中,金波特暴露其真實的身份是來自一個遙遠的北方國度的流亡國王查爾斯二世。《微暗的火》作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虛構性文本,暴露這一點的正是隱藏在模仿話語中的金波特的不可靠敘述。*在《越界的敘事者》一文中,黃藝聰運用可能世界理論對《微暗的火》的故事世界進行了劃分,探討了嵌套模型和越界問題,展現了納博科夫與敘事者之間的層級關系,同時建構了讀者進入各個可能世界的橋梁。詳見文獻[12]。
復雜的迷宮式的敘事結構,作品中主人公之間的交織關系和多重闡釋深刻地暴露出納博科夫的現實觀,以及他對現實與虛幻關系的獨到理解。納博科夫在其復雜的、帶有自我意識的小說中經常探究現實的虛幻本質以及藝術家與其手法的關系。在納博科夫看來,藝術的最偉大之處在于其幻想性的欺騙性和復雜性。通過將藝術的文體特性置于道德或社會意義觀念之上,納博科夫倡導想象力的至上性。通過想象力,他認為可以獲得更有意義的現實。[13]為此,許多評論者批判納博科夫一味地使用文字游戲、拼字手法和多重雙關語等伎倆來創造復雜的迷宮敘事結構,批判他拒絕處理社會、政治問題和倫理主題。事實上,在其復雜的文字游戲、語言戲擬和文體互文性等美學策略的背后,隱藏著納博科夫對捍衛自由與個性、追求彼岸世界、反思時間哲學等形而上主題的深刻拷問。
納博科夫堅決反對將真實生活與藝術創作等同起來。在他看來,現實主義具有誤導性。“真實是一種非常主觀的東西……你離真實越來越近,但你不可能完全達到真實,因為真實是不同階段、認識水平和底層的無限延續,因而不斷深入、永無止境。”[5]10-11納博科夫創作的藝術世界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現實,而具有現實的多樣性和多層次性。“藝術的起源便是人運用記憶和想象來調整、組建混亂的外部印象。真正的作家創造的是自己的世界,是自己對現實的美妙幻覺。因此,藝術現實永遠是一種幻覺;藝術不可能不是虛擬的,但虛擬性絕不是弱點,而恰恰是藝術的力量之所在。”[6]373他認為所有的藝術同自然界一樣都是騙局,而大作家就是魔法師,運用高超的手法和藝術的想象,諷喻和嘲弄一般意義上的現實存在。
總之,納博科夫多元的文本樣式、迷宮式的文本敘事、多層次的文本結構等特點賦予了其“小說文本本身具有文學批評的功能”的后現代元小說特征。這一寫作范式和文體策略并非去揭示現實生活,而是試圖揭示由話語構成的敘述文體的虛構性質。作者直接表達了對文本的藝術思考和質疑,玩弄小說的藝術本質和創作過程,使得敘述策略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納博科夫采用的元敘述在構筑小說幻象的同時又揭露這種幻象,使讀者意識到它遠不是現實生活的摹本,而只是作家編纂的故事。納博科夫的多部小說文本揭示了元敘述的革命性和實驗性,指出小說虛假性的本質,因此保持了小說作為虛構想象藝術的魅力,構成了顯示現實和想象之間的巨大張力。
二、納博科夫的蝴蝶世界:科學與藝術的交融
在世界文學史上,納博科夫不僅是一位優秀的文學大師,他還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博物學家和科學家。納博科夫對蝴蝶分類學的滿腔熱情與成就,讓讀者看到了他在藝術與科學兩個領域中的建樹與造詣。他創作的部分作品扉頁上都有一只蝴蝶和印有To Véra(獻給薇拉)的字樣,似乎說明他的創作靈感都來自蝴蝶和薇拉。早年的很多詩歌如《發現》、回憶錄《說吧,記憶》、短篇小說《蝶蛾研究家》,以及長篇小說《天賦》《洛麗塔》《愛達》等都涉及蝴蝶的要旨和對鱗翅目昆蟲學的敬意。“納博科夫的文學不僅巧妙且毫不做作,作為天才科學家的納博科夫在鱗翅目昆蟲學上體現了對自然界更深的理解。他在科學上的敏銳對見多識廣的讀者解讀其文學的方式產生了影響。”[14]406
納博科夫對蝴蝶的熱愛已經引起了國內外研究學者的關注。*進入21世紀,西方學者就將眼光投向納博科夫的蝴蝶分類研究領域,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2001年,約翰遜(Kurt Johnson)和科茨(Steve Coates)共同撰寫的《納博科夫的蝴蝶:文學天才的博物之旅》(Nabokov’s Blues: The Scientific Odyssey of a Literary Genius),為讀者揭示了納博科夫在蝴蝶分類研究領域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2009年,布萊克威爾(Stephen H. Blackwell)撰寫并出版了專著《筆尖與手術刀:納博科夫的藝術和科學世界》(The Quill and the Scalpel: Nabokov’s Art and the Worlds of Science)。通過探究其藝術思想中的物理學、心理學和生物學的多重維度,布萊克威爾闡釋了納博科夫的美學敏感度如何幫助其科學工作,以及其科學熱情又如何塑造、影響和滲透于其小說創作。2016年,由布萊克威爾和約翰遜共同編寫的《優雅的線條: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科學藝術》(Fine Lines: Vladimir Nabokov’s Scientific Art)以精裝形式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該著作第一部分首次全面地對納博科夫的科學研究工作進行了跨學科的描述,列出了148幅珍貴的納博科夫研究蝴蝶的圖片和構造。第二部分呈現了前沿科學家和納博科夫研究專家撰寫的10篇研究論文,闡釋了納博科夫對進化生物學的預言性貢獻,同時為其獨特的藝術想象力和創造力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某種意義上說,布萊克威爾嘗試理清納博科夫藝術世界和科學世界的內在聯系。他們認為納博科夫的科學活動和博物之旅對其小說美學思想具有發生學意義,[15]或是認為納博科夫的蝴蝶情結,使作品閃爍著超現實的激情,達到了寫實性與詩意性的雙重效果,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美學意蘊。[16]甚至認為作者筆下的洛麗塔是作者塑造的一只變態的蝴蝶,是文學中的一個昆蟲學試驗。[17]盡管將納博科夫的蝴蝶情結強加于其文學創作影響的做法值得商榷,但是納博科夫的蝴蝶世界是讓讀者深刻全面地了解納博科夫藝術創作的一面鏡子。實際上,他對藝術創作的獨到見解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捕蝶的科學發現中對自然敏銳的觀察力和洞察力。這種自然觀對納博科夫的藝術創作觀或文學觀具有重要的啟示,也讓讀者領略到納博科夫的科學世界與藝術世界重疊交織的別樣風景。
首先,在納博科夫看來,文學是創作。小說是虛構。[18]5小說創作的本質是虛構性。自然的騙術比大作家技法更為高超。“從簡單的因物借力進行播種繁殖的伎倆,到蝴蝶、鳥兒的各種巧妙復雜的保護色,都可以窺見大自然無窮的神機妙算。”[18]4-5因此,對于作家而言,如同大魔法師般,運用其獨特的藝術手段和技巧,一方面去敘述故事,設計棋題與制造迷宮,一方面要暴露虛構,體現互文性的元敘事策略。換言之,納博科夫作為世界公認的藝術大師,首先要歸功于其創作中高超的藝術手法、文字游戲和后現代敘事技巧等。
再者,1962年,納博科夫在接受BBC電臺采訪時重申:他對蝴蝶的興趣純屬科學性質的。而這種觀點與其創作緊密相關。在他看來,一件藝術品存在著藝術與科學之間的某種融合,即詩的精確與純科學的欣喜。[5]10納博科夫從7歲開始捕捉蝴蝶,12歲投稿《昆蟲學家》雜志,1941年發現第一個蝴蝶新種,并且創新分類方法。可以說,納博科夫將文學與博物學的深度結合做到了極致。有學者認為納博科夫給予我們的啟示是,在藝術上、在科學上有所成就,是需要一點貴族氣質的。[14]11納博科夫的貴族氣質在于無論生存境況如何,始終如一地堅持文學創作,迷戀蝴蝶與博物發現。這種堅守科學的韌性與文學創作的詩性讓他對優秀讀者提出了獨特的標準:讀書人的最佳氣質在于既富藝術味,又重科學性。[18]4-5因此,對于閱讀納博科夫作品的優秀讀者而言,一定是一個“反復讀者”,需要在其創造的藝術世界中不斷探險、發現驚奇、領悟真諦,一如納博科夫經歷多年發現蝴蝶新品種時的狂喜與快感。他說過,“我不能把發現蝴蝶的美學愉悅與知道它是什么品種的科學樂趣彼此分離”[19]。
最后,納博科夫將博物情懷與文學創作巧妙地結合起來。強調科學觀與藝術觀的和諧交融,兩者都注重對細節的關注。一方面,在納博科夫的教學生涯中,他總是設法讓學生去關注藝術作品的細節。“關于細節,關于細節如此這般地組合是怎樣產生情感的火花的,沒有它們,一本書就沒有了生命。”[5]162另一方面,從事博物學研究同樣要求精益求精、考究細節,對復雜的蝴蝶品種的鑒別與分類,離不開細節的精確。納博科夫最大的創造性在于他在科學探索和藝術創作中體驗樂趣和愉悅,發現了一種深層次的審美快感。在博伊德看來,對于一個作家的成長歷程,他是在探索更為有力的方式,以便將他在昆蟲學中發現的快樂傳給他的小說,那是特殊性的愉悅,是發現的驚喜,是神秘的直覺,是愉快的騙術。[20]102
總之,納博科夫作為藝術家和科學家的雙重身份,使得其藝術創作具有科學和藝術的重疊特性。這來自納博科夫想要了解世界的科學觀。“這種想要不斷了解世界的激情部分是科學性的,部分是美學的。最終藝術與科學的不可剝離成為納博科夫創造視域的核心。”[21]可以說,納博科夫豎立起一座高聳的山脊,一面是科學的激情,另一面是藝術的想象。納博科夫認為,沒有幻想就沒有科學,沒有事實就沒有藝術。他總是巧妙地回答藝術與科學的關系。納博科夫通過自己全面的博物學及鱗翅目昆蟲學知識,把他虛構的創作牢固地根植于真實的鱗翅目昆蟲學世界里。[14]409他在其文本世界中多次使用蝴蝶意象和鱗翅目典故或修辭,一方面是要引導優秀讀者去思考其作品中的藝術策略,另一方面展示了其看待世界的習慣方式。一言以蔽之,納博科夫不僅為科學世界和藝術世界豎立起一座山脊,更為兩者搭起一座橋梁,讓科學和藝術交織生輝。
三、納博科夫的“彼岸世界”:詩性與哲性的形而上主題
可以說,國內外學界對納博科夫藝術作品闡釋最多,也是無法避開的一個重要主題便是“彼岸世界”(the otherworld)主題。亞歷山大羅夫、博伊德都多次著書立說對“彼岸世界”主題進行解讀,盡管兩者的觀點不盡相同。這也引發了讀者和評論家對這一主題的多元化解讀。但是,筆者認為對“彼岸世界”的解釋不能基于自我推測,而是要根據作品自身的方式來理解這一主題。在亞歷山大羅夫看來,納博科夫的藝術創作展示的是形而上學、倫理學與美學思想的不可分割性。[22]接著他對三者分別進行了界定與區分,認為三個方面密切相關、協調統一。在這一點,他同博伊德一起為納博科夫正名,駁斥了納博科夫僅僅是一位杰出的,但卻沒有深刻內容的文體家的觀點。其實,他作品的背后潛藏著深刻的倫理與哲學內涵,是詩性與哲性的形而上主題的內在統一。讀者要真正理解“彼岸世界”主題,首先要走進納博科夫的詩歌、小說、文學講稿,甚至是他的翻譯作品,反復研讀文本,領悟“此岸”與“彼岸”的內涵與聯系,從而理解納博科夫的詩性與哲學信仰。
一方面,納博科夫的真正奧秘是他創作的抒情性或是詩性。在納博科夫的藝術創作中,他巧妙地將其詩人的氣質融入其小說創作中。從《微暗的火》中那首由約翰·謝德所作的四個詩章、共999行的優秀詩篇,到作者自認為最為出色的俄語小說《天賦》中那首作者最喜歡的俄語詩,*在《獨抒己見》中,納博科夫對這首詩解釋道:詩中有兩個人物,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站在一座橋上,河水映出落日,燕子飛掠而過,男孩轉身對女孩說:“告訴我,你會永遠記得那只燕子嗎?——不是任何一種燕子,也不是那些燕子,而是剛飛過的那只燕子?”她回答:“當然,我會記得!”說完,他倆都熱淚盈眶。“有如這位年輕的詩人使用其他詩人的形容詞和感嘆詞來描繪他的世界和感情一樣,他試圖通過走向鄰近的天堂使人聯想到有比這個世界更廣闊的空間”[20]。納博科夫在多次接受采訪中稱《斬首之邀》是他“最富夢幻性且最有詩性的小說”[5]76。《阿達》是“最為世界性的詩性小說”[5]179。在納博科夫看來,詩性是帶有想象的魔力,是帶有和諧的精致。“活躍的想象或詩性,是納博科夫全部生命活動的核心,是納博科夫藝術世界的關鍵詞。”[23]總之,納博科夫筆下無論是對主人公細膩的心理刻畫,還是對俄羅斯本土及異域風光的描繪,對童年時光的深刻記憶與詩性想象,都揭示了納博科夫創作語言上的抒情性和詩性情懷。
另一方面,納博科夫的哲性世界在于其藝術創作中的存在主義主題。“納博科夫的小說使人在無意義的世俗生活中,感受到某種真正的、崇高的東西。”[6]3891999年,由亞歷山大羅夫主編的《加蘭版納博科夫讀本》(TheGarlandCompaniontoVladimirNabokov)中收集了42位納博科夫國際研究學者的74篇評論。該書從多元化視角全面評述了納博科夫的詩歌、小說、譯作、風格及其與其他世界作家的內在關聯。其中,不乏評論者探究了納博科夫與柏格森、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普魯斯特、托爾斯泰、普希金等作家、詩人和哲學家的關系。*國內學者劉佳林在《納博科夫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中對兩者的文學風貌進行了比較分析。他認為兩位作家在文學觀念及俄羅斯文學傳統的認識方面有著一致的立場,同時都具有世界性或西歐性的藝術品貌。對雙重人格形象的描寫,對個性自由的關注,使得這兩位作家在心靈方面更加契合。詳見文獻[24]。這些研究為探究納博科夫小說創作中的哲學命題提供了學術基礎和研究視角。在《尼古拉·果戈理》一書中,納博科夫認為:“在藝術超塵絕俗的層面,文學當然不關心同情弱者或譴責強者之類的事,它注意的是人類靈魂那隱秘的深處,彼岸世界的影子仿佛無名無聲的航船的影子一樣從那里駛過。”[25]
對此,國內學者戴卓萌等將俄羅斯文學中的存在主義傳統置于俄羅斯宗教哲學思想與西方哲學思想的理論框架內,梳理和解讀了蒲寧、納博科夫等作家和白銀時代詩人作品中的存在主義特點。可以說,國內學者的獨到眼光和哲學意識為納博科夫在新時期的研究開辟出一條頗具挑戰卻值得嘗試的路徑。戴卓萌等給予納博科夫較高的評價,“20世紀20—30年代,俄羅斯文學中的存在主義意識在納博科夫的創作中達到了頂峰。納博科夫的創作玄妙難解,他因此成為俄羅斯存在主義文學中最深刻、細膩和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26]。納博科夫不僅在其早期俄語小說《眼睛》《絕望》《防守》中隱藏著存在主義思想,其后期英語創作的成熟小說《洛麗塔》《微暗的火》《阿達》等同樣具備形而上的哲學思想。
納博科夫小說中的亨伯特、普寧、金波特等人物都具有孤獨的個性,都生活在想象的世界中,這種孤僻與其周遭的世界形成了對立和沖突。他們又渴望一種方式,或是亨伯特心中洛麗塔的不朽的藝術形象,或是普寧心中對往昔生活濃重的懷舊情結,或是金波特對謝德詩篇“微暗的火”中的自傳想象,來闡釋孤獨的個體在世界中的獨立存在意義。這些流亡者的經歷反映了失去故國家園的知識分子的精神漂泊與歷險。盡管流離失所、放逐流浪,卻獨立不羈、追逐自由。“流亡的知識分子回應的不是慣常的邏輯,而是大膽無畏;代表著改變、前進,而不是固步自封。”[27]透過其筆下人物的形象映射,納博科夫把流亡中無法彌補的損失與懷舊輸入其畢生的藝術創作,在不斷認知世界與探索存在中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學風格。這種風格既帶有詩性的、阿卡狄亞式的風景想象,還具有形而上意義上的“彼岸世界”哲學命題。
四、結語:納博科夫的世界遺產
國內外學界對納博科夫的研究歷經長達百年的漫長過程,經過種種爭議與正名之后,其遺留的文學佳作與科學遺產已經具有經典性和世界性。盡管納博科夫的“俄羅斯性”和“非俄羅斯性”頗受爭議,*20世紀60—70年代,納博科夫的藝術創作享譽世界,對此俄羅斯僑民文學圈認為,納博科夫是一位“世界主義者”作家,獨立于俄羅斯文化之外,毫無“俄羅斯骨血”。這一看法將納博科夫排除在俄羅斯文學邊界之外。事實上,納博科夫運用俄語和英語創作,同時將大量的俄語作品翻譯成英語,代表作為詳細注解的四卷集譯本《葉普蓋尼·奧涅金》,向西方傳播俄羅斯文學經典與藝術成就。納博科夫在藝術創作和俄羅斯文學譯介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他作為一名世界文學大師的身份得以確立。他創造的多重世界涵蓋著現實與虛幻、科學與藝術、詩性與哲性之間多維關系的邊界主題。納博科夫的藝術世界不僅具有多元復雜的主題、意象、結構和游戲手法,還具有高度的詩性和哲性信仰。
總之,納博科夫與俄羅斯、俄羅斯文化分離相連的失去故國家園,現實與幻想之間的戲劇性關系以及“彼岸世界”的形而上等三大主題的共同核心在于現實的多樣性和多層次性。俄羅斯流亡知識分子被迫離開故國和族群,不僅要面臨與祖國“物理邊界”上的分離,還要面對語言的分離與本土文化等“內部邊界”上的剝離。盡管如此,納博科夫卻超越了物理邊界,依托其流亡體驗、世界認知和藝術想象,創造出優秀的詩歌和小說杰作、文學講稿和翻譯詩作,為世界文學和俄羅斯民族文學留下了豐厚的文學遺產。與其文學成就相比,納博科夫對其在鱗翅目昆蟲學上的貢獻始終保持低調和謙遜。盡管他在科學界的地位未能達到其文學領域的高度,但是他在生物分類學上的成就讓讀者領略到了納博科夫另一種意義上的人生。
[2]MICHAELSEN S, JOHNSON D E. Border theory: the limits of cultural politic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2.
[3]張德明.流浪的繆斯——20世紀流亡文學初探[J].外國文學評論,2002(2):54.
[4]納博科夫.說吧,記憶[M].王家湘,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
[5]NABOKOV V. Strong opinions[M].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6]阿格諾索夫.20世紀俄羅斯文學[M].凌建侯,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7]趙君.納博科夫對“文學枯竭論”的超越性思考[J].外國文學,2006(6):62.
[8]吳曉東.從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紀的小說和藝術家[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354.
[9]STARK J O. 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 Borges, Nabokov, and Barth[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4: 64.
[10]伯科維奇.劍橋美國文學史:第7卷[M].修訂版.孫宏,主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235.
[11]NABOKOV V. Nabokov: novels 1955-1962[M].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6: 291.
[12]黃藝聰.越界的敘事者——《微暗的火》中的可能世界模型[J].國外文學,2016(2):118-126.
[13]MATUZ R.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64[M]. Cambridge, UK: Cengage Gale, 1991: 330.
[14]JOHNSON K, COATES S. Nabokov’s blues: the scientific odyssey of a literary genius[M]. New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1.
[15]趙君.蝴蝶研究對納博科夫小說美學的發生學意義[J].湘潭大學學報,2011(5):130.
[16]何岳球.納博科夫的蝴蝶情結和美學意蘊[J].當代外國文學,2007(1):104.
[17]何岳球.洛麗塔:納博科夫的“變態”蝴蝶[J].外國文學研究,2008(5):118.
[18]NABOKOV V. Lectures on literature[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
[19]GOULD S J. I have landed[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1.
[20]博伊德.納博科夫傳:俄羅斯時期[M].劉佳林,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21]BLACKWELL S H. The quill and the scalpel: Nabokov’s art and the worlds of science[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2.
[22]ALEXANDROV V E. The 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M].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568.
[23]劉佳林.納博科夫的詩性世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7.
[24]劉佳林.納博科夫與陀思妥耶夫斯基[J].外國文學評論,2010(2):87-99.
[25]納博科夫.尼古拉·果戈理[M].劉佳林,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149.
[26]戴卓萌,郝斌,劉錕.俄羅斯文學之存在主義傳統[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258-259.
[27]薩義德.知識分子論[M].單德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