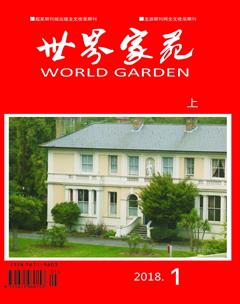淺談古代書法教育
張艤方
摘 要:古代書法教育自興起以來,每個朝代都有其自身的特色。教育目的也從最開始偏向實用性、功利性到后來的注重書家的品性及修養(yǎng)。本文通過梳理書法教育從先秦到清代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旨在廓清其發(fā)展脈絡。
關鍵詞:書法教育;方式;特點
書法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書法教育則是其發(fā)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教育的延續(xù)使得歷朝歷代涌現(xiàn)出大批杰出的書家以及傳世的書法創(chuàng)作、書學著作。
先秦時代,應該是我國有史書可考證的文化藝術趨于系統(tǒng)規(guī)范的最早時期,《周禮·大司樂》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按照史書中的記載和歷史的傳說,我們可以推測五帝時代的成均,是已知的我國最古老的學校,此時的學校重視樂教,而不是文化的教育,且并不像現(xiàn)代意義的學校具有嚴格的校規(guī)校紀,而更是像原始社會的集會場所。《周禮·保氏》中記載:“養(yǎng)國子以道,乃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shù)。”周代文獻中的“書”是指文字的讀寫。以字書為范本而展開的識字的教育和書寫的訓練,在西周的宣工年代出現(xiàn)。這一時期以文字之學為基礎的書法教育,成為了我國古代書法教育的基礎,具有深遠意義。
兩漢時期,統(tǒng)治者對字書進行了修訂和重新編寫,打破了古體并行的模式,隸書成為社會的主流,鄉(xiāng)村閭里之間廣泛分布著教育兒童讀書寫字的學習場所——“學館”、“書社”、“蒙學”等。學成之后,學生可以選擇精通經(jīng)史老師進行更高等的教育,漢代的皇室貴族更是從小就要學習文字的讀寫,《漢書》、《后漢書》中常有“善史書”的記載。每個人都把書法歸為個人應有的修養(yǎng),而不是單純意義上的書寫。東漢中后期甚至出現(xiàn)了圍繞書法而展開的家庭教育,兩代或同胞之間都是書法家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國最早的文學藝術大學——鴻都門學——也在這一時期設立,盡管在設立的目的上存在一定的不妥,但不可否認,它為社會提供了一批藝術人才,并將書法設立為獨立的學科,上升到了藝術的高度。
魏晉南北朝政治的分裂、朝代頻繁的更迭,造成了社會的動蕩,人心的震撼,卻也極大地激發(fā)了人們活躍的思維,此時期的書法更是書法史上的一顆璀璨的明珠,墓志、摩崖等遺跡亦是后世寶貴的財富。南北對立的格局不僅僅造就了書風的差異,亦造成了書體的差異。書法教育并未中斷,如西晉設立博士,教習學生行書,楷書也成為了“傳秘書,教小學”的書體,二體皆被納入了書法系統(tǒng)中。書法家往往承擔起探究歷史,編寫著作的工作,呈現(xiàn)了一批優(yōu)秀的書學著作,如王僧虔的《書論》《書賦》、庾肩吾的《書品》、陶弘景的《與梁武帝論書啟》等。
唐代無論從經(jīng)濟、政治還是文化上來說,都是我國歷史上一個空前繁榮的新時期。雕版印刷術尚未發(fā)明,需要大量的人抄寫書籍,且科舉制度的革新伴隨著書寫的要求,基于這兩方面的因素,推動了唐代書法教育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唐代國子監(jiān)設立了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六學,其中的書學就是專門培養(yǎng)書法人才的學校,學科中亦設立了書法博士等職務,受教的學生經(jīng)過考試審核有些被選拔出來授予官職,可能是為了抄寫秘籍。又如,六品以下官員的選拔在原則上有四點標準,也可稱之為“四才”——“一曰身,二曰言,三曰書,四曰判”。“書”就是指考生字的精美。可見不論是地方還是中央,書法水平的高低都是選拔人才的前提條件。顏真卿、柳公權這一類在書法史上享有高度贊譽的大家,也在這一文化繁榮的時代里誕生。
宋遼金時代政治維持艱難,與唐朝的安定繁榮大相徑庭。戰(zhàn)亂導致大量的書法范疇的優(yōu)秀作品遺失,文化出現(xiàn)間歇與中斷,加上皇室貴族對于書畫的壟斷,也導致了作品面世量少,傳播受限,缺乏書法方面的人才。朱熹理學所推崇的“存天理,滅人欲”從另一方面打擊了藝術創(chuàng)作的積極性。書法家往往要在此付出更多的時間精力。但這一時期“尚意”書風、刻帖的流行以及像蘇黃米蔡這類的大家、遼金的書法形式等,仍然對后世產生了有力的影響。
元代是民族大融合,漢文化大傳播發(fā)展的時代。以趙孟頫為代表的書法界,掀起了一股以恢復古法為宗旨的的書法教學熱潮,他們在復古的道路上,將理論與技法結合起來,整理了一批教科書。教科書分為兩種,其一是傳授技法,如《翰林要訣》、《雪庵字要》等,這些書對明代的書法教科書的編寫有著積極的影響;其二是傳授書論,匯總整理前人的書論,探索其發(fā)展軌跡和規(guī)律,如盛熙明的《法書考》就在當時受到高度評價。明代伊始,就恢復了以八股取士為核心的科舉制度,以程朱理學為標準,考試有嚴格的限定形式和規(guī)定的教材,這一舉措使當時的知識分子局限于狹小的空間,猶如精神的牢籠。而后出現(xiàn)的臺閣體也與這種思想的局促有著一定的聯(lián)系。
明代也曾設立書科,《大明會典》記載:“洪武二年,詔天下府州縣立學校,……,以禮、東、射、御、書、數(shù)、設科分教……習書依名人法帖,日五百字以上。”另外,明代武學也有下列記載:“幼官子弟日寫仿書一張,率以百字為度,有志者不拘。”可見明代全國各類型的書法教育盛極一時。
清代官方未特別設立有關書法教育的學校,但是在科舉考試中,想要取得好的成績,字體工整,熟練掌握館閣體,是先決條件。由于處于滿漢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關鍵點,所以書法水平也是對官員考核的重要標準之一。這一時期的書法藝術多依靠家庭的教育和名師授徒這兩種方式向前推進發(fā)展。書中記載:“書者,小技也,然為六藝之一,古之小學教焉,乃有用之技,人生不可缺者也”。可見書法有其必然的存在價值。學生不僅要學《四書》《五經(jīng)》一類書籍,臨習碑帖也是日常教學的一部分。供學者參考的書法論著不斷涌現(xiàn),如包世臣的《藝舟雙楫》、蔣衡的《書法論》等。
縱觀古代書法教育發(fā)展,書法不僅是教育的內容,更是選官的重要手段。主要內容是理論技法和品評等,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大量書法理論著作的產生。其中品評尤重書家之品性。在要求書法人才具備儒家要求的品德之外,還強調書法人才學識、才情等綜合修養(yǎng)等。歷史上一些著名的書法家,如王羲之、顏真卿、蘇軾等,不僅書藝高超,更是高尚人品與深厚修養(yǎng)兼?zhèn)洌虼藗涫茏鸪纾瑢笫缹W書者的影響深遠。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jīng)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