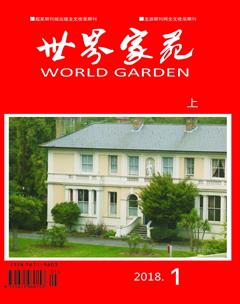試析亞太國際關系的主要瓶頸與突破
沙曉莉
摘 要:201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引進陳峰君的《亞太崛起與國際關系》論著,該書系統講解了亞太地區政治經濟的發展狀況、發展模式、地區合作等,其中講到美國組建的TPP,詳細論述了TPP的進展與障礙以及美國的戰略意圖。由此可以看出,美國的霸主地位對整個亞太地區的格局影響尤其重要,當今亞太地區國包括中國、日本、俄羅斯遠東地區和東南亞的東盟國家等國隨著經濟技術的不斷的發展,各國的崛起,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日美同盟、美俄關系、朝美關系、及中國的政治軍事大國的國際地位的提升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發展具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亞太崛起與國際關系;東亞一體化;日美同盟;
1.新時代下的國際關系
隨著冷戰結束,世界進入了“后冷戰時代”,且正面臨一種史無前例的轉變,即由過去的“兩極格局”向一個“一超多強格局”轉變,亞太地區的國際關系格局亦如此。
自一個半世紀前,東亞被強力卷入西方國際體系開始,步履蹣跚的東亞諸國開始艱難的復興路程。現代化之路的艱苦抉擇不斷困擾著東亞國家,并由此引發百年的戰亂與紛爭。直至20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復興始,至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相繼重演日本的發展歷程,東亞國家與地區上演一幕波瀾壯闊的崛起奇跡。而社會主義中國在70年代末施行改革開放政策,指引國家走上快速發展之路,同時也將東亞的經濟崛起推向一個新的高峰。
在分析50年來亞太國際關系格局問題上,東亞國家為主要分析對象,蘇聯(俄羅斯)、美國等國家為外部強權。界定“東亞國家”的概念也很重要,中國、日本、朝鮮半島及東南亞國家為主要對象。這些亞洲國家,連同大洋洲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及美洲太平洋沿岸的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共同構成了亞太國家關系網。
2. 美蘇爭霸對東亞崛起產生影響
二戰結束伊始,國際體系迅速走向美蘇兩極爭霸的格局。二戰中,伴隨著日本在東南亞的軍事勝利,英法兩國的殖民統治被徹底摧毀。戰后,重歸東南亞的英法兩國勢力也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而處于風雨飄搖的境地。此時,能夠對東亞事務產生重大影響的國家只有美蘇兩國。
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東亞政治版圖中,此時新中國建立伊始,國際地位與國際威望均不高;日本仍處于美國的軍事占領下;朝鮮半島南北方仍屬于美蘇的勢力范圍;東南亞諸國大多仍是殖民地或新近獨立國家。整體而言,此時的東亞在國際體系中只是無足輕重的從屬地位。
從另一個角度看,東亞的復興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此時的東亞在世界歷史進程中處于歷史上的最低谷,而崛起之路便從此開啟。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外部勢力的美蘇兩國深刻地影響著東亞國家的復興之路。全球冷戰格局在東亞得到涇渭分明的體現。
3.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及日美同盟使其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中堅力量
日本的經濟奇跡堪稱東亞復興的楷模。在“工業革命之路”(即科學技術為導)和“勤勞革命之路”(即勞力密集型)的有機融合下,日本經濟自60年代獲得高速發展。而緊隨其后的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等其他東南亞國家,也采用此發展模式。作為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非西方地區,或許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為現代化理論提供了有別于西方資本主義之路的新范式。
日本迅速崛起為一個經濟超級巨人,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力量一極。至少在經濟層面顯示日本開始參與分割美蘇的亞太蛋糕。至于日本何時成為一個真正的亞洲大國,應是80年代中曾根康弘執政時期。82年至87年中曾根執政5年間,是日本內政外交的一個分水嶺。此時的日本成功走過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過渡向平穩發展;政治及外交上開始明確提出自主的要求,也明確提出“政治大國”的建設目標。另外,美國在亞太地區實施“離岸平衡”戰略,同盟是其戰略實施的重要依托。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丹尼爾.拉塞爾于2015年1月26日在泰國朱拉隆功大學的講話中指出:“美國的聯盟和安全伙伴關系不是20世紀的遺產,而是21世紀的投資......”美國繼續強化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澳大利亞、等盟友的合作,并加強與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伙伴的合作。美國的亞太雙邊同盟體系逐漸形成多邊互動頻繁的伙伴關系網絡。日本在美國再平衡戰略中占據重要戰略,其是美國亞洲戰略的基石。總體而言,綜合國力以及國際威望的持續積累使得日本以“大國”的身份介入亞太政治版圖。
4.中國的復興之路及政治軍事大國地位的提升
中國的崛起,在東亞范圍內應是一個特例。其他東亞國家或地區都是由經濟復興邁向國家崛起。而中國卻最先獲得政治軍事大國地位,這是與中國建國后嚴酷的國際環境及冷戰形勢在東亞的表征所決定的。
新中國建立之初,世界輿論認為中國不過是蘇聯的又一個小兄弟,是蘇聯在東亞的代言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關系開始惡化。中國的發展進入最艱難的十年,至70年代,中國周邊環境開始緩和,此時的中國也邁入“大國”的行列,成為亞太地區力量的重要一極。
沒有經濟的崛起,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偉大復興。70年代末,中國施行改革開放,在長達2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中國走向一條經濟復興之路,東亞力量版圖隨之重新書寫。如今,中日兩國成為影響亞太事務的核心國家。
5.俄羅斯遠東地區發展目標需與亞太地區國家建立緊密聯系
對“東亞復興語境中的亞太國際關系格局”這個問題,美蘇(俄)兩國被看作外來的強大勢力。在亞太國際關系中,絕不能忽略這兩個外部勢力。美蘇冷戰格局深刻塑造亞太地區數十年來的國際關系。蘇聯,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介入東亞以來,成為影響該地區最重要的兩個國家之一。蘇聯的興亡史也伴隨著東亞地區不斷的局部戰火硝煙。難逃“盛極必衰”天則的蘇聯灰飛煙滅,留下一個虛弱的俄羅斯。而現如今的俄羅斯能夠在東亞發揮多么大的影響。或許,石油、天然氣能夠帶來更多的美元。將來的俄羅斯能否重現昔日蘇聯的輝煌?用歐洲人的說法,俄羅斯從來不按常理出牌。或許,俄羅斯是未來亞太國際關系格局的一個重大變數。俄羅斯在太平洋方向除遠東開發的國內議程之外,還包括融入亞太經濟的國際議程,這一內一外的兩項議程是俄羅斯太平洋戰略中的一組雙向維度。俄羅斯多年在亞太地區處在“邊緣化-被邊緣化”的地位,加強與亞太各國的聯系,尤其烏克蘭危機爆發后,亞太地區在俄羅斯外交中的地位被推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俄羅斯也加強了與非西方國家的關系,在這其中,推動中俄更緊密的合作仍是俄羅斯的首要目標。
6.美國的亞太戰略
50年來,美國始終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力量。冷戰時期,日美同盟將遏制所謂的共產主義威脅作為其介入東南亞地區安全事務的主要目標;冷戰后,日美兩國試圖以日美同盟為框架應對亞太地區沖突和中國的崛起,因而研究日美同盟對東南亞這一我國周邊安全關鍵地區的影響,對維護我國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為判斷21世紀初期日美同盟在亞太安全事務中的功能提供了獨特的觀察視角。隨著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日美兩國的共同威脅消失,日美同盟陷入何去何從的“漂流”狀態,而兩國關系在東南亞表現出以競爭性為主、競爭與合作并存的兩面性。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美國的亞太戰略都不會有大變化,東北亞戰略及東南亞戰略仍將是美國亞太地區最重要的戰略支點。總而言之,美國是影響亞太國際關系格局的最重要的國家。
7. 東亞一體化促進和平與穩定
東亞一體化問題的討論一度被熱議,東盟也被歐美國家標榜為“一體化”的樣板。東南亞國家因“東盟”的建立也升格為亞太地區的重要力量之一。將“東盟”看作亞太的“一強”或“一極”。
作為“一極”,并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合作就可以成就。東盟在政治、軍事以及對外政策等方面的合作任重道遠。在地區一體化進程中,歐盟就是一個不可復制的獨特現象。
東盟不能成為“一極”最重要一點在于它在國際事務中的自主性值得商榷。東南亞諸國自獨立,數十年來苦苦追尋的不過是能在大國的夾縫中求得自主生存。但它們往往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大國爭霸的權力游戲。這或許就是小國政治的悲劇。因馬六甲海峽戰略地位以及東南亞特殊的地緣政治重要性,美國一直將東南亞當作其亞太戰略最重要的兩個支點之一。東盟作為地區組織的松散本質更消釋了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強大勢力的身份存在。無論如何,東盟的國際地位仍有較大的提高空間,需看它是否能將東盟十國的力量更好地整合到國際事務的對話中去。
8.結語
整體而言,50年來的亞太國際關系格局是一個由“美蘇爭霸”的冷戰體系走向一個“一超多強”的后冷戰時代,也是一個不斷走向“全球化”的過程。在這樣的格局中,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發揮著主導作用。俄羅斯作為蘇聯的遺產,昨日的輝煌已成明日黃花,未來之路尚待國力恢復之時。東盟是一個由中小國家組成的地區組織,想在亞太事務中掌握更大的主動權,勢必需要從內部整合入手。
在全球化時代,亞太的國際關系走向如何,很難定論。“全球化”絕不是“全球資本主義化”或“資本主義全球化”,更不是“美國化”。無論東亞的未來發展如何,這一復興過程都是值得繼續思考的因素。
亞太關系的主線是以美國為首的陣營,以中國等五國為主的金磚四國,及以東南亞國家為主的東盟,三者之間正在演繹著當代版的三國演繹,東亞始終是主角。
參考文獻
[1]張潔 《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評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第40頁
[2]徐萬勝 《冷戰后的日美同盟與中國周邊安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187-188頁
[3]肖輝忠 /韓冬濤《俄羅斯海洋戰略研究》,時事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第257-259頁
(作者身份證號碼:411023199106263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