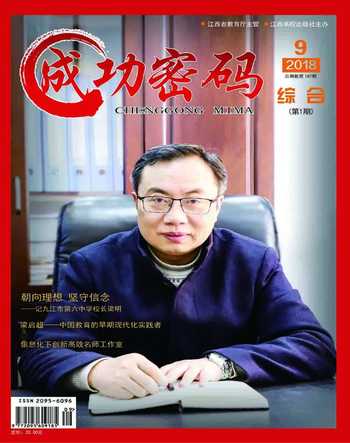天下三大行書
李澤華
書法史上公認最好的行書作品,是王羲之的《蘭亭序》、顏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和蘇軾的《黃州寒食帖》,被稱為“天下三大行書”,乃學習行書的法帖。
或許當下人有所不知,這三件作品,其實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作品,而是文稿—— 一篇是序文、一篇是祭文、一篇是詩作,而且都是草稿,字里行間皆存在刪改補漏之處,有些還不少。草稿,居然成就極品,難道是對書法的諷刺?
當然不是。草稿是即興之作,一氣呵成的。也緣于此,書家并無亂七八糟的功利色彩。內心無負擔,故能意隨筆走、筆隨意轉,筆法與情意在無意識狀態下達到高度融合的境地,也就具有了淋漓盡致的生命氣息。書家的本真性靈,自然而然抒發其間。
在觀感上,媲美“天下三大行書”的作品比比皆是。但在抒寫真性情上,估計出其右者鮮矣。可以推想,雖同為書法精品,很多是經專業書家精心構制的,幾乎毫無瑕疵。但就是這毫無瑕疵的精品,似乎缺了些什么。對,就是書寫的現場感,書寫時率真性情的噴薄。專業書家往往把作品當成作品來經營,而“三大行書”的作者王、顏、蘇把作品當成生命來揮灑。
《蘭亭序》流傳至今,但據史料記載,王羲之并非有意寫來流傳的,只是酒后微醺時的信手之作。可以想象,正因為酒后微醺,恰是身心最放松之時,書寫也就沒有顧慮和妨礙。這篇草稿,是諸多詩作的序文,記述王羲之本人與一群名士在會稽山陰的蘭亭“修禊”,實則飲酒賦詩的情景(就像當下作協組織的文學采風活動),作品有率真的寫實場景,有真切的人生感悟。
《祭侄季明文稿》(也稱《祭侄文稿》)的誕生,有其歷史大背景:一說安史之亂時,顏真卿與其兄顏杲卿、堂侄顏季明并肩作戰,抵抗叛軍,效忠王室,因援軍不救,顏杲卿與子顏季明先后罹難,遂成文;二傳是顏真卿的侄子在戰亂中被殺害,首級被呈到他面前,哀郁之情迸發,作文祭之。不管怎樣,《祭侄文稿》是悲憤之作。也由于哀筆而成,文稿中多有刪改涂抹。這些“敗筆”,恰恰是顏真卿真情實感的證據。藝術家在遭受情感極限考驗時,往往成就神作。
《黃州寒食帖》(也稱《寒食帖》),可謂蘇軾沉浮人生的藝術化總結。黃州,是蘇軾被貶之所,此間,乳母王氏過世,自己仍待罪于邊陲,正常生計幾成問題,心中悲苦不言而喻。此時的蘇軾,根本非我們印象中曠達的大文豪形象(事實上在寫《寒食帖》之前,蘇軾是意氣風發的,甚至是不無自負的,是端有姿態的)。后人對其稱道的灑脫泰然,多半是《寒食帖》之后的人生。經歷“烏臺詩案”等系列挫折的蘇軾,看清了上層社會,也結識了草根階層,他這才頓悟了,豁達了,《寒食帖》就是對復雜心情的一種收拾。因此,此帖的信息量十分豐富,其間的生命能量能不充盈么?若能欣賞進去,似乎每個字就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或行吟,或感喟,或在堅韌地面對人生。
藝術,雖離不開技術的充分準備,但技術之后,藝術就是性情的表達了。所以真正的藝術就是生命,是鮮活生命的極致呈現。名家在情感極限時一揮而就的草稿,就是鮮活的生命,是性情的搖滾,怎能不撼動人心?怎能不成就絕美?
天下三大行書,不禁令我想起人的一生,何嘗不是草稿,即興的,一次性的?正因于此,生命才可貴,生命也成其生命。否則猶如商品,做壞了做次了可再造一批,可無限制復制,也就沒多少價值和意義了。
(作者單位:江西省南昌十中高三〈10〉班 指導老師:鐘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