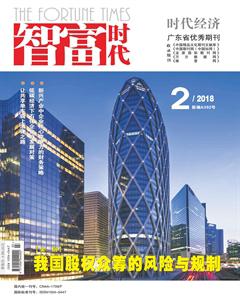孟子識人用人思想淺析
劉穎
【摘 要】孔子、孟子雖同為屬儒學,是春秋時期和戰(zhàn)國時期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在識人用人方面固然有許多相同看法,但由于時代背景的差異,他們的識人用人思想又有很多自己的特色。本文分別淺析孔子、孟子的識人用人思想特色,并進行簡單比較。
【關鍵詞】孟子;識人用人思想;人才觀
先秦時期,儒家思想作為主導流派,對社會和文化的各方面都提出的自己的思想。其代表人物,孟子在識人用人思想方面可謂是“先驅”。
一、孟子識人用人之道
孟子把人才分為“圣人”“君子”“大人”“士”。對于圣人,孟子說:“圣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圣人是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對于君子,孟子說;“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君子居心于仁,居心于禮。孟子區(qū)分出,“大人”和“小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而孟子提出還全面的提出“士”的觀念“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士最基本的要求是在窮困時不失去仁義,顯達時不背離道德。
孔子不以言舉人,而孟子則提出用眼神來分辨一個人的善惡,他在《離婁》下中說:“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朱熹解釋說;“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心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①用眼睛來識人是孟子在先秦儒家觀點中比較獨特的一個觀點。
孟子在發(fā)現(xiàn)人才方面還要求要深入底層求賢,這里的底層不僅是指進一步打破階級觀念從當時的所謂下層人民中求得賢良,還指在求賢才的事情上要廣泛聽取民眾的意見。首先要不問職業(yè)的從各個階層里發(fā)現(xiàn)人才,孟子舉例道“舜發(fā)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舜帝、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都是從平民中被舉薦,但卻最終都被證明是賢才的人。其次孟子還認為在選取人才時還要充分考慮人民的建議,把下層人民的意見作為重要參考。正如《孟子·離婁上》所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再聯(lián)系孟子的“民貴君輕”的思想,我們可以的、看出孟子識人用人思想的先進性,即重視民意。
在獲得賢才后如何對待人才也是孟子關心的問題。孟子以堯舜為例:“堯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yǎng)舜于畎畝之中,后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朱熹注;“能養(yǎng)能句,悅賢之至也。”②對于人才不只要明白怎樣招攬他們,還要懂得留住他們。善待他們,生活生給予無微不至的關心,才能真正的讓人才為你發(fā)揮充分的潛力。孟子還具體舉了商湯與伊尹、齊桓公與管仲的例子,說明這些成功的君主都是主動放下尊貴的架子而啟用賢才,甚至拜賢才為老師。正如孟子所說“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霸。”
另外孟子還注重苦難對人才的磨礪:“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天要把重大的責任交給某人,就一定先使他經受內心痛苦,筋骨勞累,經受饑餓以致體膚消瘦,讓他做事受到阻撓干擾,用這些來鍛煉他的意志,使他心靈受到震撼,使他的性格堅忍不拔,這樣增長他原來所不具備的才能。孟子提出“浩然正氣”的概念,他認為浩然之氣是人才必須擁有的,是人才成就事業(yè)的強大支撐。“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yǎng)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浩然之氣的培養(yǎng)對于人才的成長非常重要。孟子也提出過“專心”和“恒心”的重要性。孟子在《盡心下》中說“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即使有天下最容易生長的植物,曬它一天,又涼它十天,沒有能夠長大的。比喻做事一日勤,十日怠,沒有恒心,是不會成功的。他還說:“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努力到一定程度,要靠恒心來進行最后的堅持,能否再堅持一下將決定自己的成功或失敗。
以上孟子識人用人思想幾乎全部繼承孔子,卻又與孔子有所不同。 二、孟子對孔子識人用人之道的擴展深化
第一,在打破人才階級的限制方面,孟子在相比較孔子更近一步。因為孟子提倡人性本善,固人皆可以為堯舜。孔子求賢的眼光還基本停留在統(tǒng)治階級的范圍內,他區(qū)分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認為“小人“是不可能有仁德,一輩子只可能是被統(tǒng)治者。孟子則主張主動關心蘊藏在社會下層的賢才。他以舜帝、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等為例,說明在商販工人,奴仆甚至刑徒中都有值得注意的賢才,只是需要我們去發(fā)覺。
第二,孟子在人才的使用范圍上較之孔子,有所擴大。孔子在識人用人思想闡述時,舉得例子大多是如管仲,自產,比干等大夫,對于君主是否符合賢才的標準,他盡量采取了回避的態(tài)度。孟子則不一樣,他主張“欲為君,盡君道”貴為國君、天子也必須是他所認定的賢才。身為君主,必須有施行施行“仁政”的能力。所以他和齊宣王有以下對話。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一個不符合孟子人才標準的國君,與“殘賊”并沒有什么區(qū)別,百姓可以推倒他另換國君。
第三,由于孟子民本思想決定了孟子在識人用人上比孔子更加注重民意。孔子制定賢才的標準,而孟子則把人民提上來做為標準的掌握者。標準的判定與制定也應廣泛征求民意。孟子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選拔人才時孟子提倡要擴大評議的范圍,把百姓的意見納入選拔規(guī)范,這樣能夠提高選拔的公信力。
孔子與孟子同作為先秦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思想的默契性是不言而喻的,當然識人用人思想也不會例外。兩人對人才的發(fā)現(xiàn)與使用都高度重視。孔子說;“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于斯為盛。”對與不重視人才的人孔子批判道“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孟子也說“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用不用賢才是決定君主成功與否的原因,孟子也明確“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就是說執(zhí)政者只有尊重人才,重視人才的使用,天下的人才便愿意聽從召喚,這個自然而然便能“無敵于天下”。但是倆人畢竟處于不同的社會階段,他們的思想不可避免的烙上了所處社會的印記,所以不管是用人范圍和用人標準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不過已經于兩千多年前就開始識人用人思想的探究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并且對現(xiàn)在社會仍有很大借鑒意義。
注釋:
①②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5:276,283.
【參考文獻】
[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5.
[2]劉寶楠.論語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90.
[3]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60.
[4]焦偱.孟子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7.
[5]朱耀廷.諸子百家論人才[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