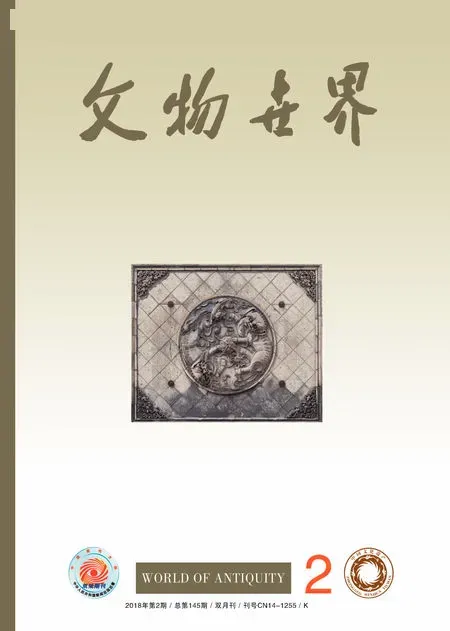古代“七事”小考
□馬楠
(作者工作單位:廣州市荔灣區文物管理所)
引言
“事”,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云:“事,職也。”[1]可見,其本義為職務。傳承至今,“事”已經泛指人類日常生活中的作為和事物。在唐代以來的歷史文獻或文學作品中,曾出現有“七事”“六事”“五事”“三事”等詞匯(以“七事”“五事”最常見),通常用于描述人的裝束,顯然與古人的裝扮佩飾有關。近年來,在一些唐宋元明清時期的墓葬中,考古出土了一類物件,或七或五件組合形制,這些物品應當就是文獻記載的“七事”“五事”。近期筆者看到收藏于博物館的一些清代飾件,也與上述物品極為相似。基于此,筆者在收集文獻和考古材料的基礎上,對古代“七事”“五事”的源流和功能流變等進行粗淺探討,求教于方家。
一、文獻所載的“七事”
目前所知,“七事”一詞最早見于《舊唐書·輿服志》中關于官員裝束制度的記載:“上元元年八月又制,一品已下帶手巾、算袋,仍佩刀子、礪石,武官欲帶者聽之。景云中又制,令依上元故事,一品已下帶手巾、算袋,其刀子、礪石等許不佩。武官五品已上佩(韋占)韘七事,七謂佩刀、刀子、礪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等也。至開元初復罷之。”[2]
《冊府元龜》卷六十載:“睿宗景云二年四月,制:九品已上一品已下,文官依上元故事,帶手巾筭袋,武官咸帶七事韋占韘並足。”[3]
《新唐書》卷三十四載:“高宗嘗內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帶、皂羅折上巾,具紛礪七事,歌舞于帝前。帝與武后笑曰:‘女子不可為武官,何為此裝束?’近服妖也。”[4]同書第二十四卷記載:“初,職事官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手巾、算袋、佩刀、礪石。至睿宗時,罷佩刀、礪石,而武官五品以上佩韘七事,佩刀、刀子、礪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是也。”[5]
通過上述文獻可知,“七事”即隨身佩掛的七種實用性物件,是武官的裝束規范和等級象征,它至少于初唐高宗時代出現,但遵用時間不長,在開元初年就被罷棄。
之后,“七事”雖然退出了官服體系,但依然保留了身份和榮譽的象征意義,成為朝廷對外藩賞賜的“寶物”。
明代丘濬編纂的《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收錄張九齡于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撰擬的“敕識匿國王書”一節有“今授卿將軍,賜物二百匹,錦袍金鈿帶七事,已下節級亦有衣物,各宜領取”的記載[6]。
《冊府元龜》卷九七五記載天寶五年(746年)至十四年(755年)朝廷對前來朝貢的外國來使的賞賜情況,“七事”與同是貴重之物的“錦袍”(綾袍、紫袍)“金(鈿)帶”“魚袋”等并列,屢屢出現在授賜之物中:
(天寶)五載十月癸巳三葛邏祿伽葉護頓阿波移健啜遣使朝貢授葉護為左武衛大將軍員外置依舊在蕃其使賜二色綾袍金帶七事放還蕃。
七載八月庚戍悒怛國遣使朝貢授將軍賜二色綾袍金帶魚袋七事放還蕃。
十月丁卯九姓勃曳固大毗伽都督默每等十人來朝并授特進賜錦袍金鈿帶魚袋七事放還蕃。
十四載三月丁卯ヌ拔國遣其王子自會羅來朝授右武衛員外中郎將賜紫袍金帶魚袋七事留宿衛康國王石國副王并遣使朝貢各授折沖都尉賜紫袍金帶魚袋七事放還蕃[7]。
筆者沒有查閱到宋代文獻有關“七事”的記載。元至清代的文獻和文學作品中,除了“七事”,還出現了“五事”“四事”的記述。
元末明初流行于朝鮮,供朝鮮人學習漢語的教科書《老乞大》中,有這樣的記述:“我引著恁買些零碎行貨。紅纓一百斤。……雜使刀子一十把。割紙細刀子一十把。裙刀子一十把。五事兒十副。”[8]這本書以口語對話的形式記錄朝鮮商人來到中國之后的道路見聞及住宿飲食、買賣貨物等日常生活,形象地反映了元、明兩代的社會生活和風俗民情,從引文中可以看出,作為日常生活用品的“五事兒”在民間廣泛流行。
明代顧起元撰的《客座贅語》卷四“女飾”篇:“以金珠玉雜治為百物形,上有山云題、若花題,下長索貫諸器物,系而垂之,或在胸曰墜領,或系于裾之要曰七事。”[9]清晰地描述了明代七事的形制、材質,且與另一種掛飾“墜領”做了使用和叫法上的區分,這時的“七事”已成為女子衫前的裝飾之物。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貪官嚴嵩被抄家后,根據其家產羅列成冊的《天水冰山錄》“墜領墜胸事件”一章中有“金鳳牡丹七事一掛、金素七事一掛、金廂寶玉七事一掛、金廂寶玉四事一掛、金廂石榴事件一吊”[10]的記錄,“事”的材質、紋飾至此更為豐富。
《金瓶梅》第九十一回描寫孟玉樓改嫁李衙內之日“戴著金梁冠兒,插著滿頭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系金鑲瑪瑙帶,玎珰七事”[11],明末清初的長篇小說《醒世姻緣傳》第七十一回描寫:“連那銅行的生意絕無指望,先把家中首飾,童奶奶的走珠箍兒,半銅半銀的禁步七事,墜領挑排簪環戒指,賠在那幾只象的肚里,顯也不顯一顯。”[12]可見,明清時期的“七事”都是指系在衣前的七物組合掛飾。
綜上可知,“七事”從最初唐代高級武官隨身佩掛的七種物品的統稱,經過發展、演變,成為一種專指佩掛于衫前腰間,懸掛有七種器物的組合式掛飾的專有稱謂,根據器物數量的多少衍生出“五事”、“四事”等。通過文獻,我們初步推斷佩飾“七事”、“五事”的形制、材質以及樣式,但七件或五件器物究竟是何物,除唐七事有確指外,其他則無從得知。根據元末《老乞大》所述其為“零碎行物”以及《客座贅語》《醒世姻緣傳》作為女性首飾的描述來看,七事應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內容,這就需要結合考古資料和流存實物資料加以分析。
二、考古發現和傳世有關“事”的實物資料
文獻所載“七事”“五事”不少,但我們對于其具體所指還沒有太明確的概念。近年來,在全國各地考古發現了一批唐代以來的實物資料,通過對比分析,可以確認它們就是古代文獻記載的諸“事”,這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古代“事”的形制、材質、功能及其演變。
目前所見最早的實物“事”例,是唐代法門寺地宮出土的蹀躞十二事帶[13]。銅制,腰鏈式,鏈殘長62.8厘米,剪刀、鑷子、勺、罐、耳勺、牙簽、燧、鐫、魚等11件器物(缺一器)并系于鏈上,鏈一端設一彎鉤,可與另一鏈端扣合,圍系佩掛(圖一)。
遼之后出土的六事、七事,則不再見腰鏈形式,而改為由單條鏈子垂掛一束口的牌子,其下墜系數條鏈繩將幾件小工具或小物件串聯、系合為一副,根據垂掛物件的數量確定為幾事。

圖一 唐代銅蹀躞十二事帶

圖二 遼代玉六事

圖三 金代銀六事

圖四 元代銀五事

圖五 明代金七事

圖六 明代金四事
遼陳國公主駙馬合葬墓出土的玉六事[14],上部為一片透雕玉蓮瓣,蓮瓣邊緣垂掛六根金鏈,下系剪、觽、銼、刀、錐和勺。其中,剪為交股,觽、銼、刀、錐、勺為竹節柄,墜件長5.8~8.2厘米,金鏈長4.5~5厘米(圖二)。
河北遷安市開發區金代墓葬出土的銀六事[15],一端單環另一端雙環連套,其中一環鏈系小剪一把,長7.2厘米,另一環分別以五條鏈系圓盒,直徑2.8厘米;提梁壺,壺高2.1厘米;四瓣瓜棱形壺,高3厘米;鑷長6.3厘米;剪刀長5.5厘米。其中,剪刀為雙股,與現代剪一致(圖三)。
湖南株洲攸縣丫江橋元代窖藏的銀五事[16],上部是一枚荷葉形銀片,葉片下緣以環鏈墜五事:剪刀、鑷子、荷包、圓盒、蓋罐,荷包上飾叢菊瑞兔圖案(圖四)。
北京明萬貴夫婦墓出土的金七事[17],華麗精致。在一鴛鴦荷葉片下墜著七根金鏈,分別系錐、劍、剪刀、花鳥紋荷包與小盒、小罐、小瓶(圖五)。
江蘇南京市明黔國公沐睿墓出土的金四事[18],包括耳挖、牙剔、鑷子和鼻煙棒,由一金管收納,管長8厘米,一條金鏈將其與四事連接拴掛,可于管內外自由伸縮,鏈上并系一半圓形小蓋,用于封閉底口(圖六)。此件四事各物件不外露懸掛,用時抽出,不用時入管,既方便又科學。
浙江臨海張家渡明王士琦墓出土的金二事與上述金四事有異曲同工之妙,金管雕飾更為考究[19],為一仕女造型,身著衫裙,盤髻插簪,手捧連葉壽桃,高6.9厘米,管內中空,金鏈一頭拴小圓環,一頭系掛牙簽和耳挖,并連壽桃形塞。拉伸頭頂處金鏈,耳挖等物便收入管中,壽桃形塞塞住腳端,構思十分精巧(圖七)。

圖七 明代金二事
除了考古發現,還有一些傳世的類似物件被博物館或民間藏家收藏,其時代多為清代至民國初期,如廣東佛山市博物館收藏的銀五事(圖八),廣州市荔灣區博物館收藏的銀鑲玉五事等。這一時期的事多見銀質,個別鑲玉,形制基本統一,單股或雙股銀鏈下墜一或兩層銀片,下層銀片通過小環垂掛三、五、七條銀鏈,銀鏈下掛各物件,形成具有層次的垂墜排列。銀片的錘鍛鏤刻形制豐富,可見蝴蝶形、雙魚形、花籃形、寶盒形等,雕琢精美、雅致。

圖八 銀五事(佛山市博物館藏)
三、“事”的質地與形制組合變化
早在先秦時期,先民就已隨身佩帶一些實用的小物件,同時也有裝飾的功能。《詩經》《禮記》均有記載。“七事”“五事”的掛件,多數也是由先秦時期的實用物件演化而來,在發展流變的過程中,又會在形制、材質等方面表現出多樣化特征,逐漸形成比較固定的組合和專有的名稱,反映出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審美觀念。
(一)形制
總體來看,事是一種以鏈條串聯、系掛數量不一的小物件用以隨身佩帶、使用的佩飾,根據物件數量有七事、五事、三事等的區別,其主要構件包括勾環、鏈條、連接件(片)、掛件等,鏈條上至中部通常設有一至二個或三個連接件,它們形狀各異,裝飾豐富,有片狀、有管形,既起到串聯、束口的作用,又可將整件事分層,最下部拴系鏈條懸掛小物件,使整件器物雖呈長條狀懸掛,但看起來層次豐富,和諧美觀。
最早為特定等級官員所佩的唐代七事,是通過腰帶環繩掛系佩帶。宋代沈括著《夢溪筆談》記載:“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靿靴,有蹀躞帶,皆胡服也。……帶衣所垂蹀躞,蓋欲佩帶弓箭、帉帨、算囊、刀礪之類。自后雖去蹀躞,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蹀躞,如馬靿根,即今之帶銙也。”[21]
之后,隨著使用范圍的擴大,其逐漸擺脫與腰環的搭配使用,演變為由一條鏈繩和束口自上而下總串各部件的組合形制,可系掛于胸前、腰間,使用更為方便靈活。
(二)材質
從歷史文獻和考古實物資料看,唐代開元初年之前,七事主要為武官所佩的實用之物,根據其佩刀、刀子、礪石、針筒、火石等的功用,材質應為銅制、石質等;其后,七事不再用作裝束必配,作為朝廷賞賜之物的“錦袍金帶七事”,其材質發生變化。遼至明代墓葬出土的事,有玉、金和銀等不同材質。明代文獻中的“金珠玉雜治為百物形”、“金鳳牡丹”、“金廂寶玉”等說明也存在多種材質的搭配鑲嵌使用。清代以后見于博物館藏的“七事”以銀制為主,少量有玉石鑲嵌。
(三)組合變化
從《舊唐書》里的“韋占韘七事”、元《老乞大》記述的“零碎行貨”以及明代文獻、小說所指的“女飾”來看,在不同的時期或場合,“七事”有著不同的物件組合內容,且根據組合物件的數量,發展出五事、三事等。結合目前掌握的實物資料,我們可以看出,除唐代文獻確指的佩刀、刀子、礪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之外,剪刀、鑷子、食勺、罐、耳勺、剔牙、燧、刀、劍、錐、銼、勺、觽、圓盒、蓋罐、扁瓶、葫蘆、荷包、香囊等均是曾出現的物件。
文獻記載的唐七事中,契苾真、噦厥為何物,不易理解,筆者亦未能查找到確切的文獻記載,只知契苾是敕勒部落之一,隋唐時居于焉耆西北,貞觀六年(632年)歸唐。《新唐書·回鶻傳下》載“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娑川,多覽葛之南。”[22]由此推論,契苾真、噦厥應是該部族語言的音譯。馮盈之認為,契苾真是用于雕鑿的楔子,噦厥是古代用骨頭制的解繩結的錐子[23]。無論是否如此,這兩件物品和其他的刀、礪石等用途相仿,都是游牧民族掛于腰間的常備實用之物。
從唐、遼、金各出土的一件“事”來看,唐十二事(缺一事)包括剪刀、鑷子、勺、罐、耳挖、牙簽、燧等十二器;遼六事為剪、觽、銼、刀、錐和勺;金六事含一大一小兩把剪刀、鑷、小盒、蓋罐、小瓶。
元代出土的五事、六事、七事,除前朝常見的剪刀、鑷子、刀之外,瓶、盒、罐也成常物,還增加了香囊、葫蘆等小件,是人們生活日益講究和追求精致的反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金代、元代事中的剪刀形制也發生了變化,由唐代的交股變為雙股。陳巍認為,11~13世紀,中國古代剪刀的形式逐漸從交股剪刀轉變為雙股剪刀,到12世紀雙股剪刀已經成為華北地區遺址中常見的器物[24]。
明代出土的事有二事、三事、四事等更為靈活的組合,其中,耳挖、牙簽成了最常見的物件,其他還有鑷和刀等。
清末至民國初年的事常見五事、三事等,基本為耳挖、牙簽與其他鑷、刀、劍、戟等物件的組合。
四、“事”的功能演變
(一)從生活實用器到吉祥裝飾物
從唐朝七事所指之物和佩戴方式來看,七事最初為實用物品,是游牧民族隨身佩戴的防身、日用的小工具。唐朝初年,作為武官官服專屬裝束一部分,兼具實用和等級規范功能。此后,七事作為朝廷賞賜之物,逐漸成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元代,隨著其所含之物逐漸轉變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隨身用品,“七事”“五事”等開始在民間流行。明代的事漸趨裝飾功能,制作精巧、紋飾華麗,材質也出現了搭配鑲嵌使用。清至民國的傳世品以裝飾和吉祥寓意為主,束口連接片造型豐富,雕琢精細,可見花籃形、雙魚形、寶盒形等,形態美觀又寓意吉祥,系掛之物除耳挖、牙簽等仍具實用功能外,其他如刀、劍等應演變為護身辟邪的寓意功能。
(二)從男子佩掛之物到女性裝飾品
唐初,“七事”作為武官等級裝束的一部分,僅為男性佩掛,這從《新唐書》載高宗、武后笑太平公主的裝束可以看出來。此后,“事”作為身份的象征,實用功能趨弱,使用范圍開始逐步擴大,出土于遼陳國公主駙馬合葬墓的玉六事,系掛于公主腰帶間,應作為佩飾,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元代起,“事”成為日常貨物,在民間廣泛流通,使用人群更為廣泛。明代,“事”的實用性漸弱,裝飾性趨強,《客座贅語》記錄“七事”于“女飾”章節,可見,至遲從明代起,“事”主要成為了一種女性掛飾。當然,從考古發現來看,明代男性特別是上層社會的男子仍然可以佩戴“事”,裝飾制作極為考究,至于是否還有等級的體現,則有待更多的考古材料來驗證。
五、結 語
本文通過對歷史文獻的梳理、考古材料的分析,得出這樣的結論:古代的“七事”,是衣前的一種多物件組合型佩飾,這種佩飾最初發端于北方游民族隨身攜帶的實用小工具,大約在南北朝隋唐時期傳入中原,被漢文化吸收,一度成為特定官員階層的裝束規范以及身份等級的象征,經過不斷的發展、流變,衍生出“五事”、“四事”等,且形制日益豐富,使用范圍趨廣,從實用物逐漸變為裝飾品。其形制獨特,功能多樣,寓意豐富,是時代特征、使用需求、社會禮制以及不同時代先民審美觀念的具體表現。
“七事”“五事”等專用名詞的出現,反映了唐以來人們對耳挖、牙簽、剪、燧石等實用小物件組合的認識,也十分形象地表達了這類組合的形制和功用,即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七種、五種……物件。既然先民已經為這類組合取了專屬的名字,筆者認為,對于考古發現的實物材料,或傳世留存的這類物件,不妨仍以“七事”“五事”等命名,而不是簡單地以“佩飾”“裝飾品”來籠統稱謂,這樣既體現了它們的文化內涵,也讓先民植根于生活給予它們的“美名”得以傳承。
[1][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第65頁。
[2][后晉]劉昫等《舊唐書》第六冊卷四十五,中華書局,1975年。
[3][宋]王欽若等編纂《冊府元龜》(校訂本)第一冊,卷六〇,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636頁。
[4][宋]歐陽修,宋祁合撰,《新唐書》第三冊卷三十四,中華書局,1975年,第877頁。
[5][宋]歐陽修,宋祁合撰,《新唐書》第二冊卷二十四,中華書局,1975年,第529頁。
[6]轉引自盧燕新《由唐人詩文之“胡商”看西域與唐的文化交流》,《甘肅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
[7][宋]王欽若等編纂,《冊府元龜》(校訂本)第十一冊,卷九七五,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89-11290頁。
[8][韓國]鄭光主編《原本老乞大》,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65頁。
[9][明]顧啟元撰《客座贅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4頁。
[10][清]吳允嘉(述),《天水冰山錄》,商務印書館,1937年。
[11][明]蘭陵笑笑生撰《全本金瓶梅詞話》第九十一回,香港太平書局,1982年,第2719頁。
[12][清]西周生《醒世姻緣傳》,岳麓書社,2014年,第854頁。
[13]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05~207頁。
[14]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遼陳國公主駙馬合葬墓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11期。
[15]唐山市文物管理處、遷安市文物管理所《河北省遷安市開發區金代墓葬發掘清理報告》,《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
[16]揚之水《中國古代金銀首飾》,故宮出版社,2014年,第362頁。
[17]揚之水《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第二卷)》,中華書局,2011年,第 96頁。
[18]南京市博物館《江蘇南京市明黔國公沐昌祚、沐睿墓》,《南京考古資料匯編4》,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2384頁。
[19]裘樟松、王方平《王世琦世系生平及其墓葬器物》,《東方博物》2004年第2期。
[20][宋]沈括著,金良年、胡小靜譯《夢溪筆談全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頁。
[21][宋]歐陽修,宋祁合撰《新唐書》第一九冊卷二百一十七下,中華書局,1975年,第6142頁。
[22]馮盈之《中國古代腰帶文化略論》,《浙江紡織服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23]陳巍《11-13世紀中國剪刀形態的轉變及可能的外來影響》,《自然科學史研究》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