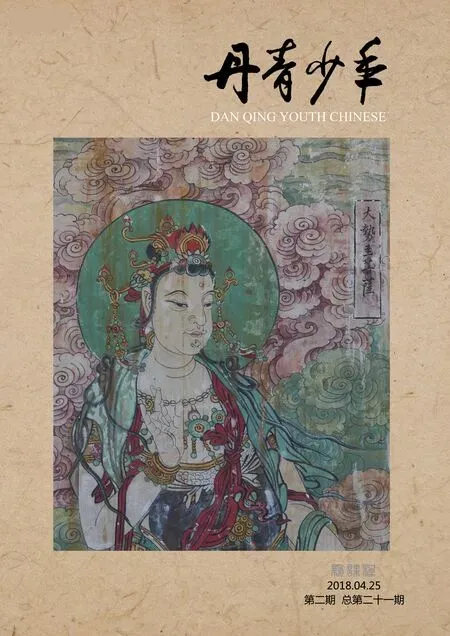戰國文字啟示
文/魏兵然
對于春秋戰國青銅器銘文,我有一種說不清楚的特別的愛好。不論何時,每當那些緘默不語的銘文展現在我眼前時,我的心靈就會受到強烈震動。真的不可思議——那些埋藏了四千年左右的青銅器銘文依然閃耀著令人炫目的異彩,漫長的歲月,非但沒有把它們泯滅,反而使它們顯得沉著有力,璀燦奪目。這些古老的銘文為什么具有如此超越時空的藝術魅力呢?這對我來說真是一個耐人尋味、值得深思的問題。
春秋以后,諸侯鑄器之風日盛,銅器富麗美觀,裝飾繁縟精致,青銅器銘文鑄制的部位逐漸由器內移到器表,文字與花紋圖案一起,成為器物裝飾美的一個組成部分,銘文筆畫均細修長,這種協調之美,強烈地刺激著人們的熱情、想象和創造力。
春秋戰國青銅器銘文非常豐富,刻款銘文逐漸流行,字形向縱長方面發展,受鳥蟲書影響,篆引曲線明顯地擺脫了仿形的功能和特點,作大幅度的擺動與組環,圖案性增強。山東出土曾國《曾姬天壺》線條圓暢,自如輕松,近于書寫狀態,非個中高手不能臻比。


戰國青銅銘文不帶有描述性,也看不出對當時生活的精確再現,只能看到有“意味的形式”,此時代銘文給我最強烈的印象就是體現濃郁地區性的具有的裝飾情趣的線條,如戰國時期銘器韓國驫羌鐘銘文,此器銘文以陰文界線安置文字,突出此器的花重曲雅,以纖細流暢的線條來表現銘文的瑰麗,銘文配上鈕部、鼓部的精致紋飾和鉦部粗獷的乳釘相映結合,形成此鐘雄偉奇麗的造型風格,具有一種巋然不動的霸氣,充盈有著剛健、凝重、古拙,甚至蠻勇的氣質。戰國青銅器銘文所顯示出來的霸悍之氣是其他藝術所無法替代的,銘文所特有的堅實、少言、寧靜意態,對當代書法藝術創作也是極為重要的因素,我以為缺少了這種強烈的崇高的寧靜,書法藝術就無法達到高尚的境界。

戰國銅器上那種具有象形意味的理念巧妙地嵌入字形之中,或只取其一部分,或使字形的線條屈曲蜿蜒而象征地摹擬蟲蛇的形神動態,或把多種形式撮合于一字一器,千萬變化,不一而足,青銅器銘文的各種形式的造型,不是摹仿客觀的自然,而是表現“區域特征文化”的自然,是極富隨機性和主體自覺化的結果,它往往表現為各種變異的形象,這是戰國青銅銘文藝術的魅力所在之一。青銅銘文那奇怪的“變形”是對外部世界大膽的詮釋,再重新組合為一個奇異瑰麗的魔幻世界。這些單純簡練的字形,無所謂抽象,也無所謂具象,那只是豐富多彩的大自然的濃縮凝聚。

戰國青銅銘文中表現出的異乎尋常的藝術想像力和藝術表現手法,可作為當代書法藝術創作的一把鑰匙。春秋晚期蔡國出土的蔡侯盤銘文,文字與器表花紋圖案,浮雕裝飾相結合,構成統一的形式,成為器物美的組成部分。銘文因“形式”采用瘦硬勻細的筆畫,修長秀美的體勢,結構疏密有致,行款疏朗寬松,每字都有一筆或幾筆豎畫,夸張得很長,而將其他筆畫合理密集,使多數字的結構上緊下松,又由于長筆畫的垂直與對稱,使得字字修長而穩定,有雄強之風,傲岸之氣,整體的書法布局十分嚴整規矩,出入有方,凜凜不可侵犯,這種單純但整體的力量更加強了莊重威嚴的意味,顯示豪壯厚重的春秋戰國時代的審美趣味,契合他們按照表現感覺去組合、表達情緒的造型觀念。


在藝術作品中,節奏是通過空間表現的。春秋戰國青銅器銘文的又一特點,是在那相互的字形組合里構成的豐富的節奏美。如《曾侯乙編鐘》銘文形體堂皇妍麗,結字修長,在較多的文字結構上顯得上密下疏,并能在綿密的文字排列中達到氣息相通的效果,其筆畫飄逸瀟灑,亭亭玉立,結體婉靜遒美,鋒穎秀挺,運筆純熟而顯得結構自然,蓄意曲逆的線條中給人一種在靜中有飄飄欲起的動感,戰國銘文那種共有的嚴謹、大氣、活潑、寓動于靜的視覺效果,直曲、方圓的對比,從整體上看,都表現了很強的節奏,其空間安排的完美,令人叫絕,雖然那時人們是憑直覺和敏感或出于實用目的來安排這種形式節奏關系,但從這種形式關系中生發出來的藝術意趣,給了我們當今書法創作以巨大的啟示。




戰國銘文另一種極有吸引力的表現形式是那沉著有力的線條,這種線條完全是風格化、規范化的。如河北平山出土戰國《中山王方壺》,銘文排列整齊,修長的線體顯得優美纖麗,加上極為成熟的雕刻技巧,使人觀后有字字珠璣之感。我認為戰國青銅器銘文線條不是一般的圖案花紋的形式美,尤見生命力和力量感,如齊《陳曼簠》銘文的書法,就像齊桓稱霸一樣,不免讓人觀后激動、欽敬、崇拜。我把這種線稱之為戰國“青銅線”,我運用這種獨特的“青銅線”進行創作,使作品回避量感和體塊感,把作品濃縮成線的形體,使作品獲得一種精筋的元氣,這種墨線形式比墨塊狀形式更加奪目,空間更加奇特,節奏更加豐富。因為線條是從自然對象中抽象出來,省去了多余的瑣碎的東西,能使作品的形象更加概括傳神,一目了然,突出了作品的主題。
戰國青銅器銘文作品一般運用對稱的格式,世世代代人們總是在創造秩序。我在創作戰國銘文風格的書法作品時努力將這種美的感受注入進去,使之更簡化有序,從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知覺和理解的感受性。
在書法創作時,我的藝術思維方式和藝術表現形式是從豐富多彩的戰國青銅器銘文中建構起來的,我的書法藝術與戰國銘文結下了不解之緣。傳統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不僅僅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戰國青銅器銘文所表現的藝術形式是植根于中國文化意識的土壤上的,我們只有對中國文化意識有了深刻領悟,才能對戰國銘文藝術的獨特形式把握于指腕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