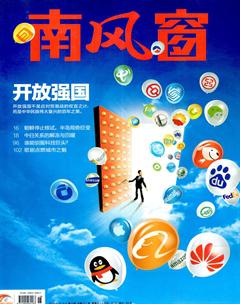新東方PK學而思:市值:價值?
何子維

草根,曲折,成功。《中國合伙人》的勵志創業故事在中國,永遠都有其存在的價值,但現在新的版本出現了。
2017年7月,好未來(前身“學而思”,以下采用“學而思”)的市值首次超過新東方,人們發現,一個是俞敏洪用10年時間讓股價漲了9倍的新東方,另一個是張邦鑫用7年的時間讓市值膨脹9倍的學而思。
企業市值的較量從經濟層面講,饒有趣味。但在經濟結果以外,這個案例正好提出了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我們的孩子是誰?教育應該如何幫助他們成長?
爭奪K12
俞敏洪在1993年創辦了新東方,因培訓留學考試一舉成名,穩坐教育培訓機構的頭把交椅。甚至2006年在美國進行上市路演時,許多華爾街的中國人都曾經是新東方的學生。
新東方的崛起,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想象力,一群極富野心的創業家南征北伐中國的教育市場,也將這個市場分得越來越細。
2003年,張邦鑫入局,成立學而思。2010年,赴美上市。成為國內首家在美上市的中小學教育機構。2013年,“學而思”更名為“好未來”,全面布局教育產業。張邦鑫的創業傳奇幾乎是俞敏洪的翻版,要說不同,就在于一個選了英語,一個選了數學。還有一點,是學而思似乎是為K12(專注于小學,初中,高中這12年過程的全科課外輔導)而生,而K12起初并不被新東方重視。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我國大概有在校中小學生1.64億人,到2020年,預計將達到2.12億人。從這點上來看,對于中國的教育機構,K12不只是一項業務,更是一場布局當下關乎未來的角逐。
2008年,新東方的K12業務拓展到了全科。到2011年,新東方K12業務營收增長約130%,營收占比約35%.超過留學考試業務成為新東方最大的收入來源。此后,K12業務就一直成為新東方主要的聚寶盆。
當大家感嘆俞敏洪的目光敏銳時,新東方內部的情緒并不高。“這只是一場被動的選擇,”張宜南對《南風窗》記者說。這位新東方西南地區的前財務員認為:“留學生的基數沒有中小學生大。更何況留學市場也在不斷瓜分。”
事實上,頗為吸引眼球的出國留學潮,其總人數并非如外界普遍感覺的那樣在高速增長。據教育部數據顯示,2011年留學人數增長率為19.32%,2012年為17.63%,而2013年僅為3.58%。
與此同時,面對愈演愈烈的國內應試教育,學生受教育年齡在不斷降低,爭搶優質教育資源的家長人數在不斷增多,這些需求最終“落在”K12市場。
速途研究院的報告顯示,從2013年的1800億到2016年的3270億,三年時間內,K12市場的規模增長近一倍。
相比留學潮的回落,需求旺盛、成為剛需的K12市場,無疑是一塊肥肉。要維持教育培訓市場霸主地位,要維持增長空間持續,當然,也為了股價和投資者,俞敏洪也必須選擇K12業務。
一個很奇特的事實是,盡管新東方和學而思都在K12取得了令人驚嘆的業績和增速,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它們沒有發生過正面的競爭。至少,在學而思起步階段,對新東方這樣的巨頭而言,學而思的星星之火,不會形成顛覆新東方的燎原之勢。
但是形勢的發展讓許多人所料未及。2013年,學而思十歲的時候,新東方在當年二季度凈虧損了1580萬美元。接著在2016年,新東方被披露在留學咨詢業務上造假,股價一度暴跌24%。這時候人們才恍然發現,那個從兼職做家教,靠補課壯大的張邦鑫已然登堂入室。
2018財年第一季度,新東方凈收入約為6.61億美元,同比增長23.8%。而學而思凈收入約4.56億美元,同比增幅為68.1%。單純從數據的絕對值上看,前輩新東方依然領先。但在投資者的手高高舉起的時候,學而思比新東方不逞多讓。
誰是支付者
41歲的黃媛坐在廣州天河區學而思一間教室的后面,她在草稿紙上做的數學題,和在前排上課的兒子是同樣的。今天,這樣的“陪讀”模式在所有培訓機構里比比皆是,是一種常態。在黃嬡眼里,學而思有點“高大上”。
黃嬡所謂的“高大上”,是學而思對學生寧缺毋濫的選拔原則。反過來說,不是每個學生都可以上學而思。其次是學而思的分班原則。每個學生至少要經過一次入學考試,然后被分到相應的班里。這是學而思自有的漸進式在“攬客”(即學生的增長)模式。
之前也曾把小孩送到新東方參加暑期課的黃媛觀察到,新東方的一個班級動輒百人,里面的學生自控能力和學習能力各有千秋。新東方講師李敬煒也認同這個說法,因為新東方無論大小班級,入學幾乎沒有門檻。
在K12業務的拓展中,新東方照搬了英語“攬客”的那套模式。建立分校、品牌促銷、短期營收。從結果來看,它的營收數據比學而思更好。然而“現在看,新東方的一個大班里有一、兩百人,大家就覺得是很多人了,但在前幾年是四、五百人呀。”新東方上海校區的講師李敬煒對《南風窗》記者說。
物業租著,人員雇著,水電耗著,分分秒秒都要花錢。當教育遇上商業。活下去的必要條件就是持續創造穩定的現金流。在一線城市,學生數量減少,但成本卻沒有隨之同幅度減少,意味著現金流的下滑,在資本市場,這很不好看。
因此,新東方的分校不斷地下沉到三、四線城市。不過,張宜南質疑這樣的擴張方式和速度是否適合K12市場。她認為,新東方優先開展的高年級業務,導致口碑很難向下傳遞。中小學輔導為小班制教學,需要引入大量教師,要求學生不斷續班,以保證營業收入的持續增長。然而,多數情況是“學生來上一期課程就走了,沒法續班”。
這兩種招生方式,其實指向兩種生源:新東方籠絡所有學生,學而思則盯住能出成效的小孩。
不管全部還是部分,關鍵是,哪種方式更能增加營業收入?其實,問題的根本是,哪種生源的消費能力更強?
遭遇學生退課,原本是教育培訓機構的常態,但作為新東方講師的李敬煒,遇到學生退課時,聽到家長留下這樣的話:“你們為什么不能像學而思那樣把小孩管的嚴格一些?”在李敬煒看來,新東方將對成人使用的發散式教學模式,輻射到低年齡段的k12教學中,并不符合“中式家長”的教育認知。
嚴格是話語表達的一種形式。中式教育的指揮棒受制于高考升學。是一種追求升學率的應試教育。在中式家長眼里,教育機構的核心競爭力還是教學質量,最終結果是分數。或者說,仍處在財富快速流動中的當下中國,尚未形成固化的社會階層,“學而優則仕”、“知識改變命運”仍然是人們心目中顛撲不破的真理,升學則是最直接也最便捷的上升通道。
培育優質教育,新東方采用了明星講師制度。就像新東方的地鐵廣告,永遠是站一排穿著西裝的教師,重視人才是新東方的基因。
不過,對名師的依賴,也讓新東方掙扎。家長在給孩子選擇課外補習班的時候,的確會在乎教育培訓機構的品牌,但最重要的還是在乎孩子的學習成績能不能得到提高。在這方面,老師的名氣和實力大過機構,這是K12的核心。
家教出身的張邦鑫比俞敏洪更清楚這點。
學而思對教師的訓練采取了標準化模式。一位學而思教師告訴本刊記者,他們培訓期間,每天50元餐飲補助,住宿不花錢,報銷交通費用,整個培訓就只做一件事——練課。凌晨備課、板書漂亮、聲音洪亮、拿出激情等都有統一的標準和要求,這使學而思的教學保持了可復制性的可能,也讓“三四線城市擁有一流教學資源”成為可能。相比新東方一直做大的思路,這便是學而思彎道超車的策略。
在接受本刊記者調查的教育培訓機構中有一個共識:學而思吃透了應試規則。在看似只關聯學生和老師的教育培訓機構,在看似精悍但卻豐富的K12產業鏈中,真正對營收起決定作用的.是那些為孩子爭搶優質教育名額的家長們。他們作為孩子教育費用的支付方,在優質教學資源面前既持幣待購,又重復消費,而最重要的是這種可重復的消費。
續班是教育培訓機構重復消費的最直接體現。續班和約會網站是一個道理。在這個以結果為導向的K12市場,只有學生愿意續班,才會帶來源源不斷的營收。這有點像約會和婚戀,聽起來差不多,但其實不一樣,前者的用戶重復性使用和消費的可能性更大。這也就是為什么陌陌比世紀佳緣的市值高。
豈止是補課
不過還有一點“高大上”,是黃嬡沒提到的。對于應試教育機制的僵化與粗暴,廣州某大學的中文教授鄭奇海雖然深惡痛絕,但更多的是無奈。
鄭奇海的小孩與黃媛的小孩在同一個班級。每周六夕陽西下,他要載著小孩穿越大半個城市,去學而思給小孩“加餐”。在鄭奇海看來,學而思讓應試考試變本加厲了。
“可是,你看這墻上貼的”,鄭奇海向《南風窗》記者指著走廊上的板報,板報上主要是“祝賀學而思多少人,或者某某在競賽里獲獎”之類的宣傳,在這些內容的刺激下,哪怕是“饑餓營銷”,“也只好定好鬧鐘為小孩搶名額”。
鄭奇海的態度有些令人不安。公允而論,我們都是在這樣的教育氛圍里學習并成長起來的。可是,若連鄭奇海自己也深深質疑這個教育模式,那么他的孩子怎么能夠相信呢?
更令人不安的是,鄭奇海不是孤例。《中國中小學課外輔導行業研究報告》顯示,有八成家長認為課外輔導是中小學教育的組成部分,在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參加課外輔導的中小學生比例超過70%。
在現行教育升學體制下,孩子沒有選擇,家長們也沒有選擇。問題在于,部分家長選擇孩子的教育方式只是跟風而已。他們對于給予孩子什么樣的教育是最好這個問題的認知,停留在他們所受的教育層次上,沒有認知升級,沒有與時俱進,只好跟風。
基于對家長教育理念的缺失和停滯的判斷,學校、教育培訓機構在每年高考后張貼所謂的紅榜,其目的不是表彰學生,而要告訴家長,這個學校、教育培訓機構的教育水平在當下的體制內是多么厲害,迫使那些沒有認知升級的家長對這個學校、教育培訓機構趨之若鶩。而在教育已然產業化的當下,收生率高就意味著收入高。這就是為什么學而思要把功夫花在K12上,也是為什么學而思的市值高于新東方。
但是整個社會的普遍傾向是,學生的負擔越來越重。政府也開始介入。去年,成都學而思被叫停。今年,“為學生減負”也寫進了政府報告。教育產業化是政府公共治理改革及教育自身發展的必由之路。然而,教育產業化并沒有經過社會運動真正有力的捶打和拷問。
事實上,教育產業化的好壞,并不是由討論或表態決定,而取決于現實的社會需求、價值導向和利益博弈。但現在,家長、學校、政府,乃至社會各方面,被教育競爭的焦慮攫住而忽略不同孩子的需求是不明智的。
社會學家鄭也夫曾舉例說,能研究出最好的手機的人,在社會上占的比例連1%都不到,你研究不出來,跟著用就行了。社會的分工是很細的,教育要多元化,絕不能讓高等教育把越來越多的青少年裹挾進來,教育要呈現多樣性。
一個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長則告訴本刊記者,相比許多公辦學校本身管理上缺乏活力,管理手段落后、單一,官僚化、體制化十分嚴重,已逐漸成為效率低下的組織,類似學而思等機構的教育理念則更適合自己的孩子。他舉例說,“我陪著女兒去聽過他們的課,老師確實講得深入淺出,很生動,這能夠激發孩子學習的興趣。”
(應采訪者要求,文中張宜南、李敬煒、鄭奇海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