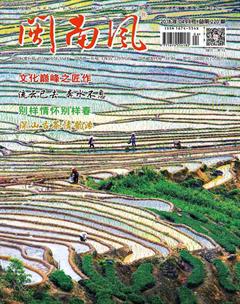遭遇花生
文雨
花生于我的家鄉來說不是特產而是土產,許多地方的農作物都有花生,所以這一產物雖然好卻并不稀貴。在市場上花生往往以幾塊錢的價格販賣,而且個個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粒大飽滿。自小在花生味里長大,家鄉的花生讓我覺得像一位年老的長者,我們洞悉彼此;倘若是在異鄉看到花生,一種他鄉遇故知的興奮,熟悉又親切的感覺像流水一樣滔滔入心。
在城里遭遇花生是常事,上周五路過羅錦橋的大榕樹下,一輛24寸的大自行車馱著兩個竹簍筐,筐面擱著兩個裝滿水煮花生的簸箕,我幾乎能聞到水煮時花生蒸發出來的香氣。靠近攤位,我的車都還沒停穩,攤主就開始招買了,她說:“這是今天才摘的,絕對新鮮”。本來無心在意這些花生的季節、來歷,被攤主這么一說我反倒心起警覺——剛摘的,怎么可能,現在可是十二月,在閩南花生不是都在農歷的六、七月份才有嗎?這個時候還有新鮮的花生,該不會又用什么藥水培植出來的變異果吧,不是當季的還是少吃為妙。攤主見我躊躇,抓了一把往我手上塞,要我先嘗,我推辭,她叫得更勤了,幾次三番的招呼,她甚至把殼剝了遞到我面前。不打算買,我無心嘗試,她的過度盛情讓我逃也似地離開。這讓攤主很是不解,她不知道是她的一句:“今天摘的,絕對新鮮”把我嚇成落跑顧客。我更不知道六、七月的花生是當季的,而十二月份的花生是反季的,產量雖然低了些,但是可以有的。這是回家母親聽了我的嘮叨告訴我的,聽完后我有種無知自大被貶的傀怍。做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閩南農家子女,自小就與花生結下淵緣,自以為對花生有知節解末的了解,沒想到不當農夫的人論起農業知識再熟悉也是門外漢。
在我那個如今人見人贊的老家,三十年前可謂是偏而遠的鄉村,沿海風大,黑土地缺水,農業主打產品除了水稻、番薯、花生,再插種一些紅高粱和旱麻,除此以外再無其它了。水稻的生長得看老天爺的臉色,天不下雨鄉親們就得籌款上交給水庫,求人放水灌溉,而種花生就相對比較省事了。
花生在我們的生活中可不僅僅像許地山筆下的象征處事為人的那么一點點價值,它還是我們生活的全部經濟來源。希望大,種植量也大,為此在我那充滿勞作記憶的童年里,花生是我非常排斥的作物,因為農忙時節實在太累了,偏偏它的收獲季節總在一年之中最炎熱的六、七月份,這期間全家人都忙于下地根本沒空煮一頓像樣的飯,而且老人、小孩皆沒能逃過忙碌的派遣。我們每天天還沒亮就得跟著雙親下地,到中午頂著火辣辣的太陽回家,還得隨行挑一擔花生回來。山高路陡,且都是羊腸小道,兩旁又有農作物纏絆,空手走都很不方便更何況要挑擔子。挑回到家的花生還得一顆一顆地摘下來,曬干,擇凈。摘花生是一個叫我痛苦的差事兒,之前拔花生就已經讓手密布水泡了,這會兒我還得用這只累累傷痕的手去碰那外殼堅硬的果實,簡直要人命。我于是經常找各種借口溜出家門,農忙時節還這么不懂事是最容易觸怒母親的,從地里回來,一看我不在家,母親必扯開嗓門喊,把我喊回來棍子伺候,后來我學聰明了,夏天也穿長褲,防備母親的棍子。不耐煩的時候我問母親:“今年花生收完,明年還種嗎?”母親吼道:“不種,我們吃什么?”這是要人崩潰的回答。不過在一次打過我之后母親偷偷地抹淚,我怯著膽告訴她我手疼,并且把雙手攤在她面前,過后我便被允許不用下地,還可以帶著手套摘花生,雖然笨拙了些,但很好地保護了我的雙手。
曬干后的花生能在院場上打滾,像活潑亂跳的小人兒,發出呵啦啦的聲響,一個個都黃燦燦,要是堆成堆看著像一堆黃金小山。可惜這些“黃金”并不歸農戶所有,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家政策里還要農民交三金農業稅,對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來說,秋收后的日子是農民交稅正當時。收獲完畢的花生要經過一番優劣篩選,小部分的優質花生要留著明年當種子, 其余的都被送往糧站進行統購,售出后所得的錢基本都上交農業三金,多還少補。要是遇上好年頭,大豐收,統購完還能余一點留著自家打油,花生油可不像現在的菜仔油、玉米油純粹烹調作用,在皮外傷方面花生油有很好的去瘀消腫、消炎作用,對于極個別的皮膚炎癥,用花生油調藥粉涂抹能根除。打油后花生渣會形成一圈一圈類似糯米糕的圓形固體花生箍,農民用它來喂豬營養很豐富。倘若遇上糟糕的干旱年景,收成少,農業三金得想辦法籌去上交,更別想打油了。
后來體制改革,村里按人口分土地,繳納三金的政策也取消,少了繳稅的壓力,父親還是堅持種花生,賣給販子換取生活費,收獲越多,賣得越多,我們那一年就能過得越滋潤,為了讓我們更好地生活,父親那些年像打了雞血一樣鉚足了勁,一口氣承包別人家十幾畝地,全種花生。也多虧了那十幾畝地和花生,我們家庭經濟的最大轉折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花生在我們那兒多得泛濫,如閏土說的:“過路人采個瓜吃,在我們這里不算偷”。在我們村里,過路人隨便在哪個院子里抓一把花生吃,都不會有人說你偷,人們總是在拿到它換來的錢時,心里才覺得花生要越多越好,收獲的過程中它不過是一種農作物罷。
花生有許多種食用方法,最常見的是生吃和今天我在攤販上看到的水煮花生。花生生吃很養胃,老家的人要是胃犯上個喛氣,反胃酸,抓把花生吃準能緩解。那時候,我們要上學或外出,口袋里都必須裝上花生,或生或熟都行,肚子餓時用來充饑,即使不餓,當零食一路咀嚼也相當有趣。把花生煮熟再曬干味道可不一樣了,因為煮的時候要加入鹽巴和蒜蓉,曬干后吃起來有淡淡的咸味和蒜蓉香,這樣的熟花生在若干年前是我們農民最拿得出手的伴手禮。連殼干炒,焗油,酥鹽炒,油炸都是花生極妙的食用方法。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母親除了能用以上的方法將花生變成一道菜以外,她還有更好的方法為來年青黃不接的梅雨季節儲上一甕下飯菜,那就是腌制花生,這個過程不簡單。
在腌制之前,準備工作不少,母親會在提前十來天就清洗出一個甕,洗完倒扣著風干。再準備一些黃豆,姜,醬油,紅糖,叫我剝一大盆花生。
黃豆是用來做豆腐的,浸泡過的黃豆膨脹起來,在石磨上能快速磨出漿,這些豆漿磨出后倒在粿巾里過濾,濾出來的純豆漿倒入鍋里煮沸,撇凈一些浮沫,經過一小段時間的冷卻,然后緩緩加入按比例調配好的鹽鹵水,在加的過程中必須得有一個人用飯勺不停在鍋里攪拌到兩者完全融合,豆漿出現豆花樣的時候才能蓋上鍋蓋,添把小火,待火完全熄滅,鍋里的豆花結成塊,再倒入鋪著濕粿巾的豆腐模里,四個角落理均勻后蓋上粿巾,放上壓蓋,還要在壓蓋上壓一塊石頭,有時候這樣一壓就要一整晚,第二天才拿出來切,這樣做出來的豆腐如果馬上食用不僅營養豐富,還新鮮嫩滑,可是這是要放到甕里腌制的,必須再經過鹽水煮,煮過后風干到微硬才能放進甕里。
要腌制的花生也必須用鹽水煮,煮完晾到沒水份才能用。為確保出味,姜得切成絲,鹵鹽水,把鹵出的汁倒掉,只利用姜絲。
一系列材料準備就緒就可以入甕了,先在甕底鋪一層鹽,在鹽上鋪一層豆腐,豆腐上鋪一層花生和姜,撒上薄薄的紅糖,再一層鹽,一層豆腐,一層花生和姜,循環著鋪上來,直到甕滿放不下為止,再緩緩地灌入醬油,醬油要分幾次灌,確保滲透到甕底,最后一次往往要在相距二至三天以后,灌完才把甕口封住,封口以后要一段時間不能打開,避免空氣進入甕內干擾發酵。這樣的一甕腌制品在我們家能管大半年的稀飯,美味又實惠。
在我還沒外出求學之前,要制豆腐磨黃豆一直是我的美差,我很樂意在那兩片小小的磨盤上看完整的豆粒如何身不由己默默地粉身碎骨,爾后幻想濃白的豆漿是它的淚。
由于甕口小,母親手大伸不進去,裝料入甕也都是我幫忙的,母親在一旁監督,就因為參與了整個過程,所以我對腌制花生的步驟記得特別清楚,對家鄉的石磨情感特殊。
花生幾乎占據了我大半的記憶,現在經常是一閉眼,全是城門外無邊無際的綠葉,和大汗淋漓挑著花生的父老鄉親。前些年去郭坑鎮采風,我負責鼎寨山采風寫作,親臨鼎寨山后,站在山頂居高臨下,有坡有坑的鼎寨山多像家鄉東門外那一片農田,那些矮植株的茶樹遠看像極了記憶中的花生樅,在那么一瞬間,扛著尖擔,一頭綁著草繩的鄉親們都在我眼前走動,他們你來我往地走在通往坑底的羊腸小道上,他們挑花生,挑高梁,挑旱麻,他們披星帶月,揮汗如雨,氣喘如牛,恨不得把山也挑回家。記憶讓我激動,青草綠葉于我是最普通也是最特別的煽情物,下山時我狂奔在鼎寨山的山路上。如今家鄉的農業已經荒遠,田地雜草眾生,藤蔓攀爬,菅芒長出一人高,許多小樹現在參天生長,站在水門城門口已經無法望見坑底,無法望見牛頭山,無法望見遠處的流會燈塔,記憶成了懷念的全部,只是再也回不去。
那一夜,我因為商販的水煮花生而回憶了整個童年,靈魂重繞了一趟崎嶇的山路,看到許多深深淺淺的腳印,最終還是定格在花生的味道里,我決定去找攤販買花生。
次日晌午,我特意再路過羅錦橋,遠遠就看到昨天那個攤販把自行車停在大榕樹底下,我往她的方向靠,她老遠就看見我了,扯開嗓門沖我大喊:“昨天的花生是新鮮的,你怕,今天的花生還是新鮮的,你肯定又怕……”這么奇特的招客方式,不得不佩服她的大嗓門,我瞬間有種被路人的眼光灼傷的尷尬,我趕緊調轉方向離開。
有心插花盡夭折,該不會是我無緣吃她的水煮花生吧,但我總相信我與花生是有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