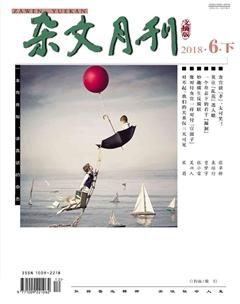三不負主義
唐翼明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根基是祖宗崇拜、圣賢崇拜,這跟西方文化以上帝崇拜為根基不同。上帝崇拜的終極關懷是能不能進天國,祖宗崇拜、圣賢崇拜的終極關懷則是能不能澤被后世,能不能垂范后昆。能垂范后昆的就是雖死不朽,所以中國人的歷史感特別強,中國人喜歡在祖宗、圣賢的前言往行中尋找榜樣。春秋時候,魯國的賢臣叔孫豹把能夠垂范后昆的言行歸納為三個方面,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他說:“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見《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唐朝的學者孔穎達解釋說:“立德謂創(chuàng)制垂法,博施濟眾”;“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于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見《春秋左傳正義》)總之,無論德、功、言,只要能造福子孫,影響久遠,便不會隨身而沒,便雖死而不朽。
因此,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核心的儒家學說,不講靈魂不滅,也不講來世輪回,而講“三不朽”。只是“三不朽”立意太高,只適合少數想做圣賢的人物。而且“三不朽”還容易走偏,有些起意做圣賢的人最后卻做成了獨夫民賊。“不朽”是不朽了,卻不是好的“不朽”,而是壞的“不朽”,不是造福國家,造福百姓,澤被后世,而是禍害國家,禍害百姓,流毒千年。這種例子還并不少見。
我現在提出一種“三不負”主義,即“不負天,不負人,不負己”。這是我平生做人做事的信條,也可以說是我的信仰。竊以為“三不負”主義可以避免“三不朽”主義立意太高的缺點,比較適合一般人。
先說不負天。這個“天”不是天老爺的“天”,而是先天的“天”,天賦的“天”。人生下來并不是一張白紙,而是一顆蘊含了很多潛質的種子,這些潛質是先天的,或說是天賦的,用現代科學來講,略等于基因。但這些天賦或說基因能不能充分顯現出來、發(fā)展出來,卻有待后天條件的具備。這后天的條件中,有時代、地域、環(huán)境等因素,還有個人自己的因素。時代、地域、環(huán)境,基本上不能由自己決定,但個人努不努力卻是自己可以決定的。我說的“不負天”的意思,就是個人自己要盡自己的力量,努力讓自己的天賦得到充分的發(fā)展,而不要辜負了這個天賦,不要對不起這個天賦。例如,你有音樂的潛質,你就要千方百計努力奮斗,讓這個潛質得到可能有的最大的發(fā)展,成為一個音樂家,而不要老是感嘆生不逢時,埋怨沒有生在德國、奧地利,沒有生在富裕的家庭。這種感嘆和埋怨是沒有意義的,改變不了現狀,而你的努力卻說不定可以沖破時代、地域、環(huán)境的限制。
再說不負人。不負人首先是不要對不起生你、養(yǎng)你的父親母親,古人叫“不忝所生”。其次是不要辜負在你的成長過程中教導你、輔助你、愛護過你的老師、朋友、恩人、貴人。再其次,就是不要有害人之心,努力做到不傷害任何人。曹操的名言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我的信條相反,寧可別人負我,我也決不負人。當然,我得聲明,這里講的是一般的原則,不是講特殊情況,也不能推至極端。我并不提倡任人欺負,我的意思是說寧可自己吃點虧,受點委屈,也絕不損人利己,不做虧心之事。
再說不負己。不負己的第一層意思是對自己負責,我以為人生在世,最高層次的責任感不是對他人、對團體、對身外的什么負責,而是對自己負責,就是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人,必須讓自己達到一個人應該達到的高度,任何情況下決不自暴自棄。不負己的第二層意思是不屈己,即維護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尊嚴,決不在有關人格的原則問題上委屈自己,決不對任何人低三下四,唯唯諾諾,決不放棄獨立思考,人云亦云。這對一個知識人而言,基本上就是陳寅恪先生提倡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以上就是三不負主義的大概意思。
“三不朽”是外向的,“三不負”是內求的;“三不朽”主要看結果,“三不負”主要看動機;“三不朽”更多依賴于外在條件,“三不負”主要依賴于自己的意志;“三不朽”只適合于社會頂層人士,“三不負”適合任何人;“三不朽”只有極少數人可以達到,“三不負”則人人可以做到。“三不負”雖說人人可以做到,但真正做到的極少。這有點像孔子說的“仁”,“仁”是一種主觀精神境界,只要你自己肯做,沒有人能夠阻擋你。所以,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見《論語·述而》)但“仁”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所以孔子很少以“仁”許人。
“三不負”跟“三不朽”并不矛盾。一個人真正做到了“三不負”,是可以通向“三不朽”的,如果你的天分足夠,條件又具備的話。
裴金超薦自《羊城晚報》2018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