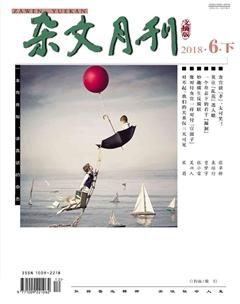我的愿望誰知道
吳非
在某地參加活動,主辦單位派司機開車接送。司機職業(yè)素養(yǎng)很好,見我行動不方便,每次都細心地關照我動作慢一些,不要急。送我去機場的路上,我們談起這個城市的交通,順便也說氣候,也說市場供應,自然也談到房價。我想,要在這個城市買房子,像司機這樣的職業(yè)收入,會不會有些困難。畢竟該地收入差異很大,一個普通勞工,能適應這里的高物價嗎?我認為這也是了解一個地區(qū)生活狀態(tài)的參考依據(jù)。
我猶豫了一下,問:“可不可以問一下你的月收入?”青年司機愣了一下,爽快地說:“可以呀!我每個月實際到手的錢是3800元,加班費三四百元,年終全勤獎4000元,加上節(jié)假日補貼,七七八八,平均每個月大約4500元。”我說,那就是說,一年收入能買兩平方米的房子了。司機笑著說,我不買房子。我一輩子不吃不喝也買不起,我只能租房子。沉默了一會兒,司機忽然說:“老師,三年了,我到這個單位開車三年了,這是第一次有人問起我的收入。整個單位,從來沒有一個人問過我晚上住哪里。”這就令我困惑。這個司機每天為單位各部門開車,還經(jīng)常要加班,三年多,他的車幾乎拉過單位所有人,為什么沒有人想到關心一下他的收入情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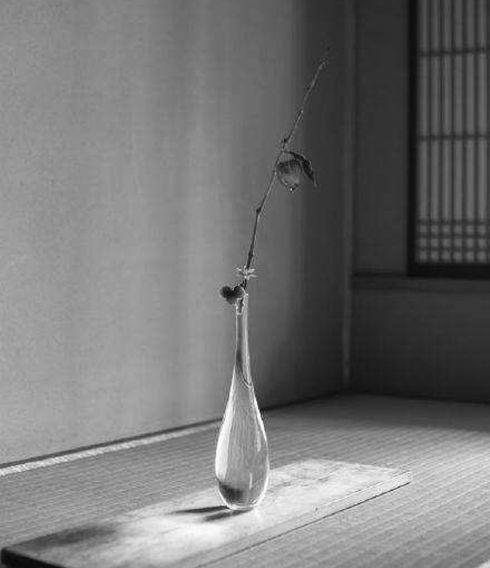
不隨便打聽他人的經(jīng)濟情況,是應有的禮貌;如果出于研究社會狀態(tài),特別是對所謂弱勢群體的關心、過問一下,我不認為有什么不妥。特別是在當下,多了解“階層”問題,尋求溝通的渠道,有可能緩解社會矛盾,可能正是讀書人應有的責任和態(tài)度。
司機說,其實他知道這個單位職工平均收入是他的五倍以上。但作為聘用制的合同工,他安于本分,這就是他的“命”,從沒想過換個單位。司機也說道,八小時工作制沒有保障,實際工作時間遠遠不止。而且有些工作是額外的,但他還是盡可能為大家提供方便。畢竟開車是服務工作,適當?shù)命c補貼就會心滿意足。比如,讓他在機關食堂用餐,中餐只要8元錢,比外面20元還要好,想到這一點他常常感到知足。總之,他從沒有非分之想。
這位司機希望該單位的人了解他的收入情況,可能的愿望是什么?我發(fā)現(xiàn)他并不是想讓單位增加他的收入,有財務制度管著呢,沒有這種可能性。他可能只是想讓人們有個比較,他是怎樣對待工作的,他是如何加班的,他實際拿了多少錢,他的勞動付出和收入是不是很合理……
我的思緒在延伸。一些同類的情況我們也許忽略了。比如,一些官員不知道“群眾”每個月生活費是如何開支的,因為他們幾乎不會花錢。機關食堂吃慣了,以為一個菜就該三元錢,到社會飯店就批評老板心太黑。大學教授不知道自己的學生每個月生活費是多少,但卻很在意自己的名銜和收入;研究生為什么會稱導師為“老板”,而教授也把校長稱作“老板”?這都是可以一說的話題。
“孔子過泰山側(cè),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我小時候背誦,不知有什么用。我學生時代被教會一個詞,“訪貧問苦”,至今記憶猶新,不敢忘之。魯迅說:“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和我有關。”真的有關。
若子薦自《揚子晚報》2018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