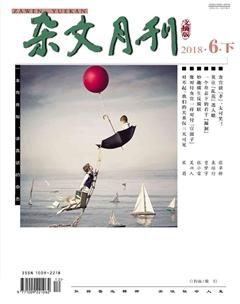茶客留言
美文讀三遍
張小華(甘肅靖遠)
“如果你曾愛過我,你自然知道。如果你不曾,我該如何讓你明白呢。”葉傾城在自我介紹中如是說。她的文章報刊轉載率很高。盡管《最美的文字背三遍》我已經看過,當拿到《雜文月刊》(文摘版)2018年4月下后,我又仔細閱讀了一遍。讀了又讀,意猶未盡。我便把這篇文章推薦給我的學生和孩子,旨在激發他們誦讀經典的熱情。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強調,應該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嵌在學生腦子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
同期我還向學生推薦了《只要心里還有光》一文。光就是光亮、希望。在求知的過程中,在人生的道路上,心中的光極為重要,尤其是在困頓、挫折、坎坷的境況下。孔子最看重的弟子顏回被列為七十二賢之首,其優點之一便是安貧樂道。對此,孔子極力點贊: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無數志士仁人演繹了“生于憂患”的道理。只要心中有光,腳下便會有路。
期待《雜文月刊》繼續摘發美文,我們將讀了又讀。
畫中雜文
郭樹榮(山東濟南)
漫畫,我認為可稱為是畫中雜文,所以,《雜文月刊》每期都刊發若干幅漫畫,自是刊物題中應有之意。我很愛看。
每幅漫畫,都可見出作者水平高低。有的漫畫,寓意深刻,觀之,使人賞心悅目,與讀者心有靈犀一點通,閱讀的效果不亞于一篇雜文,這,自然是上乘之作。例如:《雜文月刊》文摘版2018年4月下,于昌偉先生畫的《踢》,就是這樣一幅漫畫:想把“問題”踢走,最終卻讓問題找上身。由此可見,問題要解決,踢是踢不掉的。但是,畫中人物,要像,這是最低要求。同一期中《教人學雷鋒,自己學和珅》中的雷鋒,就不像雷鋒。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常回家看看
張道銳(江蘇沛縣)
《雜文月刊》文摘版2018年2月下載有《固本培元》一文,作者對于蘇州一家護理院推出的“獎孝金”制度表達了一種萬般無奈之聲:“如果只用世俗去喚醒人心,那我寧愿淌入世俗;如果用錢財可以找回失去的心中悸動,那又何樂而不為?”1999年春晚,一首《常回家看看》唱哭多少中華兒女,時至今日,哼唱起來仍不禁淚眼婆娑。聽著、唱著《常回家看看》的一代大多也正值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齡,可又有多少人能“常回家看看”?父母不期你能常回家“捶捶后背揉揉肩”,也不期你能常回家“刷刷筷子洗洗碗”,更不指你“為家做多大貢獻”,只要你能常回家看看,父母就心滿意足了!
《孝經·開宗明義》篇中講“夫孝,德之本也。”孝,從小的方面來說,是個人修身做人之根本;從大的方面來說,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屹立于世界舞臺之根本。無論時代怎么變遷,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孝”不能變也不會變。愚認為,不能將是否盡孝、能否盡孝、盡孝到何種程度等問題的板子打在“快節奏的生活”上,而應打在作為子女的我們身上,我們該反思自己的心是否“日益麻木”了?如果,“獎孝金”真能“獎”出一批孝子,真能“激活孝心善意”,這樣的“孝”又有何價值與意義?“(真不是錢的事),萬望引導人們向孝的種種,(能帶著人們)去追本溯源,走向固本培元的未來。”
常回家看看,別讓父母把心望穿!
“顯擺者”的可笑
張立超(遼寧錦州)
讀完《顯擺的度》(《雜文月刊》文摘版2018年4月下)一文,有些話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作者說:“顯擺也是一種生活權利,關鍵是要與個人素質相匹配,盲目的顯擺其實很難得到社會認同。”顯擺,或者說自我炫耀,即使經過周密醞釀、精心策劃后再“完美實施”,恐怕也很難得到社會認同,說不定還會讓人更加嫌惡。說到底,“顯擺”是人性的“硬傷”,就像成熟的麥穗總是低頭,癟子穗卻高高昂頭一樣,誰能認可那風中肆意搖擺、不可一世的腹內空空之物呢?“有素質的顯擺”筆者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樣子,但一“顯擺”肯定會讓自身的素質大打折扣,高調捐贈也不是沒遭遇過質疑,“富豪式豪捐”與幾十年默默無聞、不求名不求利的捐贈者的境界肯定是不一樣的。既然施愛他人、無私奉獻都不值得炫耀,那請問還有什么值得“顯擺”的呢?
“顯擺”無疑是向別人炫耀自身的財富、美貌、顯名、地位等自認為超越別人的東西,比如有一位女同事跟我說:“知道為什么這些男人都追我嗎,就是因為我太好看了!可惜啊,就是再貌若天仙也不能都嫁啊!”當時我正在宿舍里洗衣服,頓時驚得“兩手僵硬不能動彈”,心想:這樣的話也能從自己嘴里脫口而出?難道幾個男人你都想嫁不成?“顯擺”過頭了吧?
“顯擺的度”還真是難把握啊!
人人皆過客,不過是尚在人間而已,長得白嫩了點,不小心發了個財,或者老子僥幸混了個一官半職,再或者嫁了個小財神爺,自認為優勢占盡、掉幸福窩里了,說到底,不過是個合法公民而已,不過是個暫時享受上蒼恩賜時間的活人罷了。如果自得其樂,低調做人做事,或許還真有人羨慕一下呢!如果因此而炫耀顯擺,除了招來別人的嗤之以鼻,真不知道還有啥用?并非出語刻薄,不過是實話實說而已。如此看來,“顯擺者”不是很可笑嗎?如果不小心再招來嫉恨麻煩,那就更得不償失了。
30元買不回一輛自行車
李本華(湖北武漢)
《雜文月刊》文摘版2018年3月下的扉頁有文云“一輛自行車,當時的價格是30元”。要自行車的是當代著名作家劉震云。劉先生1958年出生,年少時應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那時30元是買不回一輛自行車的。那時名牌自行車是上海的鳳凰、永久,天津的飛鴿,價格是200元左右。而且要購車票。沒有購車票,免談。我是武漢人,當時武漢出產的黃鶴樓牌自行車質量比不上上述三大名牌,也要100多元。30元無論如何是買不回一輛自行車的。即使到舊車市場,30元也買不回一輛還能使用的舊自行車。
同期的《至少,母親不欠你》是我要點贊的文章。它批評了海子的自殺行為。是的,“在母親面前,人們沒有資格戕害她給予的寶貴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