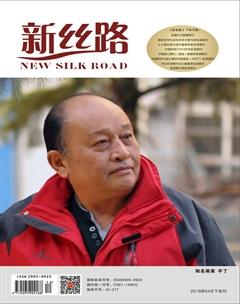從“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看麥克尤恩小說集《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
謝一榕 劉一靜
摘 要:麥克尤恩在他的處女作小說集——《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中為我們展現了一種恐怖的氛圍,他通過壓抑的環境、扭曲的人性、兩性的沖突以及人與自然的割裂來表現出一種“末世”般的荒涼感。這些元素的挖掘與生態女性主義所倡導的價值觀不謀而合,通過后者可以更容易的解讀這部小說怪誕黑暗外殼下的某種核心內涵與價值倡導。
關鍵詞:生態女性主義;麥克尤恩;性別
生態女性主義正式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它脫胎于“生態主義”中。工業化后,社會的經濟政治不斷發展但與之而來的生態破壞也隨之加劇。馬克思曾經這樣預言19世紀的景象:我們的一切發展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1】,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生態主義”研究的火熱也不足為奇。“生態批評的活力還在于它雖然立足于文學但決不拘泥于文學, 而是把批評的觸角伸向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 比如環境倫理問題的提出。 很多這方面的研究把人對待動物的態度與大男子主義、種族主義等聯系起來, 特別是將女性與動物進行類比 , 將二者同視為父權制下的犧牲品。”【2】女性生態主義批評的崛起,也為我們研讀文本提供了另一條途徑。在麥克尤恩《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從人與環境的沖突、人與人的沖突和性別間的沖突,我們都能清晰地看到生態女性主義的影子。
一、男權話語下對生態的破壞
工業革命以后,人類對自然的開發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類和環境的關系變成“征服—被征服”的二元對立,人們不是將自然作為一個平等的客體相處,而是作為索取資源的對象,變本加厲的加以掠奪和改造。不僅原有的自然風貌被破壞的千瘡百孔,被工廠和煙囪占據的城市中也呈現出一種“水泥荒原”的景象,人類這種對自然的支配如同男權話語下男性對女性的強權壓迫,在麥克尤恩的小說里,這中沖突通過對骯臟頹敗的都市景觀的直接描寫而表現出來。他在《家庭制造》里描多次使用“廣袤荒涼”、“工廠”與“高壓電纜”等意象,從環境上就帶給人一種對工業的排斥感和恐慌感。這樣的破敗的景觀是主人公的工人父輩們年年月月疲憊穿梭的,也是年少的他和朋友玩鬧游蕩的場所。正是在這里,白天工人們日復一日的重復生產線上的枯燥,下班后去黑暗骯臟的酒館講“下三濫”的笑話與的惡俗的傳聞,孩子們穿梭在這冷漠低俗的環境中自然也成長成一個個人性淪喪的“小野獸”。
在《蝴蝶》中,更有大段的文字來描寫骯臟的運河:“運河是這附近唯一的一條蜿蜒水道。走在水邊總能給人不同感受,哪怕是工廠區背后這條又黑又臭的水道。俯瞰運河的工廠大部分已經廢棄,沒有窗戶。你沿著纖道可以走上一里半,通常一個人也碰不到。途中會經過一處年頭久遠的廢品站。”,“久而久之,周圍的籬笆全都被當地的孩子糟蹋殆盡,如今只剩下大門還沒倒。廢品站是這一里半路上唯一的景致,其余路段全都緊挨著工廠后墻。”【3】正是在這樣的環境里,人性變得曖昧不明,主人公為了一己私欲殘忍的誘拐、殺害女孩,而路上一群少年的也以無比殘忍的手段虐殺了一只貓:“有一群男孩圍立在一堆點燃的火邊。他們像是一伙的,都穿同樣的藍上衣,剃平頭。據我判斷,他們正準備活烤一頭貓。煙在他們頭上凝固的空氣中懸浮,在他們身后廢品層層堆積像座山。他們把貓的脖子綁在過去拴狗的那根木桿上,貓的前肢和后腿也被捆在一起。他們用幾塊鐵絲網做了個籠子架在火上。我們走過的時候其中一個家伙扯著貓脖子上的繩子把它往火里拽。”【4】冒著黑煙的煙囪和骯臟的運河是人類對自然的褻瀆,毫無人性的濫殺無辜則是對人性的背棄,自然風貌的破壞和人性道德的沉淪在麥克尤恩的筆下都通過末日式的描寫淋漓盡致的展現在我們眼前。
除了《家庭制造》和《蝴蝶》,這種被破壞的自然生態帶來的恐怖氛圍在書中的大部分章節都有出現,比如《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里蝸居在碼頭上方的青年男女,春末微風和空氣讓他們覺得放松,而當夏季悶熱的空氣混合著腥臭的氣溫從碼頭下涌上來時,他們都變得煩躁不安。麥克尤恩正是通過環境對人類的影響來批判人類對生態的破壞,惡劣的生態會潛移默化的影響人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從而引發社會倫理價值體系的崩塌。
二、女性話語下和自然的親近
蘇珊·格里芬說過:“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是由大地構成的, 大地本身也是由我們的身體構成的,因為我們了解自己。 我們就是自然。 ”【5】女性和自然生態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性,因為自然孕育人類,而女性則承擔著繁衍生息的任務。在許多文學文本中我們都能夠看到女性對自然的親近和對生命的尊重,這和男性與自然的關系形成了極強的反差,也是女性生態主義所指出的“性別與生態的聯系”。
在《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里,麥克尤恩除了描寫壓抑衰敗的生態環境,還描寫了形形色色的人,但是相較于他筆下的變態和殺人犯男性,他把帶有希望和光芒的描寫都給了女性。在《立體幾何》中敏感又渴望愛的梅茜,《家庭制造》和《蝴蝶》中天真活潑的小女孩,《夏日里的最后一天》溫柔善良的珍妮以及《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里充滿母愛光輝的西瑟兒……她們身上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自然的熱愛與敬畏。《立體幾何》中的梅茜因為丈夫的冷落而敏感煩躁,當她徹底放松下來,充滿愛意的時候,想到的是“人行道上的山毛櫸、接骨木”、“果汁飽滿的黑莓”和“河邊遍布落葉、蝴蝶飛舞的小天地”……《蝴蝶》里小女孩被誘拐的原因,僅僅是因為想突破灰暗環境的束縛去運河邊上看一看主人公口中編造出來的蝴蝶,《夏日里的最后一天》樂于助人但因為肥胖和自閉被排擠的珍妮,最放松的時候就是帶著嬰兒艾麗斯和“我”穿過樹林,到河里的木船上無憂無慮的談天說地……在這部小說里,自然的美只有女性和孩子能顧欣賞,而人性中好的一面也自然的被放置在她們身上。甚至她們會對萬物產生一種油然而生的保護欲與責任感。
在《短篇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里,當發現那個給“我們”帶來無限恐慌的老鼠懷著一胞孩子時,“西瑟爾跪在老鼠旁邊,阿德里安和我像保鏢一樣站在她身后,那情形似乎她擁有某種特權,她蹲在那兒,長長的紅裙子鋪滿四周。她用拇指和食指分開老鼠媽媽的傷口,把袋子塞進去,合上血肉模糊的皮毛。她繼續跪了一會兒,我們默默地站在后面。然后她把幾個碟子從水槽移開好洗手。現在我們都想到外面去,于是西瑟爾用報紙把老鼠包起來,我們裹著它下樓。西瑟爾掀開垃圾桶的蓋子,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進去。”【6】這種對生命的平等與尊重正是源自女性和自然天然的聯系,她們既是自然之美的發現者也是生命的守護者。如果將這種聯系割裂開,女性的靈動與獨特也就不復存在。還是在《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中,當西瑟兒找到一份工廠的工作時,原本愜意自然的描述改變了:“那是河對岸其中一所沒有窗戶的工廠,生產罐裝水果和蔬菜。每天十小時,她要坐在機器轟隆的傳送帶邊,不能交談,搶在罐裝之前把腐爛的胡蘿卜撿出來。”【7】工廠像一個巨獸,將性格與生命力在流水線上吞噬殆盡,而原本美麗灑脫的西瑟兒變成“她的罩衣被機油和泥巴玷污,散發出異味。”【8】,所有的美都在工業中被變成了廢料。麥克尤恩也借此來表現出自然和女性同生一體,工業化的壓榨和污染,給兩者帶來的只有“美的毀滅”。
三、兩性關系與環境的沖突
女性生態主義的范疇中不僅探討了生態問題,同時也提到了性別問題,女性主義的視角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文本分析的角度。在《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里,我們看到的不僅有性別與生態的聯系與沖突,還有性別本身的沖突。在男權話語中,環境在和人類交鋒的時候處于弱勢環節,女性也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除了正面描寫生態被人類支配和破壞的景象,他還通過女性被敵對和侵害的無助來展現“男性中心主義”對自然界和女性的強權壓迫。
在《立體幾何》中,丈夫只醉心于祖父留下的日記,除此之外既不關心外部環境也很厭倦妻子梅茜。梅茜試圖將丈夫拉出逼仄的世界,但所有的交流和接觸的嘗試都被一一拒絕,甚至在矛盾激化后丈夫不僅沒有反思,還誘騙妻子進入他設下的陷阱,徹底從現實中消失。 《家庭制造》中妹妹對哥哥不設防備,哥哥卻一直厭惡妹妹“干癟”的長相,并在性欲來臨時毫無愧疚感的“誘奸”了她。更尖銳的是,在麥克尤恩的筆下,受壓迫的一方能夠做出的反抗是極為有限的,無論是夫妻間嘗試溝通的舉動,還是女孩們對施暴者的哀求統統都是徒然,就像生態環境在工業的時代只能接受鋼筋水泥的侵害和破壞。
但或許人類與自然的割裂、男性與女性的對峙也并不是那么無解,盡管麥克尤恩在書中給我們展示了一種絕望和恐怖,但提供了一種途徑來彌補,就是重拾“平等與尊重”。在《夏日的最后一天》中,珍妮和“我”有一種無形的牽絆,盡管她胖的連“我”也懼之三分,但“我”并不排斥她反而嘗試著接納,并和她渡過了相當愉快的一段時光,這種“平等與尊重”的友誼最后雖然因為可能的死亡添上一抹灰色,但并不妨礙兩個孤獨心靈之間的碰撞帶來的感動。在短篇《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一文中,因為那只懷孕的死老鼠,西瑟兒和“我”終于選擇了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西瑟兒決定辭去工廠麻木枯燥的流水線工作,而我也放掉了那只奄奄一息的“鰻魚”。或許那只死去的母鼠代表著他們過去的生活,決心釋放鰻魚的那一個瞬間,就象征了他們對生活的重新擁抱,西瑟兒和“我”不再是和別人相同的,在工業化背景下被異化的人,而是重新找回了自我,踏上了新的生活。
《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荒誕恐怖的外殼里實則包含著多層次的反思,對“人與生態關系的反思”,“對異化的人的反思”以及對“人類前途的反思”。他尖銳的指向男權話語下生態與性別的對立沖突,從這些敘述中我們反思工業化帶來的人的生存危機,以及性別對立中女性的弱勢地位。但在這看似絕望的背景下,麥克尤恩仍給我們講述了一種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也是女性生態主義所倡導的“平等與尊重”。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
[2]韋清琦:《方興未艾的綠色文學研究——生態批評》,《外國文學》,2002年03期;
[3][4]伊恩·麥克尤恩:《蝴蝶》,《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09月;
[5]蘇珊·格里芬:《女性與生態:男權語境下的壓迫》,New York:Harper&Row,1978;
[6][7][8]伊恩·麥克尤恩:《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09月。
作者介紹:
謝一榕,女,西安外國語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劉一靜,女,碩士,西安外國語大學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