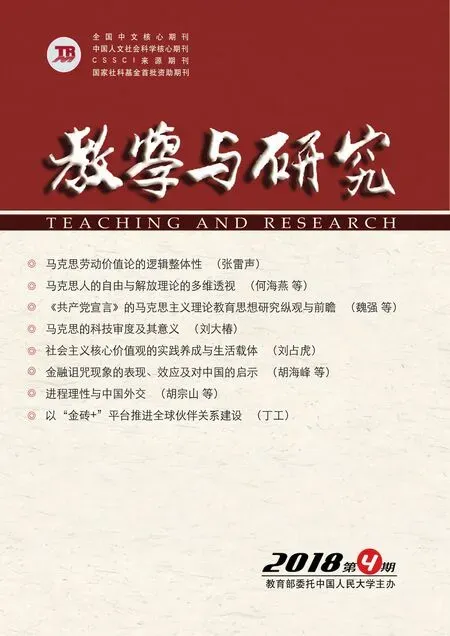金融詛咒現象的表現、效應及對中國的啟示*
,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雖然已經遠去,但它對世界經濟造成的沖擊至今仍未消除,這次金融危機影響的范圍之廣、時間之長、危害之深發人深省,并促使一大批學者開始全面反思金融對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其中英國學者尼古拉斯·薩克斯森和約翰·克里斯坦森(Nicholas Shaxson & John Christensen)提出的“金融詛咒(Financial Curse)”概念引發了學界的強烈關注和共鳴。[1]他們認為,如同資源依賴型國家受到“資源詛咒”而出現增長停滯甚至負增長現象一樣,金融過度發展的經濟體也會受到“金融詛咒”的威脅。一旦金融發展過度甚至脫離實體經濟進入無序、畸形的自我循環、自我膨脹發展軌道,就會損害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誘發金融危機,并超越國界,產生極具傳染性的“多米諾效應”,導致全球市場動蕩、經濟衰退。
一、金融詛咒概念的由來及表現
薩克斯森和克里斯坦森提出的金融詛咒概念,一方面是借鑒了近年來學術界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則是對發達經濟體金融發展過度、金融部門規模過大造成的社會經濟運行種種弊端、矛盾、惡果的集中提煉和概括。
眾所周知,早在一百多年前,西方經濟學家就開始關注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認為一個運行良好的金融體系,在經濟增長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種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正向促進作用的觀點曾長期在學術界占統治地位。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相繼出現日本房產泡沫破裂、墨西哥金融危機、東亞金融危機、巴西金融危機等,促使人們開始重新思考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將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爭辯推向了新的高潮。克魯格曼強烈質疑和抨擊金融發展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觀點,認為“金融業的過度發展弊大于利”,“金融吸納了整個社會太多的財富與人才”。[2]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主席阿代爾·特納(Adair Turner)認為,“不是所有的金融創新都是有價值的,不是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有用的,過大的金融系統不一定更好,金融部門已經超過其社會最優規模”。[3]一旦金融發展過度,不但對經濟增長沒有明顯的益處,反而會攫取大量租金收益,從而引致金融危機并使經濟發生倒退。他們的觀點得到了學術界的熱烈響應,此后眾多學者利用不同的模型、數據和估計方法,從多個角度得出了金融發展過度對經濟增長帶來抑制作用的結論。
盧梭和瓦赫特爾(Rousseau & Wachtel)利用線性模型,通過數據檢驗發現,在1965—2004年間,當金融深化達到一定程度之后,金融發展對GDP增長的促進作用就消失了,他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消失效應(Vanishing Effect)”。[4]拉詹和拉托雷(Rajan & de la Torre)等人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呈現邊際效應遞減的趨勢,最終會減少到小于其負面影響所帶來的成本,超過一定程度就會引致金融危機,最終對經濟增長起到反向作用。[5]阿坎德(Arcand)等人采用多種計量方法,對130多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1960—2010年間的面板數據進行檢驗,結果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呈現出倒U型的關系,即金融的增長效應存在“門檻”效應,當私人信貸對GDP的比例超過100%之后,金融開始對經濟增長產生抑制作用。[6]人們將他們的觀點稱之為“金融發展過度理論”。
從現實來看,金融詛咒現象被兩位英國學者高度重視還在于發達經濟體各國存在的種種亂象。
一是債務規模日益擴大,杠桿率不斷攀升。在經濟金融繁榮發展階段,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普遍經歷了債務規模迅速擴張的過程。以美國為例,1980—2016年間,其債務規模尤其是金融部門的債務規模以空前的增速擴張,政府和個人債務總額由3萬億美元擴張到41萬億美元*資料來源: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729/15557995_0.shtml.。
較之債務規模的絕對值,杠桿率更能夠體現債務負擔水平,杠桿率的大幅度提高是金融發展過度最直接的一個表現。從政府部門來看,杠桿率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債務與GDP的比例。表1給出了美國、英國和希臘從2001年到2016年的政府部門杠桿率,可以看到美國和英國的杠桿率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呈現出穩定增長的態勢,在金融危機過后由于政府為實施救助計劃所采取的大規模舉債措施而逐漸升高至100%左右。相比之下,希臘的政府杠桿率遠超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60%的上限,在2009年歐債危機爆發時一度高達124.6%,幾欲破產,在最終繼續獲得歐盟援助之后,主權債務進一步擴大至170%之多,嚴重拖累該國經濟復蘇。

表1 美國、英國、希臘政府部門杠桿率 單位:%
從金融部門來看,杠桿率的提高來自于金融衍生產品的層出不窮,再加上金融衍生產品大多采用保證金交易,杠桿率被進一步放大。例如,20世紀90年代后,美國金融機構為了規避資本充足率的管制,紛紛設立特殊投資實體并進行資產證券化操作,將高風險的資產轉移到資產負債表外,大大提高了貸款、債券的杠桿率。表2給出了1999年到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期間,歐元區國家和美國金融部門的杠桿率,其水平遠高于國民經濟其他部門,造成中央銀行失去對貨幣發行量的控制能力,使得金融系統流動性風險大大加強。
從非金融部門來看,在金融業繁榮發展、規模擴張時期,社會中的資金充裕、價格較低,實體經濟往往也出現借貸高漲的現象。20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泰國非金融部門的杠桿率一路走高,最終隨著金融泡沫破裂、社會生產蕭條而逐漸下降。21世紀初,英美國家的非金融部門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見表3)。

表2歐元區國家、美國金融部門杠桿率 單位:%

表3美、英、泰國1991—2016年非金融部門杠桿率(不包括政府部門債務) 單位:%

續前表
從居民部門來看,杠桿率的提高來源于信貸消費的擴張、家庭債務的增加。社會處于經濟繁榮周期時,大量資金被配置到股市、樓市中,出現全民忽視高風險、一味瘋狂追逐高利潤的現象,而很少有人意識到自己背負的杠桿效應。例如, 2001年—2007年,美國家庭債務總額(含住房抵押貸款和信用卡消費額)由7萬億美元激增到14萬億美元,家庭債務占家庭收入的比重達到了“大蕭條”以來的峰值水平。[7]表4給出了美國、英國和歐元區國家在金融危機前后居民部門桿桿率的變化情況:

表4美國、英國和歐元區居民部門杠桿率 單位:%
二是金融投機泛濫,商品過度金融化。在一個金融發展過度的社會中,金融投機行為大肆蔓延,金融創新衍生產品層出不窮,并且越來越多流動性低的資產被轉化為流動性高的金融資產,出現商品過度金融化的現象。
首先,傳統金融產品通過證券化等一系列操作產生大量的金融衍生品。例如,2007年中期,美國影子銀行的規模達到了67萬億美元,成為全球投資者進行金融投機獲利的場所,而2008年末,隨著金融危機蔓延擴大,大量投機資金撤離,美國影子銀行規模急劇縮減到56萬億美元,一年半的時間內減少了11萬億美元。[8]
其次,普通商品被賦予金融屬性,按照金融規則進行交易。根據張成思等人的研究,商品金融化分為高中低三個層次,房地產可以被界定為高金融化層次的商品,諸如大豆、白糖、棉花等有期貨市場的可以被界定為中等金融化層次的商品,而蔥姜蒜等普通商品則被界定為低金融化層次商品。[9]出現金融詛咒的社會,往往表現出在三個層次上的商品金融化程度同步加強的現象,具體來說,高金融化層次的商品,其金融屬性被不斷強化,甚至固化成為典型的金融工具,例如美國房地產抵押貸款已經脫離了基本的購房支持功能,而是幾經打包出售成為金融投機的工具;中等金融化層次的商品,其交易更加頻繁,交易規模不斷增大,商品期貨市場不再是為了規避現貨價格的波動風險,而是成為金融機構投機的重要場所。例如,美國金融機構投資到各種與指數相關的商品期貨市場的市值由2003年的150億美元激增到2008年中期的2 000億美元;而低金融化層次的商品范圍則不斷擴大,居民生活用品的交易價格脫離使用價值。
三是金融機構盲目擴張、關聯復雜,以至“大而不能倒”。歷史經驗表明,越是規模大的金融機構,在出現問題時獲得政府救助的可能性越大。例如,美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現過銀行倒閉高潮,但是并沒有引發金融危機,主要原因在于大銀行得到了政府的救助,而關門倒閉的都是規模較小的銀行。在1998年俄羅斯金融風暴中,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遭到了巨額虧損,考慮到該金融機構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的復雜關聯性,美聯儲安排摩根、美林等15家金融機構向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注資37.25億美元,使其避免了倒閉的厄運。在本輪金融危機中,美聯儲同樣救助了規模更大的花旗集團、AIG、美國銀行等金融機構,放棄了規模相對較小的雷曼兄弟、美林證券等。這種現象激勵了大型金融機構冒更高的風險,盲目擴張規模、過度發展,最終誕生了“大而不能倒”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
四是就業過度金融化,教育顯現金融熱。金融業的利潤過高、金融從業人員的收入過高,吸引了大量人才從政府部門以及制造業等其他部門流失到金融部門。由于金融行業輕資產的特點降低了該行業的進入和退出壁壘,因此伴隨著高端人才向金融行業聚集的同時,大量不具備金融從業素質甚至文化水平較低的人,也涌入金融業,從事著與資金運轉相關的投資咨詢公司、典當行、小額信貸公司等金融工作。金融就業熱也帶來教育的金融熱。在美國,金融、金融工程、經濟、精算、市場營銷等商科類專業受到了空前追捧,這就從人才培養鏈的上游深化了金融行業對于人才的攫取程度,導致未來的人力資本結構呈現出向金融行業傾斜的特點,也就使得其他產業人才流失的危害將在未來更長一段時間內持續顯現。
五是貨幣資金空轉,金融體系自我循環。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極大放松了金融管制,促使金融行業繁榮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虛擬經濟部門在經濟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金融資本擺脫了物質形態的束縛,具有極高的自主性和靈活性。當證券市場繁榮時,房地產市場相對蕭瑟,資金流入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場,當證券市場疲軟時,房地產市場崛起,此時大部分資金又會流入房市,進而形成在FIRE(Finance、Insurance、Real Estate)行業內部自我循環的封閉鏈條。此時企業的主要目標不再是企業利潤最大化,而是股東價值最大化。導致大量企業的資金不是投資于實際經營,而是用于虛擬經濟領域,造成資金的嚴重脫實向虛。
二、金融詛咒的后果及效應
(一)抑制經濟增長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重創發達經濟體,世界經濟因此受到嚴重拖累。據世界銀行統計,美國、日本、歐元區的經濟增長率分別從2007年的2.2%、2.1%和2.7%下降到2008年的1.1%、-0.7%和0.7%,2009年又分別下降為-2.5%、-5.4%和-4.0%。世界經濟的增長率從2007年的3.6%下降到2008年的1.9%,2009年則降為-2.2%。危機至今,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緩慢,美日歐主要發達國家的實際GDP增長均遠遠低于潛在產出的預測值。美國經濟學家多明格斯和夏皮羅(Dominguez & Shapiro)的研究表明,盡管20世紀50—80年代美國出現了多次經濟衰退,但之后經濟復蘇時期的增長率都要高于正常趨勢。然而,2007—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美國經濟的增長率卻始終低于長期趨勢。[10]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長期處于低迷的罪魁禍首就是金融詛咒,即金融的非理性發展抑制和損害了經濟發展的動力。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渠道來進行考察。
一是造成資源錯配,阻礙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影響經濟增長的諸多因素中,全要素生產率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一個金融部門規模過大、金融產業過度繁榮的社會中,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居民將更多的資金配置到金融投機中,導致與金融相關的領域投資過度,而與實體經濟相關的領域投資不足,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相關的各項活動因面臨較強的融資約束而無法實現,最終阻礙了一國的長期經濟增長。
二是導致創新動力不足,妨礙社會創新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創新需要科技人才,而金融部門會過多剝奪制造業人才,造成人才流失,會嚴重傷害那些需要技術人才的科技部門,高科技行業由于缺少足夠的研發人員而創新不足。另一方面,創新活動是一項投入較高,但是不確定性和風險也較高的活動,因此受到極大的融資約束,在一個經濟過度金融化的社會,更多的公司會為了圈錢而上市,而上市之后管理層的創新動力會大打折扣。 沙伊·伯恩斯坦(Shai Bernstein)以美國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上市會改變公司的創新戰略,由內部創新導向轉變為外部收購導向,內部創新水平和質量會出現明顯下降。[11]
三是加速虛擬經濟膨脹,促使實體經濟空心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金融部門快速發展,金融創新層出不窮,加速了虛擬經濟的膨脹,擠壓其他產業的發展空間。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對那些以向全球提供金融服務作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和地區而言,大量資金以美元的形式涌入,導致對當地貨幣的需求增多,使得匯率上漲,同時大量的熱錢涌入,購買房地產等資產,提高了當地的物價水平,匯率和物價的上漲,使得其他重要出口行業缺少競爭力而逐漸萎縮,導致整個實體經濟空心化。
四是金融危機救助成本高,拖累經濟恢復與增長。金融發展過度帶來的大衰退會給實體經濟帶來巨大成本,導致失業率上升、公共產品減少。從表5可以看出,在本輪金融危機救助過程中,歐美主要發達國家的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較大,而與此同時,危機又導致財政收入的銳減,這就引起這些國家財政赤字的快速增加,給未來經濟發展帶來極大的負擔和隱患,擠壓了未來經濟發展的空間。從當前經濟現狀來看,只有美國的救助計劃是相對成功的,不僅收回了當時的救助資金,還獲取了一定的投資收益,其他國家仍然深陷經濟危機的泥潭,進退維谷。

表5歐美主要國家與危機有關的財政支出占本國GDP的百分比* 單位:%
(二)誘發金融危機
當一國處于高負債、高杠桿率的狀態時,任何微小的負面沖擊都可能會通過高企的債務水平、杠桿率以及錯綜復雜的金融網絡被無限放大,進而引起國家資產負債表嚴重失衡,最終導致金融危機。
一是高負債狀態下借款人將面臨更多風險。首先,高負債往往表現為短期債務水平較高,這就帶來較大流動性風險和利率風險;其次,如果外幣貸款占比較高,借款人還需應對較高的匯率風險;再次,過度依賴于債務融資而非股權融資的企業,對營收下降的敏感性較高;最后,過度借債的主體極易因償債能力不足而面臨破產厄運。
二是負債規模較高會扭曲經濟的自動穩定機制。高杠桿狀態下,資產價格的波動會嚴重干擾財富和消費。在經濟繁榮期,資產價格高漲會帶動抵押物的價值升高、債務貶值,從而進一步擴張全社會借貸規模,加劇了泡沫的形成。在經濟下行期,資產價格走低會拖累抵押物的價值下跌,從而限制借款人的借貸能力,使得本就萎縮的經濟體進入去杠桿周期,不利于經濟復蘇。
三是金融部門在高杠桿狀態下積聚大量潛在風險。流動性是金融部門健康運行的重要指標,根據《巴塞爾協議》,銀行資金充足率與其風險加權資產數量有關,如果風險加權資產多,就需要更多地留存資金,可供借貸的資金就會減少,以控制借貸風險。但金融機構為牟取暴利,會進行一系列創新而無限放大杠桿以避開嚴格的監管,從而導致金融部門的流動性往往經歷急劇變化,并通過溢出效應使得整個金融體系極不穩定。美國資貸危機的爆發就是商業銀行過度創新,放大信貸規模,積聚大量風險的惡果。
四是政府財政政策在高杠桿狀態下失效。首先,政府的高負債提高了,公眾對政府未來提高稅收的預期而減少當前消費,從而使政府財政政策大打折扣;其次,為擴大投資的政府借貸行為會擠出民間投資,降低了政府投資對經濟的刺激效應;再次,政府高負債使得社會懷疑政府的償債能力,從而其主權信用評級可能遭到降低,進一步惡化一國企業債券的發行環境,最終對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三)左右政策制定
1952年,美國的金融資產總量為1.47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4.11倍,1965年上升至4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5.5倍,到2007年底,已經達到156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1.12倍,56年里增長了105倍*GDP 數據來源于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http://www.bea.gov/industry/io_histannual.htm,金融資產數據來源于美聯儲: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z1/20060309/。。金融資產的龐大規模加強了金融部門的話語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政府政策的制定過程。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認為,金融部門過大對政治的影響主要來自于三個方面:旋轉門效應(the revolving door)、競選經費支持(campaign contributions)和理念灌輸(ideology)。[12]
一是“旋轉門”效應。旋轉門是指個人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穿梭,為利益集團牟利。一方面,在金融業工作的原政府官員可以通過私人關系對政府官員和政策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在政府部門就職的原金融從業人員可以將金融理念植入政府部門中。美國多任財政部長都曾經在高盛擔任要職。美聯儲前任主席伯南克在《行動的勇氣》一書中披露,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提出的解決危機的最終方案,最終方案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13]
二是影響競選活動。金融部門獲取的巨額財富促使該部門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話語權。在通過武力獲得權力的時代流行一句諺語,“對通用汽車好的就是對美國好的(What is good for General Motors is good for USA)”,后來逐漸演變成“對華爾街好的就是對美國好的(What is good for Wall Street is good for USA)”。由此可見,話語權已經從制造業轉移到金融行業中來。當前,金融業已經成為美國政治運動,例如總統大選的最大貢獻者。
三是理念灌輸。金融業的快速擴張對學術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金融學家在金融機構擔任兼職,這種交叉身份嚴重干擾了學術研究的客觀性和獨立性,經濟學家在潛意識中帶有了主觀身份,難免成為服務對象的喉舌,進而通過其課堂講授和論文著作,對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產生嚴重影響。
(四)擴大收入差距
經濟金融化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美國近50年來最為突出的問題。收入差距隨著金融發展程度的提高而呈現出擴大化的趨勢,其主要機制:
一是金融部門報酬過高。與其他國民經濟部門相比,金融部門從業人員在高收入群體中的占比明顯較高。在美國,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當中,金融從業者占了13%的比例,而最高的0.1%的人群當中,金融從業者的比例高達18%,遠高于其他行業。[14]鮑里斯·庫爾內德(Boris Cournede)等人研究了OECD國家的收入分配情況發現,在收入最低的1%的人群當中,僅有1%的人從事金融行業,但是在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中,有19%的人從事金融行業。金融從業人員享受著金融部門帶來的“行業溢價”。[15]
二是富人通過金融資產獲得較高財產性收入。金融資產主要掌握在富人手中,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財產性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據的比例越來越高,成為拉大收入差距,造成貧富不均的主要因素。
三是高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面臨的信貸約束不同。個體能力差異、資本逐利性、金融資源獲取的門檻效應、內部人設置障礙等都使高收入者更容易獲得金融資源,從而撬動更多財富、實現收入的更快增長。蒂瓦里(Tiwari)等利用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ARDL)對印度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檢驗發現,金融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該國的收入不平等。[16]賽文和焦什昆(Seven & Coskun)對新興市場國家1987—2010年的動態面板數據進行考察發現,金融發展促進了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但并未使低收入群體受益,因而加劇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17]
三、金融詛咒假說對我國的啟示
第一,高度重視高杠桿累積的潛在風險,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
2008年以來,我國政府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而采取了多種經濟刺激手段。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雙重作用之下,全社會融資規模激增,企業和地方政府負債率高企,總債務占GDP比重不斷攀升。2015年以來,國際金融機構和組織對中國的杠桿率估計普遍在200%以上,甚至超過300%,接近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水平。[18]更令人擔憂的是,以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民間借貸等形式存在的影子銀行體系,其信貸規模難以估算,真實杠桿率可能遠高于當前公布的數據。而影子銀行體系的資金來源和業務與正規金融體系盤根錯節,極易向正規金融體系傳遞風險,一旦缺乏有效防火墻, 會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和傳染。
一路走高的杠桿率強化了經濟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當前的重要任務是通過多種改革措施逐步降低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債務規模和比例。對于政府債務,尤其是地方政府債務而言,短期來看要盡快排查摸清債務規模,并積極推進地方債務置換工作,以快速降低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長期來看要改革稅制,建立一般轉移支付制度,構建地方政府債務防控的有效機制;對于金融部門來說,要加強對金融機構的創新監管,審慎推進金融衍生品業務的開展,強化有效的信息披露和風險揭示制度,嚴控金融過度創新帶來的杠桿不斷攀升;對企業部門來說,要通過推進兼并重組、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強化自我約束、盤活存量資產、優化債務結構、有序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依法破產、發展股權融資,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就居民部門來說,要健全個人征信系統的有效性,加強對居民貸款的審查,避免向不合格客戶發放貸款,以確保守住不發生個人信貸風險引致的系統性金融風險。
第二,謹防金融過度發展,實現金融發展和實體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
近三十余年來,我國金融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到2016 年底,中國金融行業增加值占GDP 的比例已經高達9%。雖然目前我國尚未進入金融發展過度階段,但是相比實體經濟而言,金融部門的發展步伐過快、過大,已經出現金融與實體經濟發展速度和結構不匹配的現象。尤其是在信貸市場上,金融資源錯配情況嚴重,一方面是資金主要流向利潤高、周轉速度快的行業,金融領域投資過度,貨幣在金融體系內空轉的現象日益突出,而另一方面則是資金不愿意流入那些回報周期長的項目中,制造業尤其是民營制造類企業融資難、投資意愿低,以至于產業結構日趨失衡,產業轉型升級步履維艱。這種現象需要我們高度重視,防患于未然。
一方面,從總量上匹配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大力推進普惠金融體系的建設,擴大金融資源覆蓋面,積極引導社會資金流向中小微企業、“三農”領域等薄弱環節;另一方面,要加快推進金融體制改革,通過金融業雙向開放,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以及推進利率市場化,大力發展綠色金融等措施,合理配置金融資源,確保金融產品創新依托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引導金融資源支持產業結構調整,支持高新技術、綠色能源等產業的發展;通過改善金融約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逐步形成創新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模式,確保實體經濟高質量可持續地發展,從而實現金融發展和實體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
第三,打擊金融過度投機,維護市場穩定秩序。
近年來,我國的金融投機行為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2015 年我國股票市場在政策刺激之下一路飄紅,出現了全民炒股的盛況,各種配資加杠桿亂象叢生,導致市場大幅度異常波動。與此同時,我國房地產市場價格一直攀升,社會資金大量涌向房地產市場。在股市與樓市交替火熱的當下,若不對金融投機加以有效控制,將會積聚大量風險,極易觸發金融危機。因此,加大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力度,擠出金融市場泡沫,降低金融市場風險,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風險是我國今后一段時期的主要任務。
第四,調整財稅政策,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分配不公。
近年來,在高收入的驅動之下,越來越多的畢業生選擇金融行業就業。根據我國教育部直屬的75 所高校發布的就業質量報告來看,綜合類大學的就業去向中,金融類工作遙遙領先,以2016 年為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一流高校的金融類就業比例均為榜首,接近或者超過20%。中國科學院院士施一公教授認為,“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19]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應通過財稅政策的設計和轉移支付制度的改善,實現稅收對金融部門從業人員報酬過多以及資本利得畸高的調節,將金融部門的超額利潤以合理有效的方式轉移到提高社會各行業的協調發展,以縮小收入差距、改善分配不公。
參考文獻:
[1] Shaxson N, Christensen J.The Finance Curse, How Oversized Financial Center Attack Democracy and Corrupt Economies? Tax Justice Network[EB/OL]. http://www.taxjustice.net/topics/finance-sector/finance-curse/,2013-05-29.
[2] Krugman P. The Market Mystique[N]. New York Times, 26 March, 2009.
[3] Turner A. Mansion House Speech[EB/OL]. http://www.fsa.gov.uk, 2009-09-22.
[4] Rousseau P.L., Wachtel P. 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epening on Economic Growth? [J]. Economic Enquiry, 2011, 49(1).
[5] Rajan R. G. H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kes the World Riskier?[Z]. NBER Working Paper, 2005, (11728).
[6] Arcand J.L., Berkes E., Panizza U. Too Much Finance?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5, 20(2).
[7] 馬建堂等.中國杠桿率與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J]. 財貿經濟, 2016,(1).
[8] Guttmann R. Finance-led Capitalism: Shadow Banking, Re-Regulation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Market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9] 張成思,劉澤豪,羅煜.中國商品金融化分層與通貨膨脹驅動機制[J]. 經濟研究,2014,(1).
[10] Dominguez K., Shapiro M. Forecasting the Recovery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 Is This Time Different?[Z]. NBER Working Paper, 2013, (18751).
[11] Bernstein S. Does Going Public Affect Innovation?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5,70(4).
[12] Johnson S. The Quiet Coup[J].The Atlantic, 2009,(5).
[13] 本·伯南克.行動的勇氣——金融風暴及其余波回憶錄[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14] Bakija J, Cole A, Heim B. T. Jobs and Income Growth of Top Earners and the Causes of Changing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US Tax Return Data[Z]. Williams College, 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and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15] Cournede B, Denk O, Hoeller P. Finance and Inclusive Growth[R]. OECD Economic Policy Paper, 2015,(14).
[16] Tiwari A K, Shahbaz M, Islam F. 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crease Rural-urban Income Inequality?: Cointegration Analysis in the Case of Indian Econom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013, 40(2).
[17] Seven U, Coskun Y. 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Evidence from Emerging Countries[J].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2016,26(3).
[18] 鳳凰國際. 中國債務情況非常令人擔憂,因為沒人知道實情[EB/O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519/14396588_0.shtml, 2016-11-19.
[19] 鳳凰教育.施一公院士:中國大學的導向出了大問題[EB/OL].http://edu.ifeng.com/a/20141207/40894968_0.shtml, 2016-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