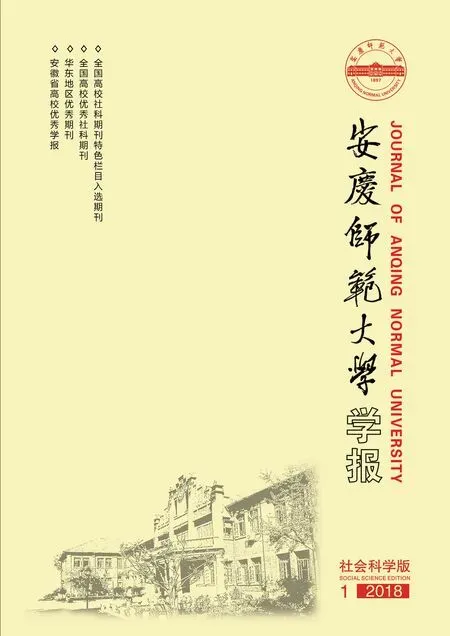吳 彬(安慶師范大學文學院,安徽安慶246011)
中華劇藝社(簡稱中藝)是抗戰時期出現的著名劇團,存在時間達六年之久,演出劇目數十部。作為在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指導下創辦的民營職業劇團,中藝引領并推動了大后方戲劇運動的蓬勃開展,為中國話劇迎來了黃金時代。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功勛卓著的劇團,有關它的研究卻相當薄弱,甚至連一些基本事實都沒有搞清,嚴重影響了中國話劇史的書寫。作為抗戰時期的職業劇團,中藝能夠成為話劇運動的領頭雁,是與其演劇實踐分不開的。為了推動劇運開展,擴大話劇的影響力,在演劇活動中,中藝曾采取多種演出體制,既有“連演”,亦有“聯演”。其中,聯演制的推行,團結了大批進步劇人,帶動了當時眾多演劇團體,使他們在認識一致的前提下能夠共同行動,并肩戰斗。聯合演出,最終推動了戰時話劇運動的蓬勃興起。
一、認識到聯演的重要
作為民營職業劇團,中華劇藝社是在皖南事變后成立的。成立之時,考慮到政治環境的險惡與經濟的困難,只組成了二、三十人的班底,要演出大的劇目,必須向其它劇團借角兒。從《大地回春》到《天國春秋》,再到《屈原》,這些大型話劇的演出,都曾匯集了當時重慶各劇團的精英演員。從其它劇團借角兒演出,這既是政治斗爭的需要,也是演出實際需要。這種演出往往是掛著中藝的牌子,由各劇團的成員聯合完成。就借約來的演員而言,他們只是義務幫忙而不領取薪金。雖然如此,從演出的成員構成和演出的性質來看,它已具有了聯合演出的特點。這種聯合演出,最明顯的一條就是,它使得演出做到了整體統一,保證了整個舞臺演出的高水平。一流的作家、一流的導演、一流的演員、一流的舞臺工作者,這種強強聯合使演出達到了很高水平,一方面招徠了大批量觀眾,另一方面也為劇團贏得了聲譽。使中藝劇團從第一聲炮響就在重慶站穩了腳跟。
其實,對聯合演出的意義與價值的認識,從下意識到意識,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在南岸草創期間,為解決日常開支困難,中藝曾經做過小型演出,在黃桷埡鎮上演出了三個小戲,當時參加者都是劇社的演職人員。但當第一部大戲寫出來之后,因人手不夠卻遲遲不能排演。及至在搬入重慶市區的時候,才從其它劇社借來演員正式投入排練。當時的演出廣告曾經預告說:“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紀念中華民國第四屆戲劇節聯合大公演”。其中,“中國萬歲劇團演出《陌上秋》”,“中華劇藝社演出《大地回春》”,“中央青年劇社演出《北京人》”[1]。
從這份演出廣告來看,這里所謂的“聯合演出”并不具有相互交叉的特點。聯合演出,英文表述是joint performance,joint內含有“聯合”、“連接”、“共同”的意思。而此處還是每個劇團各演各的,具有孤軍奮戰的性質。也就是說,這種聯合只是一種外部的聯系,是幾個劇團各自通過自己的演出實績來帶動和支撐整個劇運。中藝劇團向其它劇團邀角兒參演,只是因為劇團自身人員不夠所致。也就是說,它和其它劇團組織之間并沒有達成一種契約,只是部分演員出于個人的考慮主動來幫忙而已。如果這些演員所在的劇團臨時有演出,或者與中藝的演出時間有沖突的話,他們也只能對中藝表示愛莫能助。項堃在回憶中曾經提到,說是首次演出《天國春秋》時,演員正在后臺化妝,中制廠長鄭用之闖了進來,當眾解聘了應云衛、孟君謀、阮斐、吳茵、辛漢文和項堃他們幾個[2]。由此正可看出,雙方領導層之間并沒有達成一致意見,不存在那種契約關系。另如,1943年春,中制決定上演《藍蝴蝶》,廠方要路明參加演出,路明婉言辭謝,卻與姐姐徐琴芳一起參加了戲劇人士組織的《大明英烈傳》。《大明英烈傳》上演后,獲得了觀眾的贊賞和好評,但此舉卻觸怒了中制廠長吳樹勛。于是,徐琴芳被開除,路明記大過,陳鏗然受到批評教育。最終,三人都脫離了中制,稍后,隨同中藝去了成都[3]。再如為郭沫若祝壽演出。中藝向其它劇團借角兒演出《天國春秋》,這自然是觸犯了中萬的利益,以致鄭用之百撓不依。最后,由中萬演出《棠棣之花》才算平復了鄭用之的糾纏。

二、采取多種聯演方式
中藝的聯合演出方式主要有三種:一種是聯合其它劇團的演職人員,以中藝劇團的名義進行演出,這在重慶時期表現得非常明顯。如《大地回春》《天國春秋》和《屈原》等劇皆是如此。另一種是聯合其它劇團的演職人員,以這些劇團的名義演出,這在成都時期表現頗為明顯。還有一種是以中藝劇團和其它劇團共同的名義演出。如在武漢時演出的《升官圖》和回到上海后演出的《棠棣之花》,即是如此。
1941年10月11日,中藝在重慶演出《大地回春》,當時重慶版《大公報》在演出廣告中宣傳說:“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紀念第四屆戲劇節公演中華劇藝社首次大貢獻(五幕名劇)大地回春”[6]。與前面那份廣告相比較,同是說的紀念第四屆戲劇節公演,但這份廣告中明顯去掉了“聯合”兩個字。1942年2月10日,重慶版《新華日報》第三版報道說:“中電劇團、青年劇社、中華劇藝社等于晚間假實驗劇院聯合公演《孤島小景》,《女房東》,《一心堂》”。其實,這里所謂的聯合演出還是屬于各演各的劇目。其中《孤島小景》由中藝演出,《女房東》由中青演出,《一心堂》由中電演出。真正具有內部交叉性質而又具有某種契約關系的聯合演出,則是從1942年4月份演出《戰斗的女性》開始的。當時的演出廣告是這樣寫的:“中國萬歲劇團中華劇藝社為響應中國航空建設協會募集劇人號飛機聯合大公演四幕名劇戰斗的女性。”[7]兩個劇團,同臺演出一個劇目,而且,明確打出了“聯合公演”的旗號。
1943年7月初,中藝全體到達成都。之前的報紙就曾做過這樣的報道:“中華劇藝社俟《復活》演畢后即將與怒吼劇社合作,赴蓉聯合公演,劇目有《家》,《原野》,《安魂曲》,《法西斯細菌》等。”[8]這種合作演出的計劃是否逐一實現了,我們暫且不提。倒是怒吼劇社到成都的首場演出卻是具有了聯合的性質。當時,由于車輛中途拋錨及其它原因,中藝全體是較晚才到達成都的。而隨同怒吼劇社先期到達的中藝成員,如格煉、耿震、郁民和應小白等,則參加了怒吼劇社的《牛郎織女》演出。該劇演出之后,怒吼劇社返回重慶,中藝開始了《法西斯細菌》的演出。這次演出與在重慶一樣,還是那種借角兒的性質,作為主演的白楊是從重慶趕來的。
當時的成都,劇團并不算少,但是卻并沒有達成聯合。毋寧說,根本就沒有聯合的意識。眾多劇團只是各自奮戰,散兵游勇一般。加以游擊之風盛行,其劇運是相當混亂的。對此,時人曾有指責。歐陽喬治在《成都劇壇展望》中說:“成都的戲劇運動是在外貌似頗繁榮,內里卻凌亂無序,各自為政的奇突情勢下發展著的。這種奇突情勢之造成,當然自有其‘積習難反’的社會因素,但劇團與劇團之間的缺少聯絡,沒有統一劇運的領導機構與組織人才,這也未始不是其中主要的關鍵。”[9]從歐陽喬治的批評來看,當時成都的劇團存在著嚴重的門戶之見,相互不能團結一致,以致劇運力量遭到削弱。倒是中藝后來開赴成都,團結了當地劇團,通過聯合行動推動了成都劇運的蓬勃發展。成都劇運的混亂,應該是早已有之的。所以,田禽就曾指出,“成都的劇運有著很多而且很大的缺點”,并希望“有一個比較完善的大劇團來刺激一下,或者它會慢慢的好起來,否則恐怕沒有多大希望。”[10]據陳錚和李恩琪回憶,“‘皖南事變’前后,時局嚴峻,成都話劇運動,真正走向了沉寂。直到1943年金秋,重慶‘中華劇藝社’轉戰成都,成都劇運又步入了一個黃金時代”[11]。
1943年11月,也就是在旅蓉第三次大公演《家》之后,中藝聯合成都其它劇團演出了《勝利號》。這次演出并非各劇團的自愿,多少有點被迫和應付差事的意味。因為該劇是當時四川省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主任陳克成責成陳白塵、吳祖光、周彥和楊村彬等人創作的一出應景戲。對于各劇團來說,這次演出“純系義務性質”[12]。但是,這次演出卻意義重大。因為,它是“渝蓉各劇團第一次聯合大公演”,“八大劇團合作四大作家執筆五大導演杰構二十八大演員合作”。其陣容不但在重慶未曾見過,就是整個話劇運動史上也是很難見到的。它第一次把這么多劇團的演職人員組織起來,團結起來,使他們相互之間得到認識和交流的機會。這無疑對于演技的提高是很有價值的,也為日后劇團之間自由結合提供了條件。這次演出的效果,據當時報道稱:“賣座極佳”[13],甚至出現“售票處之木欄險被擠壞”[14],“走道上亦無空隙”[15]的景象。周彥回憶說:“由于演員陣容整齊,再加以陳某有權指揮的各報大肆宣傳,上坐[座]率很高每場均能滿座。”[12]看來,該劇演出獲得巨大成功當是無疑。
在《勝利號》演出之后的1944年1月份,中藝與其他劇團合作演出了《柔密歐與幽麗葉》。該劇是以神鷹劇團的名義演出的,但實際上是幾個劇團的聯合,而中藝的成員就“占十分之七”[16]。由于中藝的影響力大,劇團之間聯合不免引起反動當局的注意與迫害。結果,“重慶來的劇團,只有打道回府,‘中藝’不得不遠走川南”,而成都的“神鷹劇團”也于年底“宣告解散”,血花、前鋒等劇團則“不疾而終”,于是,造成“成都劇運又開始走向低落”[11]。
1944年1月下旬,中藝趕赴川西南一帶巡回演出。此后一年間,成都的劇運暫時趨于低潮,劇團聯合演出也告一段落。這種聯合若要再次成為劇運中的一道靚麗風景,只能等候中藝的歸來。這就是1945年8月份,為紀念賀孟斧逝世演出的《上海屋檐下》。
三、聯合學生演劇
1945年5月10日,著名導演賀孟斧不幸在重慶病逝。鑒于賀孟斧當時在劇壇的地位和影響,以及他與學生們的密切關系,社會各界舉行了捐助活動。成都的學生劇團也發起了為賀孟斧募捐的演出活動。據當時成都版《華西晚報》載:為追悼賀孟斧逝世,成都各大學劇團計劃在最近舉行聯合公演,并定于廿六日午后二時在三益公劇場舉行首次籌備會[17]。27日,《新民報晚刊》也曾報道說:“成都各大學劇團將聯合為賀氏籌募子女教育經費舉行公演,劇本或為曹禺之《蛻變》,或為夏衍之《上海屋檐下》。”[18]這一倡議是由陳翔鶴最先提出來的,應云衛表示全力支持。參加此次演劇的,有燕京大學的“海燕劇團”,四川大學的“劇藝社”、“話劇團”、“劇研社”,華西大學的“天竺劇社”,光華大學的“光華話劇團”,華西壩五大學的“學生公社劇團”等等,選定的劇本是《上海屋檐下》。
其實,夏衍所寫的戲多是冷戲,是不容易賣座的。為什么又要演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進行募捐呢?據當事人回憶說:“之所以選定《上海屋檐下》,公開的理由有三:一是該劇雖寫于抗戰前夕,除‘上海業余劇人協會’戰前在滬演出過外,抗戰以來在‘大后方’還沒演出過;二是當時‘業余’在滬演出的導演是應云衛,這回應也主動承擔導演,‘駕輕就熟’;三是《上》劇寫的是上海一幢弄堂房子的五戶人家,‘戲’雖有多有少,但家家有‘戲’,人人有‘戲’,‘主角’、‘配角’懸殊不大,安排起來比較容易,免得爭搶。其實,還有一個當時不便公開但卻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劇中那個郁悶的‘黃梅時節’的氣氛,正符合當時國統區的政治氣候。”[19]該劇演出時是以“成都大學生劇團為紀念賀孟斧先生聯合公演”的名義進行的,演出地點就在中華劇藝社的三益公劇場,共計演出20多場。前后臺一切工作和費用開支,都由中藝一力承擔。后臺工作人員如李天濟、陳永諒、雷觀京、申明山等都是中藝的人。而且,中藝的小演員毛葳和應小白也參加了演出,金淑之則中途代演了幾場。
從當時的情形來看,這次演出是相當成功的。當時報道說:“成績極好”[20],第一天演出,“觀眾踴躍,劇票當即賣完,開演時值大雨滂沱,但觀眾極佳”[21]。最后,演出凈收入達二十萬元,悉數捐贈賀氏子女。當然,誠如當事人所言:“其成功之處,倒不在于演出的水平,而是這次‘聯合演出’,在成都還是一個創舉。應該承認:參加的單位多,人多,政治面貌很復雜”。所以,名曰“聯合演出”,實際上,在這中間,“既有聯合,也有斗爭”[19]。這次演出,更為重要的是,它是職業劇團和學生業余演劇的一次大聯合。在這種聯合中,職業與業余相互幫助,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并肩作戰,共同扛起了演劇運動的大旗。紀念賀孟斧,其實就是對多年來劇運的充分肯定和支持。當時在成都,中藝“只是一花獨放,一枝獨秀”[11],不免有孤軍奮戰之感,眾多學生劇團的參與,無疑對于人心的鼓舞和劇運的推動起了重要作用。
四、在困難中堅持聯合演劇
就在《上海屋檐下》演出期間,八年抗戰在慘勝中結束。中藝在成都又演出4臺戲之后,便于1945年年底返回了重慶。之后,在重慶先后上演了《孔雀膽》《棠棣之花》《升官圖》《雷雨》《北京人》和《結婚進行曲》等6個劇目。其中,《升官圖》是中藝演出的最后一個新戲。
歷史往往充滿了巧合。中藝在重慶創始的時候,是以陳白塵的《大地回春》開鑼并打響第一炮的。當劇社結束在重慶的歷史的時候,也是以陳白塵的劇作收兵的。而且,更為巧合的是,開鑼戲收兵戲也是幾個劇團的聯合。如果說《大地回春》的演出是因為人手不夠,而又怕國民黨搗鬼的話,那么《升官圖》的演出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當時復員聲聲,許多主要演員已經踏上了復員回滬的征途。由于《升官圖》一劇含有強烈的諷刺性和對時政的批判,應云衛雖然想演出,卻又不敢冒這個險。最終,找到一個折中的辦法,與新成立的現代戲劇學會聯合演出。這樣才算光榮地收場。
雖然,中藝在短暫的演出后即離開了重慶復員回滬,但是,作為一種演出方式,聯合演劇卻一直沒有被放棄。而且,比以前提得更響,重視更甚。1946年9月,中藝復員,途徑漢口,并在漢口待了三個月,演出了三個劇目。值得注意的是,中藝在漢口的首場演出,便是與武漢行轅政治部政工大隊聯合公演的《升官圖》。據當時《新湖北日報》報道:中藝到漢口伊始,在一次招待會上,便明確表示“將在漢聯合演劇,希各界協助”[22]。就中藝而言,從客觀環境來說,這次聯合演出,蓋因作為外來劇團,他們面臨著劇場緊張的困難,需要借重當地劇團以利于實際問題的解決。從主觀上來說,當時中藝復員到漢口,人員只有十幾個,也不具備獨立演出大戲的能力。
中藝最后一次聯合演出是回到上海以后,也是在上海唯一的一次演出,即1947年4月間與觀眾演出公司聯合演出的《棠棣之花》。這次聯合,在中藝方面,既有主觀的要求,也有迫不得已之處,因為劇團在復員途中,曾經遭遇了一次覆舟之災,“全部道具布景隨大江東去”[23],“押運人員則狼狽抵達南京”[24]。當時,劇團是靠社會接濟才勉強回到上海的,他們已經失去獨立演劇的家底,所以,必須聯合其它劇團。而聯合演出,也一直是應云衛所提倡的。據當時上海版《時事新報晚刊》載:應云衛從漢口來到上海聯系劇場,并希望各劇團聯合演出以重振話劇,但僅覓得“觀眾演出公司”與之合作[25]。
1947年4月5-22日,中藝與觀眾演出公司在辣斐劇院聯合演出《棠棣之花》,但因拆賬等問題,觀眾演出公司在第二輪演出該劇時就沒再聯合中藝。而中藝因劇場問題等諸多原因,也再無力獨立演出。不過,聯合演劇的呼聲卻在當時的情況下有增無減,而且最終達成共識。據6月8日上海版《和平日報》載:六月五日下午三時,在海光劇院,熊佛西面對新聞界做報告,稱今年夏季,上海市話劇團聯誼會將組織包括中藝、新中國、上藝、中萬在內的滬上十一個劇團輪流演出。這是目前所見到的舊報紙中最后一次對中藝的報道。然而,當天上海版《時代日報》在其《海光劇院改演話劇舉行劇界聯歡大會》的報道中并未提到中藝,只是說中藝成員應云衛、秦怡、吳祖光等參加聯歡大會,并將于八、九兩日獻演節目。據《和平日報》所載:今日“上海話劇院一家家皆改放電影”,“海光是劇運中一個新搶作,但辣斐六月底要結束了,因房子被房東收回,以后話劇演出唯海光一家經常演出之場所了”[26]。
不管這次提出的聯合演劇對于中藝來說是否曾經進行了,但從這種聯合的趨向來看,足以看出中藝對聯合演劇這種形式的重視。而這種聯合演劇,在推動戲劇運動方面也確實起到了應有的作用,它團結了大批進步的戲劇工作者,共同為劇運、為抗建而努力奮斗著!
抗戰期間,中國話劇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這種輝煌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以中華劇藝社為代表的諸多進步劇團的精誠團結和并肩作戰。正是因為它們的不懈努力與聯合演出,最終撐起了戲劇藝術的一片藍天。
[參 考 文 獻]
[1]記者.演出廣告[N].新華日報(重慶),1941-10-11(2).
[2]項堃,項智力.瑣憶《天國春秋》[J].戲劇與電影(成都),1983(8).
[3]李箴.從泥濘的路上走來——記徐琴芳、陳鏗然、路明[J].戲劇界(合肥),1987(6).
[4]吳彬.中華劇藝社創立始末考[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2015(3).
[5]一哉.北碚演劇尾聲[N].時事新報(重慶),1942-10-02(4).
[6]記者.演出廣告[N].大公報(重慶),1941-10-11(4).
[7]記者.演出廣告[N].新華日報(重慶),1942-04-25(4).
[8]記者.劇訊一束[N].新華日報(重慶),1943-05-03(3).
[9]歐陽喬治.成都劇壇展望[N].新華日報(重慶),1943-01-14(4).
[10]田禽.成都的戲劇報導[N].時事新報(重慶),1942-10-30(5).
[11]陳錚,李恩琪.抗戰時期成都的話劇[J].成都黨史,1995(4-5).
[12]周彥.記《勝利號》在成都的演出[J].抗戰文藝研究(重慶),1982(3).
[13]記者.文化圈[N].華西晚報(成都),1943-11-20(4).
[14]記者.文化圈[N].華西晚報(成都),1943-11-22(4).
[15]記者.文化圈[N].華西晚報(成都),1943-11-26(4).
[16]記者.文化圈[N].華西晚報(成都),1943-11-01(4).
[17]記者.大學劇團聯合公演追悼賀孟斧并發揚學校劇運[N].華西晚報(成都),1945-05-24(4).
[18]記者.藝文壇[N].新民報晚刊(成都),1945-05-27(4).
[19]任耕.回憶《上海屋檐下》在成都[J].抗戰文藝研究(重慶),1982(3).
[20]記者.中藝劇團準備赴上海[N].華西晚報(成都),1945-08-23(1).
[21]記者.成都屋檐下[N].華西晚報(成都),1945-08-15(1).
[22]記者.武漢零縑[N].新湖北日報(漢口),1946-09-29(2).
[23]記者.藝文壇[N].上海新民報晚刊,1946-09-15(4).
[24]岑.應云衛悲嘆行路難![N].上海新民報晚刊,1946-09-06(3).
[25]木尊.畢生心血化于劇團 應云衛表示:話劇決難消滅[N].時事新報晚刊(上海),1947-03-11(3).
[26]何為.上海話劇工作者的夏季攻勢十一個劇團輪流演出[N].和平日報(上海),1947-06-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