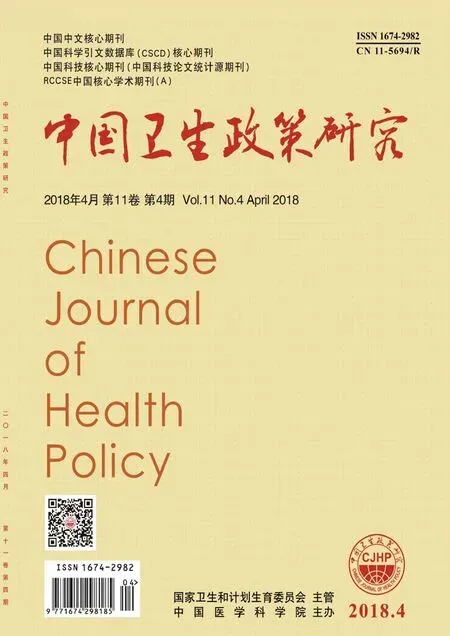衛生技術評估決策轉化動力的量表開發
劉文彬 陳英耀 施李正 龐偉明 董恒進
1.福建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福建福州 350004 2.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衛生部衛生技術評估重點實驗室 上海 200032 3.美國杜蘭大學公共衛生和熱帶病學院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市 70112 4.加拿大勞倫森大學鄉鎮和北部衛生服務研究所和北安大略省醫學院 美國西比利市P3E 2C6 5.浙江大學醫學部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政策學研究中心 浙江杭州 310058
目前,我國衛生技術評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雖已獲得一定發展,并在應用HTA證據輔助決策方面積累了一些經驗,但整體而言,我國衛生技術評估目前更傾向于單純的學術活動,衛生技術政策的制定、實施和效果評估等方面還未形成有機整體,對衛生政策決策的影響仍十分有限,即決策轉化不足。[1- 2]為促進HTA研究結果的決策轉化,對其決策轉化動力進行科學的評估測量是亟待解決的理論問題。因此,本研究擬通過對前期研究成果的理論分析,界定決策轉化的概念、明晰其內涵要素,進而開發衛生技術評估決策轉化動力的測量量表。
1 決策轉化的概念界定
決策轉化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特殊的知識轉化。根據前期理論研究的主要結果,知識轉化可被界定為“在研究成果產出方和使用者等利益相關者互相合作的復雜系統內,交流、整合并有效及時地將合乎倫理的相關知識運用于實踐的全過程”[3-5],它強調知識轉化需要研究成果產出方、使用方等多方面的共同推動;同時,知識轉化不單是知識傳播或交流,還包括促進各利益相關方之間的聯系和互相理解、循證決策和循證證據的指導、運用于實踐的反饋、知識的整合修訂等過程[6]。
決策轉化除了包含知識轉化“需要各方共同推動”、“涵蓋從知識成果產生到推廣運用的全過程”等上述基本特征之外,還具有以下特點:如轉化的知識成果更多涉及對某些技術的安全性、有效性、經濟性和社會倫理的綜合評價,知識成果的使用方主要涉及衛生技術管理的決策方(包括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醫保及其附屬司局處室、以及各地方的相關管理機構及決策人員),轉化的目的更多聚焦決策支持、政策制定、政策推廣等。
2 HTA決策轉化動力的內涵要素
基于上述決策轉化基本特征、結合前期相關研究結果,本研究將HTA決策轉化動力整合歸納為證據影響力、機構支持力、渠道聯接性、交流協作度、決策方推動力五個方面內涵要素。
2.1 證據影響力
HTA研究能否產出既科學嚴謹又貼近決策需要且有實用性的研究結果或研究證據,將決定其對決策的潛在影響程度,亦對相應研究結果的決策轉化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同時,選擇合適的時機提交發布研究證據或研究結果,也有利于促進其決策轉化。[7-9]
2.2 機構支持力
研究人員所在機構的支持情況,也被認為是轉化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一些機構對研究人員提供研究成果決策轉化的培訓,提供相應指南并安排專業人員提供技術支持,在考核激勵措施制定上強調研究結果的決策應用情況(如研究報告獲得領導批示、研究結果被引用為決策依據等),這都將促進相關研究結果的決策轉化。[10,11]
2.3 渠道聯接性
在衛生服務體系中,宏觀管理者、服務提供者、購買者等利益群體對相關衛生技術在安全性、有效性、經濟性以及社會倫理等方面的研究證據有極大的需求。同時,不同利益群體的價值判斷標準也有所不同。[12- 13]為了充分表達或了解需求、傳遞整合有關研究證據結果,進而促進其決策轉化利用,研究方和相關利益群體之間必須著力于構建相互緊密聯接的溝通渠道。
2.4 交流協作度
決策轉化不僅僅是向決策方傳遞知識信息,它還強調研究方和決策方之間的溝通交流和通力協作。[14- 15]如在課題啟動階段,雙方交流有助于明確研究目標,確保課題與決策需要高度相關;而在課題正式推進過程中的溝通交流,將有助于解決課題遇到的困難、更準確深入地分析課題研究結果,并為后續成果傳播和決策利用打下良好的基礎。
2.5 決策方推動力
決策方的推動作用也是轉化動力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16,17]決策方首先需要克服傳統決策模式中決策過程非透明化、對使用科學證據要求不嚴格(甚至只重經驗、漠視證據)等方面的不良影響;在接收相應HTA研究結果或文本之后,能夠正確解讀并綜合判斷是否將相應HTA研究證據運用于決策;對擬用于決策的研究證據,能以一定積極性推動其決策轉化。這些對于實現成功決策轉化均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3 量表開發
3.1 量表編制
基于對HTA決策轉化的概念界定和內涵要素歸納,結合文獻研究結果,本研究明確了“證據影響力”、“機構支持力”、“渠道聯接性”、“交流協作度”、“決策方推動力”五個量表維度,在此基礎上設計具體測量條目;采用Likert 五分制,對決策轉化動力的各個指標進行測量。本研究也選擇一些與決策轉化、決策利用相關的且已被證實有較高信度效度的測量問題加入問卷。通過咨詢本研究領域相關的國內外專家,針對調查問卷的內容、結構、表達措辭等進行適當調整及修改完善,整理形成調查問卷初稿(表1)。

表1 研究者決策轉化動力的維度和對應問卷問題
3.2 數據收集與樣本情況
為檢驗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進一步運用量表對HTA研究人員開展問卷調查,相應調查對象應符合以下條件:(1)就職于國內開設有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或藥事管理的大學,或者設有衛生技術評估或藥物經濟學評價部門的專業協會和專業研究機構;(2)近三年內開展過針對藥物、醫療器械、衛生材料、醫療方案、醫學信息系統、后勤支持系統和行政管理體系等衛生技術的功效、安全性、成本和效益(效果)及社會影響(倫理、道德等)的評價研究。
在實際調查中,由于難以獲得國內HTA研究人員的完整名單以開展隨機抽樣,故首先調查國內成立最早的衛生技術評估機構,通過相關評估機構研究人員的介紹,繼續向其他HTA研究人員發放調查問卷。隨調查問卷附上知情同意書,同意參加調查者填寫知情同意書;完成調查問卷并發回視為知情同意。
本研究共發放了561份問卷,對回收問卷中有多處缺漏或者有明顯填寫規律(如同一欄目內所有問題選擇同一個選項)的問卷予以刪除;對問卷中的少量缺漏,將由調查員直接郵件告知調查對象,進一步獲取其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最終回收有效問卷382份,有效回收率為68.1%。在完成調查的382位HTA研究人員中,179位為男性,占46.9%;大多數年齡在30~49歲之間;有51.8%的研究人員獲得博士學位,38.8%的研究人員獲得碩士學位;各有29.3%、28.3%和35.1%的研究人員分別獲得中級、副高和正高級職稱;大多數研究人員具有醫學和管理學專業背景,分別占64.7%和48.2%;就研究領域而言,則主要集中在組織管理體系評估(55.8%)和藥物評估(27.8%)。
3.3 探索性因子分析
為更好進行條目遴選,確定維度歸屬,隨機抽取一部分數據(n=70)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先進行KMO和Bartlett球體檢驗,KMO系數為0.755,高于經驗標準0.70,表明變量間的共同因子較多;而Bartlett球體檢驗的χ2值為1 051.987,達到顯著性水平(P<0.001),代表母群體的相關矩陣間有共同因素存在,樣本數據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在具體的因子分析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并采用Varimax旋轉方法,選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為了獲得具有理論意義的因子結構,采用以下3條標準來篩選合適的測度變量:第一,題項在某一因子上的負荷最小值為0.35;第二,題項與其它題項之間只有很低的交叉負荷;第三,某一題項的內涵必須與測度同一因子其它題項的內涵保持一致。[18]只有滿足上述3條標準的題項才被保留下來。經過這一過程,萃取出5個因子,與上述初步設定的5個維度吻合,總方差累計貢獻率為70.534%(表2)。

表2 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
3.4 量表信度分析
基于回收的全部382份有效問卷,通過計算HTA研究決策轉化動力量表的總體Cronbach’sα系數和各維度的Cronbach’sα系數,對量表的內部一致性進行評價,以確定量表的可靠性。
本研究初步得出的HTA研究決策轉化動力量表的總體Cronbach’sα系數為0.904,其中“證據影響力”、“機構支持力”、“渠道聯接性”、“交流協作度”四個維度的Cronbach’sα系數值均在0.80以上,而“決策方推動力”維度的Cronbach’sα系數值低于0.70但在0.60以上,提示還可以作進一步的改進。總體而言,本研究設計的量表具有較高的信度(表3)。

表3 量表的內在一致性信度
3.5 量表效度分析
本研究研制量表的效度水平主要通過評估內容效度和結構效度來判定。
3.5.1 內容效度
內容效度主要關注原計劃要評價測量的內容在實際測量中能否被反映出來。[19]本研究量表的編制主要基于概念內涵界定和前期研究文獻回顧,依次完成量表提綱框架和問卷初稿;在初稿完成后,再次咨詢本研究領域相關的國內外專家進行完善。從編制過程嚴謹性和條目合理性判斷,其內容效度應該是合適的。
3.5.2 結構效度
結構效度指測驗或量表能夠測量出理論上的概念或特質的程度,分為收斂效度與區分效度。
本研究通過平均方差抽取量(AVE)來評價調查量表的收斂效度,若AVE值超過0.50,則收斂效度良好。[20]如下表中所示,各維度的AVE值均超過0.50,則可認為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而對于區分效度的評估,通常根據以下兩個標準:(1)任意兩個維度之間的相關系數必須低于0.85,以免出現多重共線性的問題;(2)各維度間標準化相關系數小于各維度AVE的平方根值。[21]如表4所示,本研究量表的五個維度中,任意兩個維度之間的相關系數的最大值為0.571,低于標準值0.85;各維度與其他維度的標準化相關系數均小于各維度AVE 值的算術平方根。因此,可以認為量表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

表4 決策轉化五因子相關系數表
注:對角線“( )”內為因子的AVE 系數的平方根,“[ ]”內為AVE系數;
*P<0.05,**P<0.01,***P<0.001
4 討論
本研究在界定決策轉化概念、明晰HTA決策轉化動力概念內涵的基礎上,初步編制相應量表;通過運用量表對HTA研究者進行問卷調查,進一步檢驗量表信度效度,最終形成涵蓋“證據影響力”、“機構支持力”、“渠道聯接性”、“交流協作度”、“決策方推動力”五個維度的衛生技術評估決策轉化動力量表,這也揭示了HTA研究的成功決策轉化與以上五個方面密切相關。首先,HTA研究結果或研究證據必須科學嚴謹,與決策需要相關且具有實踐運用的時效性和實用性;其次,HTA研究機構能夠為相應研究成果轉化提供指導指南、人員培訓、激勵機制等支持措施;其三,HTA研究方與決策方等相關利益群體之間的信息傳遞渠道較為通暢;其四,HTA研究方與決策方等研究結果利用群體在課題選題、調研實施、報告形成、結果傳播等關鍵環節進行較為充分的溝通交流;最后,決策方的推動對HTA研究的決策轉化也具有重要意義,具體表現為能夠較好解讀運用HTA研究證據,積極推動決策轉化,不僅僅依據領導好惡或原有做法而拒絕研究證據。
對量表的信度效度分析結果也說明本研究開發的量表印證了HTA決策轉化動力的內涵要素,對科學測量HTA決策轉化動力有重要的工具支持作用,也為進一步深入探究HTA決策轉化影響機制奠定了相應理論基礎。此外,量表的實踐運用將有利于HTA研究人員及時發現相應研究決策轉化方面的不足,并采取更有針對性的措施加以完善,這對擴大HTA研究證據在相應社會管理決策過程中的作用、促進科學決策及循證決策,也具有一定的實踐指導作用和現實意義。
本量表的開發基于理論和文獻研究,缺乏專家咨詢以及針對研究者的定性研究,這是本研究的一個局限。同時,由于研究證據的成功決策轉化需要多個相關利益群體的協作,而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主要集中于HTA研究人員,以其視角評價其他利益群體作用時可能存在較大困難,尤其是在目前透明性相對不高的決策環節。如對量表中“決策方推動力”維度下的問題,HTA研究人員不得不通過回憶甚至推測去評價決策方的相關工作,相應的主觀評判可能對結果的穩定性造成影響,導致“決策方推動力”因子的信度相對較低。因此,后續研究中考慮對涉及其他利益群體作用的問卷問題作進一步調整,注意選擇一些有代表性又較容易通過主觀判斷反映客觀狀況的問題。未來還將考慮就同一研究內容編制針對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量表,以通過多方印證得出更為精準的研究結論。
作者聲明本文無實際或潛在的利益沖突。
參 考 文 獻
[1] 陳潔. 衛生技術評估[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8.
[2] 陳英耀, 劉文彬, 唐檬, 等. 我國衛生技術評估與決策轉化研究概述[J]. 中國衛生政策研究, 2013, 6(7): 1-6.
[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ridging the “Know-Do” gap: Meeting on knowledge translation in global health [EB/OL].[2006-09-25]. http://www.who.int/kms/WHO_EIP_KMS_2006_2.pdf
[4] Knowledge Translation Program, Facult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bout knowledge translation: Definition [EB/OL].[2006-01-08]. http://www.ktp.utoronto.ca/whatisktp/definition/
[5] 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 About knowledge translation [EB/OL].[2006-09-09]. http://www.cihr-irsc.gc.ca/e/29418.html
[6] 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 Knowledge translation strategy 2004-2009: Innovation in action. [EB/OL].[2006-09-09]. http://www.cihr-irsc.gc.ca/e/26574.html
[7] Landry R, Lamari M, Amara N. The extent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util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research in government agencies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3, 63: 192-204.
[8] 成磊, 胡雁. 證據應用在循證護理實踐的研究現狀[J]. 護理學雜志, 2016, 31(3): 101-105.
[9] Harvey G, Kitson A. PARIHS revisited: from heuristic to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knowledge into practice[J]. Implementation Science, 2015, 11(1): 33.
[10] Stern R A, Seichepine D, Tschoe C, et al. Concussion Care Practices and Utilization of Evidence-Based Guidelines in the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ncussion: A survey of New England Emergency Departments[J]. Journal of Neurotrauma, 2016, 34(4): 861.
[11] Gagliardi A R, Dobrow M J. Identifying the conditions needed for integrated knowledge translation (IKT) in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users[J].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16, 16(1): 1-9.
[12] Zechmeister I, Schumacher I. The impact of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reports on decision making in Austria[J]. Int J Technol Assess Health Care, 2012,28(1): 77-84.
[13] 陳英耀, 黃葭燕. 國際衛生技術評估新進展和熱點問題[J]. 中國衛生質量管理, 2011, 18(1): 2-7.
[14] Hyder A A, Corluka A, Winch P J, et al. National policymakers speak out: are researchers giving them what they need? [J]. Health Policy Plan, 2011, 26: 73-82.
[15] Straus S E. Determinants of implementation of maternal health guidelines in Kosovo: mixed methods study[J]. Implementation Science, 2013, 8(1): 1- 9.
[16] Mitton C, Adair CE, Mckenzie E, et a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Exchange: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J]. Milbank Quarterly, 2007, 85, (4): 729-768.
[17] Bayley M T, Hurdowar A, Richards C L, et al. Barriers to implementation of stroke rehabilitation evidence: findings from a multi-site pilot project[J].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012, 34(19): 1633-1638.
[18] Churchill G A. Paradigm for developing better measures of marketing construct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79, 16(1): 64-73.
[19] David Grembowski. Health program evaluation: measurement and data collection[R].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201-233.
[20] 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a comment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3): 375-381.
[21] 吳志平, 陳福添. 中國文化情境下團隊心理安全氣氛的量表開發[J]. 管理學報, 2011, 8(1): 7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