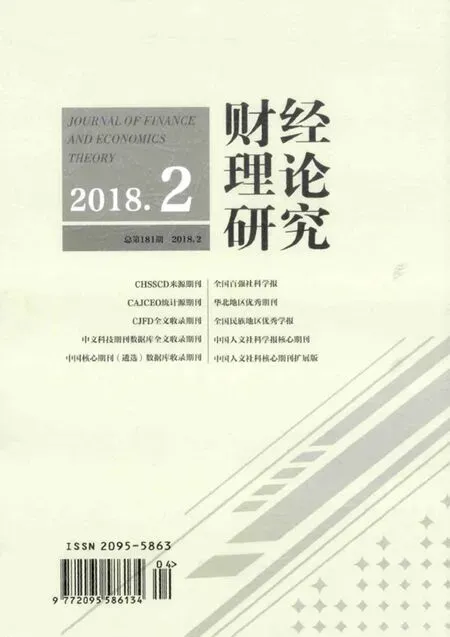中國牧區(qū)草牧場管理制度的變遷
文 明
(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xué)院 牧區(qū)發(fā)展研究所, 內(nèi)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制度,是用來規(guī)范人類行為的規(guī)則,這些規(guī)則涉及人類的社會、政治及經(jīng)濟行為[1]。制度可分為由權(quán)力機構(gòu)制定和實施的,由法律、法規(guī)和政策等組成的正式制度,和由習慣、習俗和倫理道德規(guī)范構(gòu)成的非正式制度。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nóng)村土地制度經(jīng)歷了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公社體制下的三級所有、集體土地家庭承包等四次重大變革,逐步從平均地權(quán)、“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到土地私有、生產(chǎn)合作,集體所有、統(tǒng)一經(jīng)營,再到公社體制下三級所有,最終確立“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jīng)營、長期穩(wěn)定承包權(quán)、鼓勵合法流轉(zhuǎn)”的新型農(nóng)村土地制度。而有學(xué)者把我國土地制度改革歸結(jié)為三個階段,即1949~1955年期間土地改革與互助合作、1956~1978年期間集體所有統(tǒng)一經(jīng)營,以及1979年以來的家庭承包經(jīng)營與集體統(tǒng)一經(jīng)營相結(jié)合[2]。然而,與農(nóng)村土地管理制度相比,我國草原牧區(qū)草牧場制度則采取了不同于農(nóng)村土地改革的路線和政策,下面就以70年來內(nèi)蒙古牧區(qū)草牧場的所有權(quán)制度和經(jīng)營(使用)權(quán)制度的變遷為主線,分7個歷史階段,探索和討論我國牧區(qū)草牧場管理制度的變遷規(guī)律,不僅為內(nèi)蒙古牧區(qū)70年的草牧場制度變遷做階段性總結(jié),更致力于對今后我國牧區(qū)草牧場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完善提供啟示和借鑒。
一、我國農(nóng)村土地管理制度的變遷概況
新中國農(nóng)村土地制度建設(shè)始于《中國土地法大綱》,其廢除了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開啟了中國土地制度改革之路。縱覽我國農(nóng)村土地制度之60余年的改革,大體上經(jīng)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解放初期(1949~1955),我國通過農(nóng)村土地改革,實現(xiàn)了“耕者有其田”,將封建地主私有制轉(zhuǎn)變?yōu)檗r(nóng)民個人私有制,并以互助合作運動為途徑,解決農(nóng)民缺乏生產(chǎn)資料的問題。在農(nóng)村土地改革中,通過劃分階級、沒收土地和重新分配,廢除了封建性及半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將農(nóng)村一切土地按鄉(xiāng)村全部人口,統(tǒng)一平均分配,并歸個人所有,使農(nóng)民生產(chǎn)積極性和勞動積極性空前提高。然而,分得土地的農(nóng)民缺乏必要的勞動力和生產(chǎn)資料,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受到影響。于是,農(nóng)民之間的互助合作,成為解決上述問題的關(guān)鍵。據(jù)統(tǒng)計,1951年,全國參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互助合作的農(nóng)戶占農(nóng)戶總數(shù)的17.5%,而到1955年時已發(fā)展到65%,而單干農(nóng)戶比例下降到了35%[2]。
社會主義建設(shè)時期(1956~1978),我國對農(nóng)村土地所有制進行改革,將私人所有制轉(zhuǎn)為集體所有,并將合作化經(jīng)營全面升級。1956年6月通過的《高級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示范章程》規(guī)定,入社的農(nóng)民必須把私有土地、耕畜、大型農(nóng)具等生產(chǎn)資料,轉(zhuǎn)為合作社集體所有。同年,全國參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互助合作的農(nóng)戶比例已上升到92%。而到1958年隨著農(nóng)村人民公社的迅速發(fā)展,形成了公社、生產(chǎn)大隊和生產(chǎn)隊三級組織,并很快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chǔ)” 的基本制度。在生產(chǎn)經(jīng)營上,則選擇了互助合作基礎(chǔ)上的統(tǒng)一經(jīng)營,走向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道路。然而,到了中后期,低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下的農(nóng)業(yè)合作化,暴露出“大鍋飯”弊端,“退社”和“包產(chǎn)到戶”成為農(nóng)戶實現(xiàn)自主經(jīng)營權(quán)的突破口。
而改革開放后(1979~至今),我國對農(nóng)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側(cè)重點集中在經(jīng)營權(quán)的改革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些地方開始積極試驗并推廣各種形式的生產(chǎn)責任制,如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包干到戶等。而到1983年,中共中央在《關(guān)于<印發(fā)當前農(nóng)村經(jīng)濟政策的若干問題>的通知》中充分肯定了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認為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結(jié)合了統(tǒng)一經(jīng)營和分散經(jīng)營,這種統(tǒng)分結(jié)合的雙層經(jīng)營體制具有廣泛的適應(yīng)性,并使其推廣至林業(yè)、牧業(yè)、漁業(yè)和多種經(jīng)營。之后,不管是第一輪承包中的“15年不變”,還是第二輪承包中的“30年不變”,農(nóng)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責任制已成為我國農(nóng)村土地制度之基本制度。進入新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之后,“在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zhì)基礎(chǔ)上”,“把握好土地集體所有制和家庭承包經(jīng)營的關(guān)系,現(xiàn)有農(nóng)村土地承包關(guān)系保持穩(wěn)定并長久不變,落實集體所有權(quán),穩(wěn)定農(nóng)戶承包權(quán),放活土地經(jīng)營權(quán),實行‘三權(quán)分置’”[3],成為我國農(nóng)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新內(nèi)容。
二、我國牧區(qū)草牧場管理制度的變遷
牧區(qū)草牧場,作為我國主要的土地類型之一,其管理制度與農(nóng)村土地管理制度變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但卻經(jīng)歷了有別于農(nóng)村土地管理制度的變遷歷程。當然,我國五大牧區(qū)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采取了不同的草牧場管理制度,比如西藏自治區(qū)“民主改革以前草場產(chǎn)權(quán)屬于三大領(lǐng)主壟斷,在民主改革時期實行民族公有,牧業(yè)合作化以后產(chǎn)權(quán)基本上是歸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自治區(qū)成立后,在‘一大二公’思潮影響下,實行單一的全面所有,改革開放以后又實行了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1],但其總體脈絡(luò)是統(tǒng)一的,都經(jīng)歷了所有權(quán)制度從民族公有到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兩種所有制并行,經(jīng)營(使用)權(quán)制度從放牧自由到家庭承包經(jīng)營、流轉(zhuǎn)使用與用益物權(quán)化并行的歷史變遷過程。下面就以內(nèi)蒙古牧區(qū)草牧場管理制度的變遷為主線,討論我國牧區(qū)草牧場管理制度的變遷。
(一)解放初期(1947~1953):民族公有制下的放牧自由
解放初期,內(nèi)蒙古牧區(qū)實行了民族公有、自由放牧的草牧場制度。在草牧場所有權(quán)制度上,實行蒙古民族所公有的制度設(shè)計。在1947年4月27日頒布的《內(nèi)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lǐng)》第十條明確規(guī)定,“保護蒙古民族土地總有權(quán)之完整。保護牧場,保護自治區(qū)域內(nèi)其他民族之土地現(xiàn)有權(quán)利”。1948年頒布的《內(nèi)蒙古土地制度改革法》指出,內(nèi)蒙古境內(nèi)一切土地為蒙古民族所公有;廢除內(nèi)蒙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廢除一切舊王公貴族、地主、喇嘛寺院等占有的土地所有權(quán),以及土地改革以前學(xué)校、軍隊、機關(guān)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quán)。同時,指出內(nèi)蒙古農(nóng)業(yè)區(qū)內(nèi)實行耕者有其田(凡分得土地即歸個人所有,并承認其自由經(jīng)營與特定條件下出租的權(quán)利,但仍保留蒙古民族的土地公有權(quán)[4]),畜牧業(yè)區(qū)內(nèi)實行放牧自由,按照盟旗行政區(qū)域的劃分,在該區(qū)域內(nèi)的草原、牧場上一切牧人均有放牧自由。
而在草牧場經(jīng)營(使用)權(quán)制度上則實行放牧自由、調(diào)劑牧場、保護牧場的政策,并在生產(chǎn)領(lǐng)域采取了“不分不斗不劃階級”、“牧主牧民兩利”政策,鼓勵牧民間互助合作。“自由放牧”是當時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在牧區(qū)實行的基本制度,大體上包括兩個內(nèi)容。一要廢除王公貴族、封建主對牧場的割據(jù)霸占,承認內(nèi)蒙古境內(nèi)牧場為內(nèi)蒙古民族所公有,按照盟、旗行政區(qū)劃,該區(qū)內(nèi)草原牧場一切牧人放牧自由;廢除奴隸制度,一切奴隸宣告解放,享有完全平等的公民權(quán)利,使他們有人身的自由和勞動自由。二是當前畜牧業(yè)經(jīng)濟因其分散性與落后性,必須有領(lǐng)導(dǎo)的逐步的總結(jié)群眾固有的經(jīng)驗,改進牧區(qū)放牧方法,才能提高生產(chǎn),改善人民生活。但鑒于牧區(qū)長期殘酷的封建統(tǒng)治所形成的強迫命令盛行的實際情況,必須根據(jù)各地不同的生產(chǎn)條件、民族特點與群眾覺悟水平,以典型示范,按照群眾的自愿來推行,使群眾有按照自己的意愿來選擇放牧方式(不論分群、合群、輪牧、專放、游牧、定居)的自由[5]。同時,制定保護牧場、禁止開荒的政策,劃定農(nóng)牧邊界,劃定牧場。當然,當時有些地區(qū)和牧民因曲解自由放牧政策,出現(xiàn)了亂放亂牧、爭奪牧場、開墾草原等現(xiàn)象,但都及時得到了糾正和查處。可見,自由放牧既不是無領(lǐng)導(dǎo)的放任自流,也不是強制性放牧政策,而是當時草牧場制度的高度概括,即:所有制上草牧場歸內(nèi)蒙古民族所公有;使用制度上牧民可按照盟、旗為界限,放牧自由;生產(chǎn)制度上牧民可自由選擇放牧方式;組織領(lǐng)導(dǎo)上可通過經(jīng)驗總結(jié),逐步改進牧區(qū)放牧方式。正是這一基本制度對解放初期廢除封建特權(quán)、解放封建制度所束縛的牧業(yè)生產(chǎn)力、恢復(fù)和發(fā)展畜牧業(yè)生產(chǎn)起到積極作用,也為牧區(qū)及畜牧業(yè)其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奠定了基礎(chǔ)。
(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53~1958):民族公有制下的定居游牧
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內(nèi)蒙古牧區(qū)基本延續(xù)了草牧場民族公有制度,而草牧場“自由放牧”的使用制度逐漸過渡到“定居游牧”的劃區(qū)輪牧制度。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我國決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逐步實現(xiàn)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并逐步實現(xiàn)國家對農(nóng)業(yè)、對手工業(yè)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而考慮到民族地區(qū)和牧區(qū)的特殊性,“在蒙綏牧區(qū)不僅要有步驟地、有計劃地進行國家總路線和總?cè)蝿?wù)的宣傳教育,而且對畜牧業(yè)經(jīng)濟也是要穩(wěn)妥地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在步驟與方法上更要迂回曲折,時間上更要準備長一些”[4]。所以,內(nèi)蒙古牧區(qū)社會主義改造中基本延續(xù)了草牧場民族公有制度,對草牧場“自由放牧”的使用制度逐漸過渡到“定居游牧”的劃區(qū)輪牧制度,而在畜牧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機制上逐步跟隨全國互助合作運動,遵循牧區(qū)五項方針、十一項政策和六項措施,對牧區(qū)畜牧業(yè)經(jīng)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將“在一個相當產(chǎn)的時間內(nèi),把個體的、游牧的、落后的、小生產(chǎn)的畜牧業(yè)經(jīng)濟,發(fā)展改造成為合作化的、現(xiàn)代化的、社會主義的畜牧業(yè)”[4]。因此,從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53~1958),牧區(qū)制度變遷更多集中在畜牧業(yè)經(jīng)營體制和生產(chǎn)方式的改變,并非對草牧場所有制度和使用制度的直接改革。
從自由放牧到劃區(qū)輪牧是一個漸進變化過程,同時也是牧區(qū)畜牧業(yè)從個體經(jīng)濟轉(zhuǎn)變?yōu)榧w所有制(互助合作)經(jīng)濟的過程。1953年1月1日,烏蘭夫同志在《內(nèi)蒙古日報》發(fā)表“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恢復(fù)發(fā)展畜牧業(yè)的成就及經(jīng)驗”一文中,提到要“提倡定居游牧,達到人畜兩旺”,認為定牧和游牧各有好處,各有缺點,定牧對于人旺這一點來說是有好處的,但對牲畜發(fā)展與繁殖上極為不利,因此應(yīng)當取長補短,提倡定居游牧。顯然,提倡定居游牧的初衷是為發(fā)展牧區(qū)人口,改善牧民生活,當然也會產(chǎn)生了其他的積極作用,如“由于已定居,家庭的保暖設(shè)備等自然會比較好些,老弱病人及孩子也不再跟著牲畜的游牧游動了”,“可以在定居的地方提倡打井種菜,建設(shè)較講究的住宅,進行文化教育,同時還可以把組織牧民游牧與組織牧民互助合作統(tǒng)一起來”。
而隨著牧區(qū)互助合作的推進,定居游牧與互助合作相結(jié)合,逐步實現(xiàn)牧區(qū)全面定居,并固定草牧場范圍,進行劃區(qū)輪牧。1953年12月,內(nèi)蒙古牧區(qū)把互助合作道路確定為牧區(qū)個體牧業(yè)經(jīng)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道路,提出應(yīng)進一步發(fā)展牧區(qū)的互助合作與定居游牧,在有條件的地方提倡與實行定居游牧,并以此作為牧區(qū)工作的重點。在此期間,內(nèi)蒙古牧區(qū)互助合作組織從臨時互助組發(fā)展到常年互助組,再到初級牧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而“定居游牧”政策也隨即進行調(diào)整。1956年,“隨著畜牧業(yè)合作社的發(fā)展,定居工作的推行,已經(jīng)比過去有更多的有利條件,同時按照全面規(guī)劃的方針,定居游牧政策也應(yīng)該對不同地區(qū)提出不同要求。一般說,在游牧區(qū)應(yīng)該逐步做到定居移場放牧,在牧場狹窄地區(qū)應(yīng)該做到定居劃片輪牧”[4],并指出當實現(xiàn)合作化時,定居游牧的大部分轉(zhuǎn)為定居。為實現(xiàn)這一目標,內(nèi)蒙古牧區(qū)規(guī)定在條件許可的地方,把固定牧場、打草場劃給一個或幾個合作社,成為其移場放牧的牧場。特別是1957年出臺的《內(nèi)蒙古牧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明確規(guī)定,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在牧場規(guī)劃未定前,凡是可以游牧的地區(qū),就實行定居放牧,牧場規(guī)劃已定后,則實行有計劃地定居移場放牧;定居定牧的地區(qū)就實行劃區(qū)輪牧。
1957年末,內(nèi)蒙古牧區(qū)參加互助合作的牧戶總數(shù)達到69543戶,占總戶數(shù)的84.6%,其中牧業(yè)合作社632個,入社牧戶20877戶,互助組3111個,入組牧戶48666戶[4]。在此基礎(chǔ)上,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實現(xiàn)牧業(yè)的合作化,內(nèi)蒙古牧區(qū)提出要逐步把牧場的使用權(quán)以國營牧場、合作社、合營牧場為單位固定下來。從此,草牧場的使用權(quán)逐漸被分離出來,固定給了國營牧場、合作社、合營牧場,其并責令有關(guān)單位牧場劃定以后,必須嚴守農(nóng)牧地界,保護牧場,不準破壞,并進行適當?shù)慕ㄔO(shè)。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劃定給合作社使用的草牧場,與其他生產(chǎn)資料相同有合作社集體所有制成分。
此后牧區(qū)合作化步伐不斷加快,到1958年7月,內(nèi)蒙古牧區(qū)牧業(yè)合作社數(shù)量猛增至2292個,入社牧戶達到67855戶,占總牧戶數(shù)的比例上升為80.16%;參加牧業(yè)生產(chǎn)互助組的牧戶13656戶,占總牧戶數(shù)的16.13%,兩者相加共計81511戶,牧業(yè)互助合作程度達到了96.29%。此外,有458戶牧主參加公私合營牧場、482戶牧主參加了合作社[6],牧區(qū)基本結(jié)束了畜牧業(yè)社會主義改造進程。于是,自治區(qū)要求必須加快牧區(qū)牧民定居游牧工作,應(yīng)當在一、二年內(nèi)爭取實現(xiàn)定居,定居以后即應(yīng)固定牧場范圍(使用權(quán)范圍,作者注),進行劃區(qū)輪牧,有計劃地進行各項建設(shè)(國營牧場除外)。
(三)人民公社時期(1958~1978):民族公有到全民所有的過渡
在人民公社時期,內(nèi)蒙古牧區(qū)草牧場所有制制度逐步從民族公有制轉(zhuǎn)為全民所有制,即國有制,而其使用權(quán)依然固定給國營牧場、企事業(yè)單位和人民公社的生產(chǎn)隊(基本核算單位),生產(chǎn)隊作為組織生產(chǎn)和生活的基本單位獲得了草牧場的使用權(quán)。期間,內(nèi)蒙古牧區(qū)經(jīng)受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在“以糧為綱”、“牧民不吃虧心糧”等極“左”口號下,大面積草原被開墾,為日后草原退化埋下了隱患。
1958年8中共中央決定在廣大農(nóng)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同年8~9月份,內(nèi)蒙古就研究部署全區(qū)人民公社化的問題。到1959年12月底,八萬多戶牧民已有七萬多戶加入了人民公社,入公社的牧戶已占牧區(qū)總牧戶的91.5%,牧區(qū)基本上實現(xiàn)了人民公社化[4]。如前文所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牧區(qū)實行定居,要求游牧區(qū)應(yīng)該配合社會主義的改造逐步定居下來。而到了合作化、公社化時期,自治區(qū)加強全區(qū)草原勘測規(guī)劃工作,大力推行定居游牧。1958年2月,烏蘭夫同志在中共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指出,在牧區(qū)實現(xiàn)大躍進,“要大力進行牧業(yè)四項基本建設(shè):興修牧區(qū)水利,改良牧場,建立飼料基地、規(guī)劃四季牧場,開展獸疫防治工作,改良牲畜品種”,其中規(guī)劃四季牧場要“與合作化相結(jié)合,必須積極推行定居游牧。推行定居游牧必須以合作社為基礎(chǔ),必須全面規(guī)劃,選好定居點和牧場進行飼料基地的建設(shè),逐步固定牧場的使用權(quán)。……爭取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把定居游牧普遍推廣”[4]。同時注重草牧場使用權(quán)的固定和四季牧場的劃分工作,要求在定居和半定居區(qū)實行劃定牧場劃區(qū)輪牧,獲得使用權(quán)的人民公社要有計劃的分配四季牧場,加速定居建設(shè)和進行其他固定性基本建設(shè)。1960年中共中央下發(fā)《關(guān)于農(nóng)村人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牧區(qū)人民公社開始實施“三級所有、隊為基礎(chǔ)”的政策制度,建立公社、生產(chǎn)隊和生產(chǎn)小隊三級所有的根本制度,堅持生產(chǎn)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其中提出,勞力、草場(包括打草草場、放牧牧場)、畜群、役畜、工具、棚圈設(shè)備必須堅持實行“六固定”,固定給生產(chǎn)小隊經(jīng)營和使用,并且登記造冊,任何人不得隨意調(diào)用。草場一般的應(yīng)該以生產(chǎn)小隊劃定適用范圍,并由生產(chǎn)小隊進行草場改良和水利建設(shè),必須進行草場調(diào)劑時,也應(yīng)該商得被調(diào)劑生產(chǎn)小隊的同意。草場沒有固定使用的,由生產(chǎn)隊統(tǒng)一規(guī)劃,分配給生產(chǎn)小隊固定放牧和進行草場建設(shè)[4]。因此,當時草牧場的使用權(quán)的固定范圍基本縮小到生產(chǎn)小隊,并承擔了草牧場的改良和建設(shè)任務(wù)。
1961年7月,內(nèi)蒙古頒布《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牧區(qū)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規(guī)定草牧場為全民所有,固定給生產(chǎn)隊使用,生產(chǎn)隊有永久使用權(quán)和經(jīng)營保護權(quán)。到1965年4月,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出臺《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草原管理暫行條例》(草案),以法規(guī)形式確定自治區(qū)境內(nèi)所有草原均為全民所有,標志著實行了十余年的草牧場民族公有制已過渡為國家所有制。而在使用權(quán)問題上仍然繼續(xù)強調(diào)將其固定給生產(chǎn)隊,同時適當放寬生產(chǎn)小隊的自主權(quán)。在《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牧區(qū)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中指出,生產(chǎn)隊(生產(chǎn)小隊,作者注)在管理本隊生產(chǎn)上,有一定的自主權(quán),包括生產(chǎn)隊有權(quán)對生產(chǎn)大隊(生產(chǎn)隊,作者注)固定給的勞力、畜群、草牧場、工具、設(shè)備、役畜長期經(jīng)營和使用;有權(quán)安排放牧時間、地點和冬春營地;有權(quán)在劃定的范圍內(nèi)選定打草場打草,等等。到1963年,對全區(qū)大部分公社的草場進行了綜合利用規(guī)劃,明確了社界,粗線地安排了放牧場、打草場、定居點、飼料基地、水利建設(shè)等各項用地,并根據(jù)群眾原有的移場放牧習慣,把草場按自然條件、氣候特點,劃分為冬、春、夏、秋季節(jié)營地,推行了按季移動放牧的草場利用制度,認為劃分季節(jié)營地是當時合理利用放牧場的基礎(chǔ),并且在季節(jié)營地內(nèi)實行分區(qū)分段放牧是合理利用草場的主要內(nèi)容,只要兩者正確地結(jié)合,才能達到合理利用草原的目的。于是,公社、生產(chǎn)隊甚至生產(chǎn)小隊的草牧場邊界逐步確立,侵占其他社隊的牧場、打草場和水源的行為被制止,草牧場調(diào)劑成為生產(chǎn)隊與生產(chǎn)隊、公社與公社、旗與旗、盟市與盟市之間解決生產(chǎn)之需的有效途徑,同時也出現(xiàn)了所謂收取一部分草原建設(shè)費之說。如1965年4月頒布的《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草原管理暫行條例》(草案)規(guī)定,草牧場固定后,如必須變動時,應(yīng)按下列規(guī)定辦理:……根據(jù)生產(chǎn)發(fā)展需要,相互調(diào)節(jié)草牧場、改變草原牧場使用權(quán)限時,……對原使用單位投資興建的各項基本建設(shè),應(yīng)予合理補償。同年7月,全區(qū)草原工作會議又進一步明確,凡到外單位借場放牧、摟草、砍柴、挖藥材的,必須征得對方同意。當然,當時也考慮到牧區(qū)遭遇較大自然災(zāi)害問題,特別規(guī)定將發(fā)生災(zāi)情時,盟和自治區(qū)可以統(tǒng)一調(diào)劑牧場。
期間,固定草牧場使用權(quán)和定居游牧一直被作為保護、利用、建設(shè)草牧場的前提而推行,同時自治區(qū)也三番五次下令“禁止開荒、保護牧場”。然而,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全國經(jīng)濟建設(shè)影響,大量優(yōu)質(zhì)草牧場被開墾或被非牧區(qū)單位占用。據(jù)資料,截止1975年內(nèi)蒙古牧區(qū)4.65億畝草原,近三分之一草場(約1.5億畝)不同程度退化,產(chǎn)草量減少40~70%,還有5000萬畝草原沙化,1000萬畝開墾毀掉[7]。
(四)改革開放以來(1978~至今):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制
1.改革開放初期(1978~1983):全面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制的過渡
改革開放初期,內(nèi)蒙古牧區(qū)草牧場制度實現(xiàn)了平穩(wěn)過渡。在草牧場所有權(quán)問題上從全民所有制逐步過渡到兩種制度并存的制度安排,而在使用權(quán)方面依然堅持使用權(quán)固定給基本核算單位,并使其逐步縮小至作業(yè)組、畜群、專業(yè)養(yǎng)畜戶,要求落實畜牧業(yè)生產(chǎn)責任制和草牧場責任制,同時然強調(diào)草原建設(shè)工作。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內(nèi)蒙古牧區(qū)依然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chǔ)”的制度,提出人民公社、生產(chǎn)大隊和生產(chǎn)隊的所有權(quán)和自主權(quán),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而在畜牧業(yè)生產(chǎn)領(lǐng)域推行“兩定一獎”(定產(chǎn)、定工)或“三定一獎”(定產(chǎn)、定工、定費用)為內(nèi)容的責任制度。在草牧場制度安排上,要嚴格執(zhí)行《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草原管理條例》,在草牧場全民所有制框架下,要求盡快把草牧場的使用權(quán)落實到場、社、隊。同時,清理非牧業(yè)生產(chǎn)或非牧區(qū)人口占用草牧場的現(xiàn)象和行為,并允許獲得使用權(quán)的核算單位向借場放牧者收取一定數(shù)量的管理費。如1980年2月出臺的《內(nèi)蒙古黨委、人民政府關(guān)于畜牧業(yè)方針政策的幾項規(guī)定》中明確規(guī)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有權(quán)因地制宜地發(fā)展畜牧業(yè)生產(chǎn),有權(quán)保護、利用、建設(shè)草牧場;人民公社、生產(chǎn)隊對所轄范圍內(nèi)草牧場的使用權(quán),應(yīng)當受到法律保護;劃分草牧場使用權(quán)的工作,要在一九八一年底以前完成,并有旗縣人民政府發(fā)給執(zhí)照。草牧場固定后,任何單位不得侵占。除因災(zāi)可通過協(xié)商借場放牧外,其他借場者,應(yīng)交納一定數(shù)量的管理費”。
雖然人民公社時期反復(fù)強調(diào)固定草牧場使用權(quán)問題,但受內(nèi)外諸多因素的影響,草牧場使用權(quán)落實工作進展相對緩慢,到1980年12月,全區(qū)有6個旗,72個公社,401個大隊固定了草牧場使用權(quán)[7],到1981年4月落實范圍擴大到8個旗縣[7],始終沒有完成使用權(quán)的全部落實。同期,全區(qū)草牧場退化、沙化現(xiàn)象日益嚴峻,到上世紀80年代初全區(qū)三分之一左右的草場嚴重退化、沙化[8],而其原因普遍被解釋為沒有很好地固定草牧場的使用權(quán),甚至草場的所有權(quán)安排不當[4,8,9]。
于是,對草牧場所有制度進行調(diào)整和進一步落實使用權(quán)成為必然,意在建立與畜牧業(yè)生產(chǎn)責任制相適應(yīng)的草牧場制度體系。1980年春,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人民政府決定對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草原管理條例進行修改,決定要對內(nèi)蒙古草原的所有權(quán)由單一的全民所有制改為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兩種所有制。1981年1月中旬,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專門討論內(nèi)蒙古草原的所有制問題。會議決定內(nèi)蒙古草原實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兩種所有制。1982年3月26日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黨委辦公廳印發(fā)修改后的《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草原管理條例》(試行),規(guī)定自治區(qū)境內(nèi)的草原所有制,現(xiàn)階段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試行條例發(fā)布后,在全區(qū)范圍內(nèi)進行試點,截止1983年12月,試點范圍擴展至全區(qū)12個盟市,有60多個旗縣的6億畝草場落實了草原所有權(quán),有1.3億草場落實了使用權(quán)和管理責任制,不少旗縣社隊已經(jīng)發(fā)放了草原所有證和使用證[6]。于是,實行了近20年的單一的草原全民所有制制度,過渡為以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內(nèi)容的兩種所有制制度,同時開啟了草原責任制同畜牧業(yè)生產(chǎn)責任制結(jié)合起來的“雙承包”制時代。
2.改革開放時期(1983~本世紀初):草牧場家庭承包經(jīng)營制度的確立及完善
確立草牧場家庭承包經(jīng)營制度以來,草牧場所有權(quán)制度沒有原則性的改動,延續(xù)了1982年發(fā)布的《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草原管理條例(試行)》中“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兩種制度,只是在不同的時期其表述方式有所不同。而在草牧場家庭承包經(jīng)營制度上雖然一直強調(diào)“承包到戶”,但也經(jīng)歷了循序漸進的細化過程,特別是其使用權(quán)。
內(nèi)蒙古草原牧區(qū)“草畜雙承包”制度的實施始于上世紀80年初期,特別是1984年中央發(fā)出《關(guān)于一九八四年農(nóng)村工作的通知》,要求繼續(xù)穩(wěn)定和完善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極大地推動了牧區(qū)“草畜雙承包”制度的全面實施。據(jù)資料顯示,到1985年8月,全區(qū)有95%的集體牲畜都作價歸了戶,全區(qū)10億畝可利用草原中已經(jīng)落實所有權(quán)和使用權(quán)草原面積將近8億畝,其中以承包到戶的近6億畝[4],而到1986年時,所有權(quán)和使用權(quán)落實面積已經(jīng)達到了8.9億畝和7.6億畝,分別占到全區(qū)可利用草原面積的86.8%和74.3%[10]。屆時,落實草原所有權(quán)、使用權(quán)和實施家庭承包經(jīng)營制度(簡稱“雙權(quán)一制”)成為了內(nèi)蒙古牧區(qū)草牧場,乃至全國草牧場制度安排的核心內(nèi)容。
其中,對草牧場所有權(quán)制度上沒有原則性的改動,延續(xù)了1982年發(fā)布的《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草原管理條例(試行)》中“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兩種制度,只是在不同的時期其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如,1983年7月21日,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討論通過的《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草原管理條例(試行)》第五條規(guī)定,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境內(nèi)草原屬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和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并一直沿用到2004年;而2004年11月修訂的《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草原管理條例》(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條中則規(guī)定,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境內(nèi)的草原屬于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
而在草牧場家庭承包經(jīng)營制度上雖然一直強調(diào)“承包到戶”,但也經(jīng)歷了循序漸進的細化過程,特別是其使用權(quán)。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實行“草畜雙承包”(草場公有、承包經(jīng)營、牲畜作價、戶有戶養(yǎng)),基本實現(xiàn)所有牲畜的作價歸戶,把草牧場所有權(quán)劃歸嘎查(村)集體所有(嘎查,蒙古語,相當于內(nèi)地行政村,是內(nèi)蒙古牧區(qū)最基層的自治單位,設(shè)有嘎查委員會和嘎查支部),而草牧場承包工作剛剛開始,更多的是把使用權(quán)落實到嘎查集體。1982年3月17日,新華社報道內(nèi)蒙古黨委、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人民政府決定將現(xiàn)有草牧場的使用權(quán)固定到國營農(nóng)牧場、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并將使用權(quán)按照各地不同的牧業(yè)生產(chǎn)責任制形式,分別固定到作業(yè)組、畜群、專業(yè)養(yǎng)殖戶,長期不變。1984年5月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人民政府在《關(guān)于發(fā)展農(nóng)村牧區(qū)商品生產(chǎn)搞活經(jīng)濟的七項規(guī)定》中提出,要把草牧場使用、管理、建設(shè)的責任制落實到戶,承包期至少二十年以上。據(jù)資料,截止1985年8月,全區(qū)10億畝可利用草原已經(jīng)落實所有權(quán)和使用的面積將近8億畝,其中已承包到戶的近6億畝。其中,更多的是按居住點、出牧點、水源點劃分,夏秋草場劃分到戶,冬春草場劃分到組;準備建設(shè)的草場、打草場劃分到戶,放牧場集體使用[4]。承包草原的前10年,很多地方都按浩特為基本單位進行承包,即使承包到戶,牧民仍然按照冬、春、夏、秋四季輪牧方式進行使用,牧戶之間沒有明顯的承包草場界限。
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由于草牧場“雙權(quán)一制”落實得還不徹底,落實“雙權(quán)一制”后對草牧場的科學(xué)管理體制沒有建立起來,在草牧場的權(quán)益關(guān)系上產(chǎn)生了新的矛盾,出現(xiàn)了新的吃草牧場“大鍋飯”的問題,草畜矛盾加劇,草牧場逐年退化的趨勢未能得到有效遏制[11]。為此,自1987年自治區(qū)畜牧局在阿魯科爾沁、巴林右旗等10個旗開始進行草牧場有償承包的試點和試行,探索牧區(qū)草牧場管理的新制度。1989年9月,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人民政府在阿魯科爾沁旗召開全區(qū)草牧場有償承包使用經(jīng)驗交流現(xiàn)場會議,并于同年10月自治區(qū)人民政府批轉(zhuǎn)的自治區(qū)農(nóng)委《關(guān)于進一步落實草牧場使用權(quán),實行草牧場有償承包使用制度的初步意見》報告,對草牧場使用費確定了初步標準。1993年下半年,自治區(qū)畜牧局對10個實行草牧場有償承包使用試點旗進行了驗收,并全部通過。同年年末,全區(qū)實行草牧場有償承包使用的已有59個旗縣,590蘇木、鄉(xiāng)(蘇木,蒙古語,相當于內(nèi)地鄉(xiāng)、鎮(zhèn)一級的行政單位),3998個嘎查村,26.9萬戶牧民,3803.27萬公頃草原,2497萬頭只牲畜。1994年9月,國家農(nóng)業(yè)部畜牧獸醫(yī)司召開全國草牧場有償承包使用現(xiàn)場會議,決定推廣阿魯科爾沁旗實行草牧場有償承包使用的經(jīng)驗,用二三年時間將草牧場有償承包使用制度實行至全國范圍內(nèi)。
然而,鑒于當時各地草牧場使用費收費標準不一,及牧民稅費負擔過重,1996年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政府作出《關(guān)于進一步落實完善“雙權(quán)一制”的規(guī)定》,明確提出要把草牧場徹底承包到戶,并堅持30年不變,開始了內(nèi)蒙古牧區(qū)第二輪草牧場承包工作。據(jù)統(tǒng)計,截止2005年內(nèi)蒙古全區(qū)已落實草原所有權(quán)面積10.4億畝,落實承包到戶面積8.3億畝[12],草原“雙權(quán)一制”工作基本完成。
(五)深化改革時期(本世紀初~至今):家庭承包經(jīng)營制度的改革與創(chuàng)新——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流轉(zhuǎn)
上世紀90年中后期,隨著草牧場承包到戶的徹底落實,草牧場邊界逐漸清晰,牧戶間跨界放牧行為受到極大地限制。然而,草牧場承包到戶、草牧場退化加劇及畜牧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使牧戶之間草牧場需求出現(xiàn)差異,承包戶之間的草牧場借用、租用行為逐漸增多,草牧場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的流轉(zhuǎn)作為草牧場使用制度改革方向出現(xiàn)在牧民生產(chǎn)實踐中。于是,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人民政府在《中共中央、國務(wù)院關(guān)于當前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經(jīng)濟發(fā)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發(fā)[1993]11號)、《國務(wù)院批轉(zhuǎn)農(nóng)業(yè)部關(guān)于穩(wěn)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guān)系意見的通知》 (農(nóng)業(yè)部1994年12月30日)等規(guī)范性文件的基礎(chǔ)上,于1999年12月發(fā)布施行了《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草原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流轉(zhuǎn)辦法》(內(nèi)蒙古人民政府[1999]第99號政府令)。
進入新世紀后,國家通過《土地承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quán)法》等法律法規(guī),承認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流轉(zhuǎn)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必要性,并確立其為我國土地家庭承包經(jīng)營(使用)制度的一項改革和創(chuàng)新機制。屆時正逢內(nèi)蒙古牧區(qū)草原生態(tài)問題高發(fā)期,牧區(qū)正面臨著恢復(fù)與保護草原及草原畜牧業(yè)轉(zhuǎn)型等雙重壓力,而草牧場流轉(zhuǎn)迎合了這些變化,迅速推廣至全區(qū)各草原類型區(qū)域,草牧場流轉(zhuǎn)規(guī)模快速擴大,其流轉(zhuǎn)主體、流轉(zhuǎn)方式、流轉(zhuǎn)價格等都有了新的變化和發(fā)展,也呈現(xiàn)出一些新的發(fā)展趨向。同時,草牧場流轉(zhuǎn)過程中,以及草牧場流轉(zhuǎn)而引起的各種新問題、新矛盾不斷發(fā)生,對內(nèi)蒙古牧區(qū)草原生態(tài)保護、草牧場經(jīng)營管理實踐及制度建設(shè)帶來了諸多難題和挑戰(zhàn)。在此期間,為減少和解決草牧場流轉(zhuǎn)中的問題和矛盾,自治區(qū)、盟市政府及相關(guān)職能部門出臺了很多規(guī)范性文件,如《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黨委政府關(guān)于清理非牧民占用牧區(qū)草場和依法規(guī)范草場使用權(quán)流轉(zhuǎn)的意見》(內(nèi)黨字[2003]3號)、《錫林郭勒盟行政公署關(guān)于加強草牧場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流轉(zhuǎn)管理服務(wù)的意見》(錫署發(fā)[2009]51號)、《鄂爾多斯市人民政府關(guān)于農(nóng)村牧區(qū)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流轉(zhuǎn)暫行辦法》(鄂府發(fā)[2009]28號文)、《呼倫貝爾市牧業(yè)經(jīng)營管理站關(guān)于加強草原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流轉(zhuǎn)工作的通知》(呼牧經(jīng)發(fā)[2009]8號)等。
同時,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重新修訂了《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草原管理條例》(2004年修訂)以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草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2006年修訂)等,以地方法規(guī)形式進一步完善了草牧場流轉(zhuǎn)制度建設(shè),并廢除了1999年頒布實施的《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草原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流轉(zhuǎn)辦法》,使內(nèi)蒙古牧區(qū)草牧場流轉(zhuǎn)制度建設(shè)進入全新的法制化時代,草牧場流轉(zhuǎn)實踐也進入了快速發(fā)展階段。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截止2016年內(nèi)蒙古草牧場流轉(zhuǎn)面積達7500萬畝,占落實草牧場承包經(jīng)營面積的7.2%[13]。
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共中央國務(wù)院關(guān)于加快發(fā)展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進一步增強農(nóng)村發(fā)展活力的若干意見》(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及《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等重要文件強調(diào)一再強調(diào),通過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的流轉(zhuǎn),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進而實現(xiàn)農(nóng)牧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隨后,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黨委、政府也出臺了相應(yīng)的政策性文件。于是,除了千千萬萬個普通農(nóng)牧民可以承包經(jīng)營草牧場,家庭農(nóng)牧場、合作社、企業(yè)等市場主體可以流轉(zhuǎn)使用草牧場,被許可的社會工商資本也可以進入流轉(zhuǎn)使用草牧場的行列,草牧場承包經(jīng)營(使用)制度不再是唯牧民之權(quán)益。
(六)深化改革時期(2010~至今):草原生態(tài)保護補助獎勵機制的實施、草原確權(quán)及“三權(quán)分置”
2010年10月,國務(wù)院作出決定,在全國8個主要草原牧區(qū)實施草原生態(tài)保護補助獎勵機制,中央財政每年將投入134億元,主要用于草原禁牧補貼、草畜平衡獎勵、牧草良種補助和牧戶生產(chǎn)性補助等。草原生態(tài)保護補助獎勵機制的實施,開啟了我國以草原生態(tài)為基礎(chǔ)的補獎時代,表明著人們對草原生態(tài)的認識從片面的經(jīng)濟價值或片面的生態(tài)價值走向草、人、畜為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集社會、經(jīng)濟與生態(tài)價值為一體的綜合體,表示國家直接介入草原生態(tài)保護與建設(shè)行動中,進一步體現(xiàn)了草原之準公共物品性質(zhì)。
為了落實出臺的中央草原生態(tài)保護補助獎勵政策,自治區(qū)配套出臺了《內(nèi)蒙古草原生態(tài)保護補助獎勵機制實施方案》,把全區(qū)10.2億畝草原劃入草原生態(tài)保護補助獎勵范圍,決定將其分為禁牧區(qū)和草畜平衡區(qū)。同時,根據(jù)內(nèi)蒙古草原在時空分布上的不同,因地制宜地提出草牧場標準畝折算系數(shù)的概念,以及保底補獎標準,確保補獎資金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從政策實施情況看,“十二五”期間,內(nèi)蒙古草原生態(tài)保護補助獎勵政策共投入300億元,其中國家投入213億元,自治區(qū)各級配套資金87億元。政策覆蓋全區(qū)12個盟市2個計劃單列市,73個旗縣區(qū),107個鄉(xiāng)鎮(zhèn)的10.13億畝天然草原,其中禁牧5.48億畝,草畜平衡4.65億畝,有146萬戶、534萬農(nóng)牧民從中受益,減輕了天然草原的放牧壓力,使草原生態(tài)逐步向好,保證了草原畜牧業(yè)的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牧民收入明顯提高,農(nóng)牧民草原保護意識顯著提升[14]。目前,新一輪草原生態(tài)保護補助獎勵機制已開始實施,中央和自治區(qū)政府持續(xù)保持草原生態(tài)保護之補助與獎勵力度,并把政策實施目標從上一輪的草原生態(tài)改善和草原畜牧業(yè)提質(zhì)增產(chǎn)提升為草原生態(tài)環(huán)境持續(xù)好轉(zhuǎn)、草原畜牧業(yè)轉(zhuǎn)型升級和草原牧民增收致富,并與完善草原確權(quán)承包和基本草原劃定工作高度銜接。
早在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quán)法》的頒布,明確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的用益物權(quán)。于是,農(nóng)業(yè)部從2009年開始進行土地確權(quán)整村推進試點工作;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提出“用5年時間基本完成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確權(quán)登記頒證工作,妥善解決農(nóng)戶承包地塊面積不準、四至不清等問題”;直到2016年,全國22個省區(qū)市試點,將全國試點范圍擴大至2582個縣(市、區(qū))、3萬個鄉(xiāng)鎮(zhèn)、51.2萬個行政村,已完成實測面積12.5億畝,確權(quán)面積8.5億畝,約占全國二輪家庭承包集體耕地面積的70%。從試點地區(qū)看,通過確權(quán),解決了長期以來承包地塊面積不準、四至不清等問題,推動了土地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不僅沒有影響農(nóng)村社會穩(wěn)定,還解決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得到了廣大農(nóng)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15]。
然而,全國草原確權(quán)承包登記試點工作則推遲到2015年才開始。2015年4月,農(nóng)業(yè)部發(fā)出《關(guān)于開展草原確權(quán)承包登記試點的通知》,安排部署有關(guān)省區(qū)市草原確權(quán)承包登記試點工作。其實,內(nèi)蒙古草原確權(quán)承包工作開始的要比全國其他草原牧區(qū)也要早一些。2014年9月6日,內(nèi)蒙古率先頒發(fā)全國草原確權(quán)第一證,并全區(qū)10個試點旗確權(quán)承包工作全面推開,并出臺了《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完善牧區(qū)草原確權(quán)承包登記試點工作實施方案》。2015年在總結(jié)10個試點旗縣的基礎(chǔ)上,把草原確權(quán)承包工作向全區(qū)其余旗縣全面推開。截止2016年年底,全區(qū)草原確權(quán)承包試點旗共落實草原所有權(quán)面積27156萬畝,使用權(quán)面積967.9萬畝,草原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面積26657.2萬畝;發(fā)放《草原所有權(quán)證》940本,《草原使用權(quán)證》34本,《草原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證》191922本,共涉及農(nóng)牧戶262646戶,首批10個試點旗全部通過了自治區(qū)驗收[16]。
顯然,草原確權(quán)工作為牧區(qū)草牧場所有權(quán)、承包權(quán)和經(jīng)營權(quán)“三權(quán)分置”改革提供了基礎(chǔ)。“三權(quán)分置”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后農(nóng)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chuàng)新,也是中央關(guān)于農(nóng)村土地問題出臺的又一重大政策,其核心是堅持農(nóng)村土地集體所有權(quán)的根本地位,嚴格保護農(nóng)戶承包權(quán),放活土地經(jīng)營權(quán)。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wù)院辦公廳于2016年10印發(fā)《關(guān)于完善農(nóng)村土地所有權(quán)承包權(quán)經(jīng)營權(quán)分置辦法的意見》(中辦發(fā)〔2016〕67號),要求各地各部門結(jié)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2017年3月,內(nèi)蒙古黨委辦公廳、自治區(qū)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fā)《關(guān)于完善農(nóng)村牧區(qū)土地草原所有權(quán)承包權(quán)經(jīng)營權(quán)分置辦法的實施意見》。而內(nèi)蒙古牧區(qū)草原三權(quán)分置試點工作則始于2015年,內(nèi)蒙古鄂爾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成為全國首家草原確權(quán)“三權(quán)分置”試點旗縣。到2016年5月,試點嘎查哈日根圖嘎查已拿到草原所有權(quán)證,51戶牧民拿到了草原承包權(quán)證和草原經(jīng)營權(quán)證。而錫林郭勒盟鑲黃旗作為全區(qū)草原確權(quán)登記工作試點旗縣之一和錫盟唯一牧區(qū)試點地區(qū),特別是作為全區(qū)承包土地(草牧場)經(jīng)營權(quán)抵押貸款試點旗縣,在積極推進草牧場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登記頒證工作的同時,圍繞草牧場所有權(quán)承包權(quán)和經(jīng)營權(quán)“三權(quán)分置”改革,賦予牧民對承包草牧場占有、使用、收益、流轉(zhuǎn)及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抵押、擔保權(quán)能。可見,確權(quán)基礎(chǔ)上的“三權(quán)分置”改革剛剛起步,試點旗縣也只處在摸索階段,改革對草牧場經(jīng)營以及草原畜牧業(yè)發(fā)展,乃至牧區(qū)生產(chǎn)生活的影響還有待實踐中檢驗。
三、結(jié)論、問題及思考
解放至今,以內(nèi)蒙古牧區(qū)為代表的我國牧區(qū)草牧場制度走過70年的曲折歷程,經(jīng)歷了從民族公有到集體所有的所有權(quán)制度變遷,從自由放牧到流轉(zhuǎn)使用的經(jīng)營(使用)權(quán)制度改革,雖然與全國農(nóng)村土地制度變遷大徑相同,但也有其自己的特點和變化:

綜上所述,一是在草牧場制度設(shè)計上國家權(quán)力不斷延伸至基層組織。民族公有到全民所有,全民所有到集體所有無不在體現(xiàn)國家權(quán)力在草原及草牧場所有權(quán)問題上的集中和延伸。而經(jīng)營(使用)權(quán)制度設(shè)計上國家權(quán)力也逐步延伸到農(nóng)牧戶家庭經(jīng)營中,放牧自由、定居游牧與劃區(qū)輪牧已不再可能,嘎查集體等基本核算單位對本集體所有草牧場的經(jīng)營(使用)方式基本無權(quán)干涉,而家庭經(jīng)營要顧全國家生態(tài)建設(shè)之大局、要服從全民所有之制度,從承包經(jīng)營的草牧場中劃出部分或全部面積予以實施禁牧、休牧。二是在草牧場經(jīng)營(使用)權(quán)設(shè)計中草牧場經(jīng)營的傳統(tǒng)方式快速退縮。在早期,牧民在草牧場經(jīng)營(使用)過程中可以“放牧自由”,無論放牧范圍,還是放牧方式都相對“自由”,而地方政府為牧民的“放牧自由”提供便利服務(wù)。而到后期,政府不斷強化管理,并且范圍不斷縮小,使得牧民經(jīng)營范圍鎖定在狹小的承包范圍內(nèi),甚至更小,經(jīng)營方式相對單一,進而倒逼草牧場經(jīng)營的傳統(tǒng)方式極度退縮。三是,市場經(jīng)濟主體的主體地位逐步顯現(xiàn)。資源總量和平均量逐年降低,而市場化程度日益提高,牧區(qū)畜牧業(yè)經(jīng)營與草牧場經(jīng)營中市場化成分逐步替代傳統(tǒng)經(jīng)營中的生態(tài)化成分。在民族公有到家庭承包的變遷過程中,牧民家庭經(jīng)濟成為了市場主體。而在利益最大化為初衷的市場經(jīng)濟環(huán)境下,這種制度設(shè)計使個體的逐利思想蠶食了集體的生態(tài)覺悟。
假設(shè)氣候變化對草牧場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的影響是既定的,那么新的制度設(shè)計本身以及該制度約束下的市場行為,通過改變原有制度安排下的資源配置機制,影響了草牧場生態(tài)環(huán)境。其中,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同時存在。因此,在具有社會公共資源性質(zhì)的草牧場經(jīng)營(使用)過程中,制度設(shè)計本身不能只關(guān)注政府權(quán)力的集中或市場經(jīng)濟的高效性,而應(yīng)兼顧培育具有社會責任意識的市場主體,積極發(fā)揮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非正式制度的積極作用,并使其價值化。
[]
[1] 范遠紅.西藏草場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遷研究[M].重慶: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9.
[2] 廖洪樂.中國農(nóng)村土地制度六十年——回顧與展望[M].北京:中國財政經(jīng)濟出版社,2008.
[3]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wù)院辦公廳印發(fā).深化農(nóng)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5-11/02/content_2958781.htm ,2015-11-02.
[4] 內(nèi)蒙古黨委政策研究室等.內(nèi)蒙古畜牧業(yè)文獻資料選編(第二卷)[Z].內(nèi)蒙古黨委印刷廠印刷,1987:15-596.
[5] 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三不兩利”與“穩(wěn)寬長”文獻與史料[Z].內(nèi)蒙古政協(xié)文史書店發(fā)行,2005:359.
[6] 達林太、鄭易生.牧區(qū)與市場:牧民經(jīng)濟學(xué)[M].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10.
[7] 內(nèi)蒙古黨委政策研究室等.內(nèi)蒙古畜牧業(yè)文獻資料選編(第四卷)[Z].內(nèi)蒙古黨委印刷廠印刷,1987:243-365.
[8] 許志信.草原退化與合理利用[J].內(nèi)蒙古農(nóng)牧學(xué)院學(xué)報,1981,(5):43-51.
[9] 張正明.內(nèi)蒙古草原所有制問題面面觀[J].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xué),1981,(4):23-46.
[10] 倪東法.實施草原法規(guī)加強草原法制管理[J].中國草原,1986,(6):71-75.
[11] 倪東法.草牧場有償承包使用淺識[J].內(nèi)蒙古草業(yè),1997,(6):6-13.
[12] 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農(nóng)牧業(yè)經(jīng)濟“十一五”發(fā)展規(guī)劃(2006~2010)[Z].2007/4/20.
[13] 郭建.在全區(qū)農(nóng)牧業(yè)工作會議上的講話[R].2017-02-17.
[14] 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草原生態(tài)保護補助獎勵政策實施指導(dǎo)意見(征求意見稿)(2016-2020)[R].2016-03.
[15] 2017年農(nóng)業(yè)部承包地確權(quán)登記最新政策以及進展[EB/OL].土流網(wǎng), http://www.tuliu.com/read-49599.html,2017-01-06.
[16] 李林杰.草原確權(quán)讓牧民的資產(chǎn)“活”起來[EB/OL]. 正北方網(wǎng)-內(nèi)蒙古日報,http://www.northnews.cn/2016/1223/2343291.shtml,2016-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