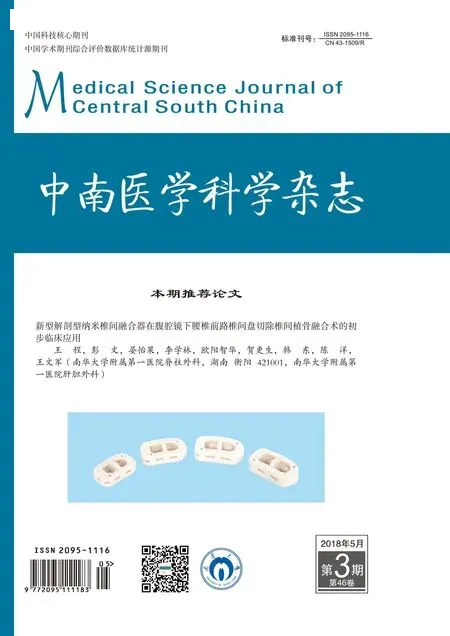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學體內模型的研究進展
,王軍
(南華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脊柱外科,湖南 衡陽 421001)
脊柱生物力學模型是研究脊柱相關疾病發生、發展的重要基礎,因此其在脊柱相關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1]。通過對模型的觀察和測試,可探索脊柱在疾病演變過程中以及受到人為干預時所發生的病理生理改變,并研究其機制。根據模型的應用方向以及研究目的的不同,Panjabi[2]將其大致分為物理學模型,體外模型,體內模型和計算機模型,共四大類。其中,僅有脊柱生物力學體內模型可有效模擬脊柱融合手術干預下脊柱植骨融合的生理病理過程[3],因此在研究脊柱融合過程中,通過實驗動物構建一種能夠更加準確模擬人類脊柱融合生理過程的生物力學體內模型成為進行相關試驗的前提。
大量學者已通過體外實驗證實山羊脊柱生物力學模型在生物力學屬性上與人類有一定相似度[4-5],可以進行相關器械評價。基于以上理由,部分學者利用山羊構建脊柱生物力學體內模型并進行脊柱融合相關研究[6],本文將對不同手術方式構建的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學體內模型的研究進展進行詳細闡述。見表1。

表1 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學體內模型匯總
1 頸椎前路
山羊頸部粗壯,且平靜時與地面呈垂直的直立狀態,大多學者認為其頸部生物力學環境及局部解剖與人類大致相同[7],因此在早期便通過山羊構建頸椎脊柱融合生物力學模型。同時Kandziora等[8]學者通過詳細對比了羊和人的頸椎生物力學、解剖形態、影像學和骨密度等,驗證了前人的觀點,認為羊和人頸椎具有良好的可比性和相似性,是一種用于頸椎疾病相關研究可行的動物模型。
1.1頸椎前路椎間盤切除融合模型最早于1992年Zdeblick TA等[9]首次構建21只山羊頸椎前路椎間盤切除椎間植骨/不植骨融合生物力學體內模型,實驗過程中共63個頸椎手術節段,通過影像學及組織形態學發現其中不植骨的21個節段無明顯融合現象出現,植入自體骨的21個節段有10個節段出現融合,而植入新鮮冰凍異體骨的21個節段中有8個節段出現融合,并通過簡單的軸向壓縮實驗評估了各手術節段的軸向抗壓縮性能,驗證了自體骨植骨融合術后椎間隙融合率及軸向抗壓縮性能最佳的結論。此后再次于1993年構建35只山羊頸椎前路椎間盤切除椎間植骨融合內固定/非內固定生物力學動物模型[10],通過之前類似的評價手段對手術節段進行評估,率先驗證頸椎前路椎間盤切除椎間植骨融合輔以鋼板內固定的手術方式較傳統手術具有明顯的軸向抗壓縮生物力學性能。在以上兩篇文章中,Zdeblick TA均描述到山羊椎體解剖形態上雖與人體不完全相同,但其與人類相似的頸椎直立狀態能為作者提供相對合適的實驗條件,并且該模型得到的融合率與人體實驗結果相似。因此上述動物模型的成功構建,不光為沿用至今的頸椎前路椎間盤切除植骨融合內固定手術提供了詳細的動物實驗資料以及理論依據[11],同時也為后期大量學者研究頸椎前路植骨融合術相關的手術植入器械、生物工程植入材料、生長促進因子等實驗研究提供了一種切實可行的頸椎椎間盤切除融合生物力學體內模型以及系列相關評價手段。
隨著山羊頸椎前路脊柱融合生物力學體內模型的深入應用,大量學者開始更加詳細地研究該動物模型并對其手術節段的選擇、融合率以及生物力學評價手段進行了完善。Zdeblick TA等[12]也意識到在早期的實驗設計中因技術限制,導致在評價山羊手術節段的融合率以及生物力學穩定性時,評價指標過于簡單。因此,該研究團隊后期逐步對模型的評價指標進行了完善,在融合率的評價中引入了免疫組化、免疫熒光等多種評價手段,并在生物力學穩定性評價中進行了前屈后伸、側彎、旋轉等接近正常生理活動的多軸運動評估。而2006年Pascal-Moussellard H等[13]學者,通過對山羊頸椎前路椎間盤切除植骨融合動物模型評價手段進行改進,首次采用了顯微骨掃描顯示植骨界面及周圍骨組織骨小梁顯微結構,進行骨組織骨量三維定性和定量分析,為山羊脊柱融合動物模型提供了一項更為有效,并且可定量的評估手段。Agazzi S等[14]學者則針對頸椎前路手術相關解剖學基礎,基于頸椎前路手術的需求對山羊頸椎結構進行更為詳細的解剖學研究,其研究結果表明山羊頸部較長,且頸前組織結構簡單,寰椎位置容易觸及,無論是定位還是暴露均相對容易。而山羊頸2/3椎體終板平坦,互相平行,并垂直于椎管長軸,遠端椎體終板大多呈穹窿狀,和終板角度明顯大于90°,這一解剖形態與人體相似。因此認為山羊頸椎前路椎間盤切除植骨融合生物力學體內模型在解剖特點上比較適于進行相關研究,同時手術節段應確立在頸2~3節段為宜,該結論為大多學者進行山羊頸椎前路脊柱融合模型應用的節段選擇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
1.2頸椎前路椎體次全切除融合模型基于前人在山羊頸椎前路脊柱融合生物力學體內模型的深入研究,目前該生物力學模型已十分成熟。近年來隨著3D打印技術的迅速發展,3D打印人工椎體或椎間融合器目前已開展了動物實驗。劉忠軍教授團隊作為進行世界上首例3D打印人工椎體臨床應用的研究團隊[15],在其自主設計的3D打印微孔結構人工椎體的動物實驗中[16],考慮到頸椎序列、骨骼結構、生物力學特征以及對感染的抵抗力等問題,選擇了山羊頸椎前路脊柱融合生物力學動物模型對3D打印微孔結構人工椎體通過Micro-CT、免疫組化以及掃描電鏡評價其融合情況,同時利用生物力學試驗機對融合節段進行壓縮、拉伸、前屈、后伸、側屈、旋轉等生物力學測試,并且進行了2 500次的反復疲勞試驗,以評估其生物力學穩定性。其實驗結果表明3D打印微孔人工椎體安全、可靠,同時該人工椎體因其獨特的微孔結構具有可觀的植骨融合率以及穩定的生物力學強度。
2 胸腰椎前路
在山羊頸椎前路脊柱融合模型應用的同一時期,因山羊的胸腰椎椎體解剖形態、大小以及數目均與人類大致相同[17],便有學者嘗試通過構建山羊胸腰椎前路脊柱融合動物模型,來評價胸腰椎融合材料或器械的植骨融合率等指標,并獲得成功。
2.1胸腰椎前路椎間盤切除/椎體次全切除融合模型最早于1994年Brantigan JW等[18]便通過構建27只西班牙山羊腰椎前路椎間盤切除植骨融合模型,用以驗證碳纖維椎間融合器的植骨融合效率。其實驗結果表明碳纖維椎間融合器在脊柱椎間融合器植骨融合率上較傳統同種異體骨具有更快、更可靠的優勢,同時也驗證了山羊腰椎前路椎間盤切除椎間植骨融合模型的可行性,但該實驗中單純通過對大體標本進行觀察、X線和CT等影像學評價以及組織形態學等相關評價手段,并未針對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學模型的優勢進行全方位的生物力學分析,從抗壓縮、抗旋轉等生物力學指標分析椎間融合后的應力強度。隨后Pintar FA等[19]重復了以上部分實驗,用以評估羥基磷灰石與自體骨椎間植骨脊柱融合上的區別,在此研究中第一次將生物力學評價指標引入山羊腰椎前路脊柱融合模型融合效果的評價,對手術節段標本進行軸向壓縮、前屈、后伸、側彎及旋轉強度等評價,其生物力學實驗結果表明在任何運動加載狀況下,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均不存在統計學差異。該模型的成功構建以及該實驗中體現出良好的生物力學測試可靠性再一次說明了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學模型具有一定優勢。自此山羊腰椎前路脊柱融合動物模型開始大范圍推廣,并且得到了國際上大多數學者的認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骨科研究中心于2002年~2007年與Skeletal Tissue Engineering Group Amsterdam (STEGA)合作,均通過構建山羊腰椎前路椎間融合器植骨脊柱融合模型來評價其研發的可吸收聚左旋乳酸椎間融合器或其他椎間融合系統的可靠性,并完成長達3年的動物實驗體內研究,這為后期進行相關材料的研發與評價提供了可靠的實踐基礎[20-22]。并且目前比較熱門的由納米羥基磷灰石等可吸收材料制備的胸腰椎椎間融合器,均通過山羊胸腰椎前路椎間融合模型進行長期的動物實驗,通過該模型驗證可吸收材料在生理條件下降解的速率、吸收后的周邊組織反應以及完全吸收后骨替代后的生物力學性能[23-24]。
在椎間盤內壓力直接測量裝置研究早期,傳統觀念認為四足動物因其四足著地脊柱呈水平位與人類具有明顯差異,因此認為其椎間盤內壓力遠遠小于人體椎間盤所承受的軸向壓力。但是,也有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羊因其胸腰背部肌肉呈持續收縮狀態,且其背最長肌為全身肌肉力量最強的肌群,在此基礎上肌肉的被動張力使得大量負荷作用于脊柱,而對椎間盤產生高強度的壓力,因此認為羊的椎間盤內壓力并不低于人類,甚至更高。Reitmaier等[25]通過在羊的腰椎間盤內安裝壓力感應裝置,24 h監測羊的日常活動后發現,在安靜狀態下羊椎間盤內壓接近于人類。而強制站立時,羊椎間盤內壓遠遠高于人類椎間盤內壓。由此認為,羊的生理狀況下椎間盤內壓力與人較為相似,且椎間盤生理結構及形態基本類似,所以羊是研究壓力相關的椎間盤退變的理想模型。基于此理論近年大多學者開始利用山羊構建胸腰椎融合生物力學模型,以研究脊柱融合后鄰近關節退變的機制及影響。2008年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骨科研究中心Hoogendoorn RJ等[26]構建了13只山羊腰椎前路椎間融合器植骨脊柱融合模型,并對其隨訪6個月,通過磁共振影像學、組織形態學等相關評價指標,用以研究山羊前路胸腰椎融合模型相鄰節段椎間盤退變的發展以及相關機制。該模型的成功構建為未來構建山羊脊柱融合鄰近椎間盤退變模型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也有望通過該方式構建山羊壓力誘導椎間盤退變模型。
2.2腔鏡下胸腰椎前路椎間盤切除融合模型隨著腔鏡技術在脊柱外科的迅速發展以及廣泛應用,大量胸腰椎前路手術采用腔鏡輔助下完成,因此部分學者通過腔鏡技術構建山羊胸腰椎前路脊柱融合模型,并且通過山羊與人類較為類似的解剖結構,進行手術方式以及手術操作本身對椎間融合率影響等相關研究。Sucato DJ等[27]于2002年將12只山羊隨機分為部分血管結扎組及血管不結扎組,其實驗第一步通過針對腹腔鏡下部分血管結扎與血管不結扎組不同的手術操作,驗證以上兩種情況下椎間盤切除的效果,其實驗結果表明兩組無統計學意義。第二步則是通過腹腔鏡輔助下構建胸椎前路椎間盤切除髂骨植骨融合模型,術后4個月對實驗動物手術節段標本進行椎間融合效果的組織學、影像學及生物力學評價。其結論顯示腹腔鏡下山羊胸椎前路椎間盤切除髂骨植骨融合模型構建過程中,術中選擇性血管結扎可能導致椎間隙植骨塊供血缺失,從而導致植骨不融合或其他并發癥的發生。該模型的成功構建不僅說明了可以通過腔鏡技術構建山羊胸腰椎前路脊柱融合模型,同時也說明了山羊較人類相似的解剖結構,可以提供給脊柱外科醫生更加真實的模擬效果以及更加廣闊的實驗空間,可廣泛應用于未來腔鏡下胸腰椎前路手術的操作培訓和臨床研究。
3 胸腰椎后路
山羊胸腰椎后路脊柱融合模型較通過其他方式構建的脊柱融合模型應用更少,這可能是胸腰椎后路進行椎間盤切除椎間植骨融合手術損傷大,風險高。并且山羊椎弓根形態成扁平狀,可容納的椎弓根螺釘直徑較小[28],與人類相比具有一定差異。但仍有部分學者在山羊胸腰椎后路橫突間融合模型以及其他類型的模型進行了一些嘗試。
山羊胸腰椎后路脊柱融合生物力學模型應用過程中,部分學者針對了山羊胸腰椎后路與人類較為相似的解剖結構與椎間盤生物力學屬性構建了相關模型用于相關研究。國內學者郝永宏等[29]通過行山羊后路正中切口,充分暴露腰4、5節段,將腰5雙側峽部用磨鉆磨斷,并在雙側峽部斷裂處各放置一阻止其骨折愈合的金屬片,并于術后喂養8周的方式,構建了16只山羊第5腰椎峽部不連模型,用以驗證其自行研發的腰椎峽部重建內固定器具有明顯的穩壓和加壓的雙重力學功效。通過該方式構建山羊腰椎峽部不連模型,再通過后路手術對峽部不連進行修復融合處理,該動物模型研究方案較為新穎,且手術難度及術后護理等方面相對簡單,是一種專門針對腰椎峽部裂修補融合術的動物模型,具有一定可行性和有效性。而顧軍等人[30]則利用山羊腰椎椎間盤生物力學屬性與人類基本一致的優勢,采用不同長度的5.0 mm椎弓根螺釘進行后路固定,再通過小關節融合,構建12只波爾雜交山羊腰椎后路椎弓根釘棒系統內固定脊柱融合模型,用于觀察脊柱內固定術中不同椎弓根螺釘植入深度對鄰椎生物力學環境和退行性變的影響,探討腰椎后路內固定系統力學強度與鄰近椎體椎間盤退變之間的取舍。其實驗結果顯示在山羊腰椎內固定融合術中,長椎弓根螺釘提供的局部堅強固定可能增加上位未融合節段的活動和承受的應力,促進椎間盤退行性變,導致鄰近椎間盤退變性疾病的發生。但山羊椎弓根呈扁平狀的獨特解剖結構帶來的胸腰椎后路椎弓根釘棒系統內固定融合模型更大的手術置釘難度在該文中也有體現,顧軍等人則通過減少螺釘直徑來避免術中椎弓根螺釘突破椎弓根內側皮質造成的神經損傷。以上闡述的兩種較為新穎的山羊后路脊柱融合生物力學模型,均充分利用了山羊胸腰椎解剖結構以及生物力學屬性與人類相似的優點,從不同角度進行脊柱融合相關生物力學分析,此構建模式也帶來了更多的思路。
4 問題與展望
雖然目前采用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學體內模型的相關文獻報道尚不多,但從其呈逐年增加的趨勢可以明確,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學體內模型逐漸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同時因山羊其直立頸椎所帶來的力學性能、比例相近的胸腰椎椎體結構以及與人類相似的胸腰椎椎間盤內壓力等,不難看出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學模型的優勢。雖然目前在構建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學體內模型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但通過逐漸實現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學體內模型手術構建中麻醉控制安全化、手術操作精細化、實驗動物生產和飼養規模化以及對山羊種系研究的逐漸深入,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學模型必將在3D打印、干細胞、組織工程、生物力學等多個新興技術領域扮演重要角色。總之,近20余年來山羊脊柱融合模型的發展趨勢,讓作者看到了該動物模型未來的潛力,作為一種多功能新型脊柱融合生物力學體內模型廣泛應用于實驗研究一線。
參考文獻:
[1] 文彬, 鄧鑫. 生物力學模型在醫學研究中的應用與展望[J].醫學研究雜志,2014,43(1):142-4.
[2] PANJABI MM. Cervical spine models for biomechanical research[J]. Spine, 1998,23(24):2684-700.
[3] 昌耘冰. 頸椎生物力學模型的應用及進展[J].中國臨床解剖學雜志,2003(2):187-9.
[4] PETERSON JM, CHLEBEK C, CLOUGH AM,et al.Stiffness matters: part I-the effects of plate stiffness on the biomechanics of ACDF in vitro[J]. Spine,2018.
[5] 黃師, 侯鐵勝, 趙鑫, 等. 山羊頸椎能成為人類頸椎的良好模型嗎?[J].中國臨床解剖學雜志,2008(3):329-31.
[6] MACEWAN MR, TALCOTT MR, MORAN DW, et al. Novel spinal instrumentation to enhance osteogenesis and fusion: a preliminary study[J]. J Neurosurg Spine, 2016,25(3):318-27.
[7] 婁紀剛, 劉浩, 武文杰, 等. 新型人工頸椎間盤山羊模型的建立及其研究[J].實用骨科雜志,2017,23(5):426-9.
[8] KANDZIORA F, PFLUGMACHER R ,SCHOLZ M, et al. Comparison between sheep and human cervical spines: an anatomic, radiographic,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biomechanical study[J]. Spine,2001,26(9):1028-37.
[9] ZDEBLICK TA, WILSON D, COOKE ME, et al. Anterior cervical discectomy and fusion. A comparison of techniques in an animal model[J]. Spine , 1992,17(10):S418-26.
[10] ZDEBLICK TA, COOKE ME, WILSON D, et al. Anterior cervical discectomy, fusion, and plating. A comparative animal study[J]. Spine, 1993,18(14):1974-83.
[11] LI XH, SONG YM, DUAN H. Reconstruction of segmental stability of goat cervical spine with poly (D, L-lactic acid) cage[J]. Orthop Surg, 2015,7(3):266-72.
[12] ZDEBLICK TA,COOKE ME, KUNZ DN, et al. Anterior cervical discectomy and fusion using a porous hydroxyapatite bone graft substitute[J]. Spine, 1994,19(20):2348-57.
[13] PASCAL-MOUSSELLARD H,BRUNET-IMBAULT B,AGUADO EPascal-Moussellard H, et al.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microscan assessment of bone fusion[J]. Rev Chir Orthop Reparatrice Appar Mot, 2006,92(6):535-42.
[14] AGAZZI S,VANLOVEREN HR, TRAHAN CJ, et al. Refinement of interbody implant testing in goats: a surgical and morphometric rationale for selection of a cervical level.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J]. J Neurosurg Spine, 2007,7(5):549-53.
[15] XU N, WEI F, LIU X, et 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upper cervical spine using a personalized 3D-printed vertebral body in an adolescent with ewing sarcoma[J]. Spine, 2016,41(1):E50-4.
[16] YANG J, CAI H, LV J, et al. In vivo study of a self-stabilizing artificial vertebral body fabricated by electron beam melting[J]. Spine (Phila Pa 1976), 2014,39(8):E486-92.
[17] WILKE HJ, KETTLER A, WENGER KH, et al. Anatomy of the sheep spine and its comparison to the human spine[J]. Anat Rec, 1997,247(4):542-55.
[18] BARANTIGAN JW, MCAGFEE PC, CUNNINGHAM BW, et al. Interbody lumbar fusion using a carbon fiber cage implant versus allograft bone. An investigational study in the Spanish goat[J]. Spine, 1994,19(13):1436-44.
[19] PINTAR FA, MAIMAN DJ, HOLLOWELL JP, et al. Fusion rate and biomechanical stiffness of hydroxylapatite versus autogenous bone grafts for anterior discectomy. An in vivo animal study[J]. Spine, 1994,19(22):2524-8.
[20] MULLENDER MG, KRIJNEN MR, HELDER MN, et al. Lumbar body fusion with a bioresorbable cage in a goat model is delayed by the use of a carboxymethylcellulose-stabilized collagenous rhOP-1 device[J]. J Orthop Res, 2007,25(1):132-41.
[21] KRIJNEN MR, MULLENDER MG, SMIT TH, et al. Radiographic, histologic, and chemical evaluation of bioresorbable 70/30 poly-L-lactide-CO-D, L-lactideinterbody fusion cages in a goat model[J]. Spine (Phila Pa 1976), 2006,31(14):1559-67.
[22] SMIT TH, THOMAS KA,HOOGENDOOM RJ, et al. Sterilization and strength of 70/30 polylactide cages: e-beam versus ethylene oxide[J]. Spine (Phila Pa 1976), 2007,32(7):742-7.
[23] 薛有地, 宋躍明, 劉立岷, 等. 聚氨基酸/納米羥基磷灰石/硫酸鈣融合器在山羊腰椎椎間融合中的作用研究[J].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2015,29(8):972-7.
[24] 滕海軍, 周躍, 范麗靜, 等. 可吸收腰椎間融合器降解過程的動物實驗研究[J].頸腰痛雜志,2010,31(1):16-9.
[25] REITMAIER S, SCHMIDT H, IHLER R, et al.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s on intradiscal pressures during daily activities: an in vivo study using the merino sheep[J]. PLoS One, 2013,8(7):e69610.
[26] HOOGENDOOM RJ, HELDER MN, WUISMAN PI, et al. 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 observations in a goat spinal fusion study[J]. Spine, 2008,33(12):1337-43.
[27] SUCATO DJ, WELCH RD, PIERCE B, et al. Thoracoscopic discectomy and fusion in an animal model: safe and effective when segmental blood vessels are spared[J]. Spine, 2002,27(8):880-6.
[28] 田勇, 王陽, 夏長麗, 等. 鹿、羊和人腰椎形態計量學關聯性分析[J].吉林大學學報(醫學版),2010,36(1):163-8;217.
[29] 郝永宏, 鄧樹才, 趙合元, 等. 腰椎峽部重建內固定器的設計及應用實驗[J].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2009,23(4):408-11.
[30] 顧軍, 王以進, 端木群力, 等. 山羊腰椎內固定術中椎弓根螺釘植入深度對鄰椎的影響[J].中國骨傷,2010,23(11):8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