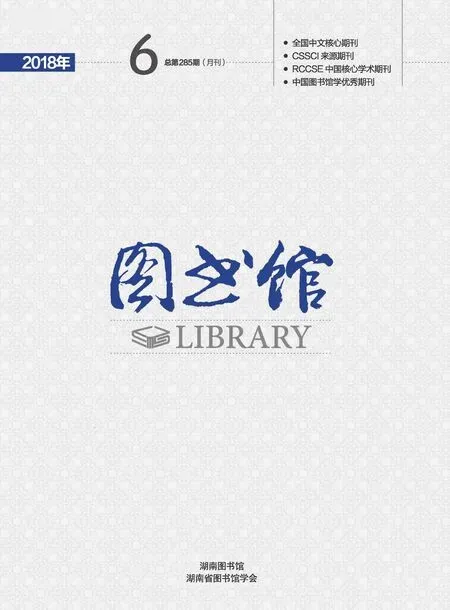創新驅動背景下企業知識轉移的系統動力學研究*
儲節旺 李章超
(安徽大學管理學院 合肥 230601)
1 引言
創新驅動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引擎,知識成為創新驅動的主要要素投入[1-2]。知識管理作為實現知識增值而采取的一系列規劃和行動,越來越得到企業的重視,作為知識管理重要一環的知識轉移也成為許多企業構筑競爭優勢的關鍵基礎[3]。知識轉移構成一個復雜的社會經濟系統,其中存在著制約和促進系統發展的反饋結構[4]。因此,知識轉移系統的運行機制及影響因素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
目前知識轉移系統的研究主要基于“兩主體論”,即知識轉移存在于外部知識源和企業之間。然而作為企業兩個不同部門的知識系統和創新平臺在知識轉移過程中承擔著不同功能,知識系統是知識轉移的中介,主要是增強知識系統功能,側重于知識接受和加工;創新平臺是知識轉移的最終環,目的是增強創新主體的創新能力,傾向于知識利用[5]。因此文章秉持企業知識轉移的“三主體論”,認為知識轉移存在于外部知識源、企業知識系統及企業創新平臺之間。另外,有效的知識轉移能夠提高企業創新效率,增加企業創新績效[6]。而傳統意義上的知識轉移是對狹義的知識流動進行研究,多為由知識源到企業的單調過程,沒有考慮到企業對于知識再轉移的影響作用。
目前針對知識轉移的研究多采用定性研究、實證研究和數理統計等方法。系統動力學認為系統是一個復雜的因果反饋機制,通過對系統進行深度剖析,尋求最優的系統結構。基于此,文章采用系統動力學的方法,研究知識轉移的運行機制和相關影響因素及知識轉移的創新保障作用,權衡創新績效與知識轉移成本間的關系,形成企業知識轉移循環。
2 企業知識轉移系統分析
2.1 企業知識轉移系統及系統結構
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轉移已經成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存在多個子系統,內部各要素都可能影響系統的運行及效果,而且內部各要素間又相互關聯。比如企業知識系統是知識轉移系統的一個子系統,它是整個傳導機制的中介,是知識轉移系統的關鍵。而企業知識系統又受到企業知識創新量、知識遺失率等多項要素影響,如此交叉形成復雜的企業知識轉移系統。
Ounjian等學者認為知識屬性、知識提供者和接收者的特性、溝通渠道是影響知識轉移的四個主要方面[7]。Albion認為知識轉移的分析應該從轉移主體、轉移意境、轉移內容和轉移媒介四個方面入手[8]。Susanty等學者則認為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合適的預算分配、文化及領導能力等原因[9]。文章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基于創新驅動的背景,從知識轉移的實際運行機制及創新保障作用的角度出發,認為影響知識轉移的因素主要來源于知識源與企業(包括知識系統和創新平臺)。知識源層面的因素包括知識屬性、知識轉移的意愿以及轉移能力等;企業層面的因素包括知識轉移情境、知識吸收能力、創新能力及對轉移成本和創新績效的衡量等[10];雙方的共同因素包括知識差距、轉移閾值等。知識具有累積性,隨著時間推移,企業接收知識轉移量越多,其知識存量也就越多。Davenport等提出知識遺失的概念,認為知識遺失量與知識存量呈正相關關系[11]。綜上,文章基于知識轉移的創新保障作用,將知識系統變量和創新平臺變量分別擴展到“知識轉移存量”和“創新績效”,引入“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作為中介變量,表1為知識轉移模型關鍵變量。

表1 知識轉移模型關鍵變量
2.2 企業知識轉移過程分析
日本學者野中郁次郎針對顯性和隱性兩種不同知識形態在不同層次間轉換的問題,構建SECI知識螺旋模型[12]。由于SECI模型的不完善,后來的學者提出知識轉移階段論。Szulanski構建知識轉移四階段模型,知識從知識源流動到知識受體需要經歷初始、執行、沖刺和整合四個階段[13]。Gilbert等學者認為知識轉移需要經過知識的獲取、溝通、應用、接受和吸收五個階段的不斷學習,才能達成組織或個人的目標[14]。Davenport等提出知識轉移“兩步論”,認為知識轉移包括傳遞和吸收兩個過程,外部知識源將知識傳遞給企業,企業根據自身能力對接收的知識進行吸收和利用[11]。基于此文章構建企業知識轉移過程模型,見圖1。

圖1 企業知識轉移過程模型
創新驅動背景下的企業知識轉移不僅是狹義的知識流動過程,還包括反饋和循環。主要包括兩個循環,其含義分別是知識源將知識發送給企業,企業權衡自身情況及知識轉移成本決定是否接受,再根據轉移知識帶來的創新績效決定是否利用;企業吸收知識之后進行整合創新,知識源在權衡創新績效之后決定是否繼續向企業進行知識轉移。
2.3 企業知識轉移系統的因果分析
宋燕等學者認為知識轉移量受知識差距、知識轉移閾值、知識吸收能力、知識需求參數和知識轉移情境五個因素的影響[10]。文章在對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研究后認為知識轉移總量還受知識轉移成本等因素影響。其中,知識差距是知識源與企業知識系統間知識存量的差距,知識源對企業的知識順差越大,知識轉移的必要性越高,知識轉移效率越高,轉移量越大。知識轉移閾值是指知識源向企業轉移知識的臨界值,即對自身核心知識的保護,知識轉移閾值與知識轉移量呈負相關。知識吸收能力是知識成功轉移的重要保證,吸收能力高的企業能夠很好地理解和吸收知識源發送的知識。知識需求參數指企業對接收的知識的需求程度及重視程度,知識需求參數與知識轉移總量呈正相關。知識轉移在具體的情境中進行,徐金發從文化、戰略、組織結構和過程、環境及技術和運營五個層面對知識轉移的情境范圍進行探討[15]。知識轉移成本是企業進行知識轉移所要支付的各種形式支出,它與知識轉移總量呈負相關。隨著知識轉移量的增加,知識遺失量也不斷增加[10],由于外部知識來源多、異質性強、基數大,因此文章僅考慮企業知識系統的知識遺失。
創新是知識轉移的最終目的,創新績效是企業創新水平的重要評價標準,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因素包括知識創新量、知識匹配、平均知識水平和知識轉移成本績效等。知識創新量是企業知識系統對接收到的知識進行整合得到的創新知識的數量,知識創新量與創新績效呈正相關。知識匹配是將企業創新平臺的核心知識與接收到的知識進行匹配,可分為互補知識和替代知識,其中互補知識是實現創新的最優因素,替代知識則可以取代企業舊知識。平均知識水平是對企業知識系統和創新平臺知識總體水平的評價,與企業創新績效呈正相關。知識轉移成本績效是創新績效和知識轉移成本的比值,是企業對創新績效和成本的衡量,成本績效與創新績效呈正相關。創新能力和平均知識水平也是影響企業知識創新績效的重要因素,與創新績效呈正相關關系。基于此,文章構建企業知識轉移因果關系模型圖(見圖2)。
①知識轉移模型以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知識轉移量及創新績效為邊界,因此反饋回路以此為主,以下為主要反饋回路。②知識系統知識存量的減少,使得知識差距加大,知識轉移量增加,進而知識系統知識存量增加。③知識系統知識存量的增加,導致轉移閾值變大,知識轉移量降低,使得知識系統知識存量減少。④知識系統知識存量的增加,使得知識創新率提高,知識創新量出現增長,使得知識遺失量相對減少或者創新績效的增長,最終知識系統知識存量出現增長。⑤知識轉移量的增加使得知識系統知識存量出現增加,因此知識系統與創新平臺的知識匹配概率越大、程度越高或者提升企業平均知識水平,進而創新績效得到增加,致使知識轉移量繼續增加。⑥知識轉移量增加,知識系統知識存量越大,使得知識創新率出現增長,知識創新量出現提升,因此創新績效增加,最終使得知識轉移量擴大。
創新績效的增長,使得知識轉移量變大,因此知識系統知識存量增加,知識創新率出現增長,提升知識創新量,最終促進創新績效的繼續增長。

圖2 企業知識轉移的因果關系模型
3 企業知識轉移的系統動力學模型
佛里斯特認為系統動力學是對整體運作的本質進行思考,將結構的方法、功能的方法和歷史的方法融合成一個整體,從而提升人類組織的“群體智力”。系統動力學基于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協同論和結構論的思想,結合經濟學,以數字計算機仿真技術為手段,它能使人們清晰地認識并深入處理產生于現代社會的非線性和時變現象[16]。創新驅動背景下的知識轉移系統主要研究知識轉移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具有明確的系統結構。另外,企業知識轉移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涉及企業內外的多項要素,系統結構較為復雜,同時企業知識轉移與企業創新之間存在復雜的非線性關系。
3.1 假設調節
為了簡化模型,反映模型的本質問題,在仿真年限內,筆者對相關條件設置限定:①模型中的知識可以被量化。②知識源知識存量的初始值是固定的,且大于企業知識存量。③企業知識系統和企業創新平臺是兩個不同的系統,知識源知識首先轉移至企業知識系統,再由知識系統整合創新轉移至企業創新平臺。④穩定的知識轉移情境。
3.2 企業知識轉移模型流圖
創新驅動背景下的知識轉移需要權衡知識轉移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企業創新績效受到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的影響,而知識轉移量又是知識系統知識存量的基礎。因此文章構建知識轉移系統流圖(見圖3)。

圖3 企業知識轉移模型流圖
3.3 方程式構建與參數設定
在對企業轉移模型進行仿真運行之前,需要對模型中的狀態變量、流率變量、輔助變量進行方程構建,對于常量進行賦值。文章根據企業知識轉移系統的結構特點及變量特征,在參閱相關文獻后通過相關方法(見表2)對方程與參數進行初始設定,在多次預仿真后對參數進行調整后得到如下設定:
知識源知識存量=WITH LOOK UP ( Time,( [(0,0)-(4,300 )],(0,100),(24,400)) )。國內學者魏瑞斌基于學術論文數量、專利數量、創意產品產值、版稅與許可費以及高等院校入校率等理論,提出以國內知識總量(Gross Domestic Knowledge,GDK)的測度指標來衡量國內知識總量[17]。基于此理論,文章假設知識源知識存量初始值為100,設定知識總量增速為每年100%。
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INTEG(企業知識創新量+知識轉移量-企業知識遺失量,5)。國內學者譚婉君認為不同企業知識存量不一致,文章采用其對中等知識存量評級的數值,賦值為5。
企業創新平臺知識存量=WITH LOOK UP(Time,([([(0,0)-(24,2)],(0,5),(12,6),(24,7.2)))。曹興等學者認為企業知識結構由公共知識、基礎知識和核心知識構成[18],其中核心知識是企業進行創新的主要知識構成。根據“二八原則”,文章賦值企業創新平臺知識初始存量為5,增速為每年20%。
知識差距=知識源知識存量-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
轉移閾值=IF THEN ELSE(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知識源知識存量<0.9,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知識源知識存量,0.9),閾值是知識源對企業知識系統轉移知識的臨界值,是對自身核心知識的保護,即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與知識源知識存量之間比例達0.9時,知識源停止進行知識轉移。
平均知識水平=(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企業創新平臺知識存量)/2
知識匹配=IF THEN ELSE(企業創新平臺知識存量/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1,企業創新平臺知識存量/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1),即企業知識系統的知識存量和創新平臺知識存量之間存在順差,創新才能進行。
需求參數=0.8
轉移情境=戰略*技術和運營*文化*環境*組織結構和過程,文章重點研究知識轉移的績效水平,因此設定影響轉移情境的因素均為正常數,取值均為(0,1)。
吸收能力= WITH LOOK UP(Time,([((0,0)-(24,0.3)],(0,0.6),(24,0.9)) ),企業知識吸收能力受知識基礎、創新活動、管理因素及內外部環境各種因素影響,且呈現動態變化趨勢[19-20],因此選取表函數表示企業知識吸收能力在仿真期間的動態變化。
轉移成本=0.3
企業知識創新率=0.1
企業知識創新量=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企業知識創新率
企業知識遺失率=0.01
企業知識遺失量= STEP(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企業知識遺失率,2)。“艾賓浩斯記憶曲線”認為知識遺失是一個過程,此階躍函數表明在2個月后,企業開始產生知識遺失。
創新率 = WITH LOOK UP(Time,([(0,0)-(24,0.2)],(0,0.2),(24,0.4)) ),隨著企業創新平臺知識存量的增加,企業創新率也會提升,由最初0.2到最終0.4。
創新績效=[創新率*平均知識水平*知識匹配*(企業創新平臺知識存量+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0.3]。企業創新績效基于創新平臺及知識系統的知識創新量,綜合考慮創新率等因素,創新績效初始值為0.3。
績效預測=創新績效*0.6,績效預測是綜合上階段企業創新績效等因素對企業現階段創新績效的預估。
轉移成本績效= IF THEN ELSE(績效預測/轉移成本<1, 績效預測/轉移成本,1)。轉移成本績效是預估績效與轉移成本的比值,是企業衡量是否進行知識轉移的重要因素,如果比值在1以下或者逐漸變小時,企業應當采取糾正措施或停止該次知識轉移。
知識轉移量= DELAY1I(IF THEN ELSE(轉移閾值<0.9,轉移成本績效*需求參數*轉移情境*吸收能力*知識差距*轉移成本,0),2,0)。由于知識轉移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需要知識源和企業知識系統的各項工作,因此使用一階延遲函數,一般2個月后實現轉移。

表2 參數設定方法
4 企業知識轉移系統的仿真分析
文章使用Vensim PLE對知識轉移系統模型進行仿真與參數靈敏度分析,仿真時長為24個月,變量仿真結果如圖4所示。

圖4 企業知識轉移模型仿真圖
4.1 仿真分析
對模型進行仿真后的結果可得出以下結論:
知識源和企業知識系統的知識存量呈現增長趨勢,雙方知識差距逐漸拉大。因為知識源知識存量初始值大于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其次由于科學技術尤其是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知識源的知識存量呈現爆炸式增長趨勢。社會化網絡的完善以及自媒體的產生使得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知識生產者,然而相對于知識源,企業知識系統相對封閉,知識創新率較低,導致雙方知識差距逐漸拉大。
在仿真期間,知識轉移量在前期較長時間內波動增長,且增速較慢,后期出現下降。知識轉移是外部知識源和企業雙方相互選擇與磨合的過程,企業需要權衡轉移成本績效等各方面的因素,導致知識轉移量的不穩定;知識源需要對自身核心知識進行保護等因素導致知識轉移量下降。
企業平均知識水平得到提升。企業知識系統將接收的外部知識進行整合創新,然后將新的知識轉移至企業創新平臺,從而增強了企業知識水平。
轉移成本績效迅速增長。由于企業在知識轉移前期缺乏經驗,知識轉移成本績效指數小于1,即創新績效小于知識成本,企業在采取相應的糾正措施后,創新績效迅速增長。
企業知識創新量逐漸增長,且增速與企業知識系統知識量趨同。因為知識創新量對企業知識系統存量影響較大,所以二者的增速趨同符合客觀規律。
企業知識系統的知識存量,知識轉移量,平均知識水平及知識創新量在仿真后期出現增速加快的趨勢。知識轉移是一個過程,在知識轉移后期,由于企業吸收能力的提升、相關經驗及配套設施的完善,知識源解除初期進行知識轉移的試探心理等原因都會造成變量增速的加快。
創新績效呈現增長趨勢,且增速明顯大于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及知識轉移量。因為知識轉移為企業知識創新及創新平臺創新提供了知識保障,同時進一步優化了組織結構及組織文化等方面為企業提供了組織保障,這雙重保障了企業創新績效的快速增長。
4.2 相關參數的靈敏度分析
靈敏度分析對于知識轉移系統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分析可以確定系統參數對仿真模型的影響程度。文章采用局部靈敏度分析的因子變化法,每次針對一個參數增加或減少10%,對其他參數取其中心值,評價模型結果在該參數每次發生變化時的變化量[21]。
4.3 知識轉移量相關的靈敏度分析
系統初始參數的仿真結果為Current。在保持其他參數不變的前提下,分別將吸收能力(方案Current1)、需求參數(方案Current2)、轉移成本績效(方案Current3)及知識轉移情境(方案Current4)的取值提高10%,結果如圖5所示。

圖5 關于知識轉移量變量的靈敏度分析
從圖5可以看出知識轉移量隨著不同參數值的提高而出現不同程度地增長,但是漲幅不大。企業吸收知識能力及需求參數的增加提升了知識轉移的質量和數量;轉移成本績效增加意味著創新績效的增加,企業需要更多的知識轉移量來支撐企業創新平臺的創新;另外,企業靈活的戰略、寬松的環境、開放的文化、合理的組織結構和過程以及先進的技術和運營都會不同程度地增加知識轉移量。知識轉移量增幅不大是因為企業知識轉移涉及多方面的因素,每一個因素都可能會對知識轉移量產生影響,不會因為系統某一特定因素的變化而出現大幅度變動。
4.4 創新績效相關的靈敏度分析
系統初始參數的仿真結果為Current。在保持其他參數不變的前提下,分別提高企業知識創新率(方案Current1)、創新平臺知識存量(方案Current2)、創新平臺創新率(方案Current3)及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方案Current4)的取值,結果如圖6所示。

圖6 關于創新績效變量的靈敏度分析
由圖6可以看出,在相同仿真期間,提高企業知識創新率、創新平臺和知識系統知識存量和創新平臺創新率的取值,企業創新績效會隨之增加,且有較大漲幅。企業知識創新率的提高使得企業知識系統的知識存量和核心知識占有量提升,為創新平臺進行創新提供知識支撐,且企業知識系統知識存量的增加帶來了創新績效較大幅度的增加;企業創新平臺知識包括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兩個部分,顯性知識的增加能夠提高企業知識水平及知識匹配能力,增加隱性知識則能夠提升創新水平,為創新注入新活力;提升創新平臺的創新率能夠避免知識浪費,使企業利用有限的知識量提升創新績效。企業知識轉移的最終目的在于創新,企業通過知識轉移獲得較多知識存量后,企業創新率等因素對于創新績效的影響尤為重要,因此企業創新績效出現較大漲幅。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創新是第一驅動力,創新越來越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動力,成為創新保障的知識成為企業發展的關鍵。通過以上的綜述與研究,得出結論:
(1)知識轉移對企業創新績效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創新驅動背景下企業知識轉移流程是:知識從外部知識源轉移到企業知識系統,由知識系統對接收到的知識進行整合創新,然后將新知識轉移到創新平臺,由創新平臺進行利用,形成創新績效,企業權衡創新績效與知識轉移成本后決定是否繼續進行知識轉移,如此往返形成知識轉移循環。
(2)知識轉移量的大小決定企業知識系統的知識存量,知識轉移量受企業需求參數、知識差距、轉移閾值轉移情境及吸收能力的影響;企業創新績效受知識系統和創新平臺的知識存量、創新率、平均知識水平及知識匹配程度等因素的影響,且受影響程度大。
5.2 建議
創新驅動背景下,創新本質上是對企業內外部知識資源的吸收、轉化、整合和再創造的過程[22],從而提升企業的創新績效,推動經濟發展。通過以上論述,文章針對企業知識轉移提出以下建議:
(1)增加和擴大企業知識需求。增加知識需求是指數量的變化,而知識需求擴大是指范圍的擴大。在創新驅動的背景下,企業應該認識到知識的重要性,主動尋求與外部知識源合作的機會,積極引進外部知識,從數量和范圍兩個層面提升企業知識素質。
(2)改善企業知識轉移情境。戰略是企業的靈魂,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應該跟上飛速發展的步伐,靈活調整企業戰略,加快企業核心競爭力創新;企業環境包括“硬環境”和“軟環境”兩個層面,“硬環境”層面,企業要加強知識轉移系統基礎設施建設,降低知識轉移損耗率;“軟環境”層面,企業要為知識轉移提供合理的激勵保障,構筑良好的轉移環境,增強外部知識源進行知識轉移的意愿。另外,企業要通過增強企業文化軟實力,獲得更多的知識轉移;組織結構的完善能夠規范企業知識行為,提升知識轉移效率,進而促進企業創新績效的提高。
(3)增強企業知識吸收能力及員工的知識素養。吸收能力的提高不僅可以提高企業知識系統的知識存量,還可以提升知識轉移質量,提升對知識的理解程度,提高知識利用率。企業可以通過提高獲取知識的欲望和積極性,增強學習努力程度,改善學習方法來增強組織或員工知識吸收能力。
(4)控制知識轉移成本。知識轉移成本績效=創新績效/知識轉移成本,降低知識轉移成本是提高知識轉移成本績效的有效途徑。具體來說,要強化成本意識,用成本效益觀念看待知識轉移;隱性知識顯性化,對隱性知識進行組織、管理、分析和傳播;通過提升知識轉移效率,降低時間成本等途徑來控制知識轉移成本。
(5)提升企業知識系統及創新平臺的創新率。知識系統的知識創新主要通過知識管理積累新知識,企業利用現代化信息技術實現企業知識資產化;將流程與知識相結合,構建企業知識管理標準化體系;加強知識轉移系統建設,規范企業知識轉移行為。創新平臺則是通過對知識系統的知識進行選擇創新,企業在強調技術內容的同時也要重視市場導向作用,并制定科學合理的技術戰略。
(6)引進和培養創新型人才。創新驅動背景下,創新型人才對于企業創新發展起著特殊的重要作用。對外,企業除了通過傳統渠道引進人才外,還要建設產學研相結合的人才引進渠道;對內,企業要堅持多方聯動,構建完善的創新型人才培養體系。
(來稿時間:2017年7月)
1.洪銀興.論創新驅動經濟發展[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
2.張銀銀,鄧玲.創新驅動傳統產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轉型升級:機理與路徑[J].經濟體制改革,2013(5):97.
3.吳婷婷.情報工作中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和模式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學碩士論文,2009.
4.賈偉強,羅艷玲,王云竹.產業集群知識轉移復雜系統反饋結構分析[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1,28(19):61-64.
5.羅偉.面向21世紀的科技進步與社會經濟發展[C]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學會學術部會議論文集.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573-574.
6.徐建敏,任榮明.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知識轉移與創新[J].河北科技大學學報,2007,28(1):66-69.
7.M.L.Ounjian, E.B.Came.A Study of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echnology Tran-sfer in a Multilocation Multibusiness Unit Corporation[J].IEEE Transaction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1987,(34):194-201.
8.朱麗君.組織的知識轉移過程[J].華人時刊:中外教育,2011(10):155-156.
9.A Susanty, NU Handayani, MY Henrawan.Key Success Factors that Influence Knowledge Transfer Effectiveness: A Case Study of Garment Sentra at Kabupaten Sragen[J].Procedia Economics & Finance, 2012, 4(3):23-32.
10.宋燕,胡飛.基于系統動力學的顧客知識轉移研究[J].情報科學,2017(2):38-43.
11.Davenport T.H., Prusak L.Work Knowledge:How organization Manage What They Know[M].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8:16-78.
12.Nonaka I, Takeuchi H.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65-89.
13.Szulanski G.Exploring internal stickiness: impediments to the transfer of best practice within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6(7):27-43.
14.Gilbert M., Cordey Hayes M.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to Achieve Successfu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Technovation,1996,16(6):301-312.
15.徐金發,許強,顧驚雷.企業知識轉移的情境分析[J].自然辯證法通訊,2003,25(2):51-56.
16.陳國衛,金家善,耿俊豹.系統動力學應用研究綜述[J].控制工程,2012,19(6):921-928.
17.魏瑞斌,武夷山.國內知識總量——GDK及其測度[J].情報雜志,2013(12):139-144,182.
18.曹興,李瑞,程小平,等.企業知識結構及其優化機制[J].科學管理研究,2006,24(6):69-73.
19.陳勁,蔣子軍,陳鈺芬.開放式創新視角下企業知識吸收能力影響因素研究[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 41(5):71-82.
20.茅寧瑩.企業知識吸收能力的分析框架與發展方向探析[J].現代管理科學,2005(9):45-47.
21.徐崇剛,胡遠滿,常禹,等.生態模型的靈敏度分析[J].應用生態學報,2004,15(6):1056-1062.
22.張煒,趙娟,童欣欣.動態知識管理能力與創新績效關系研究:創新開放度調節效應[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5(5):13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