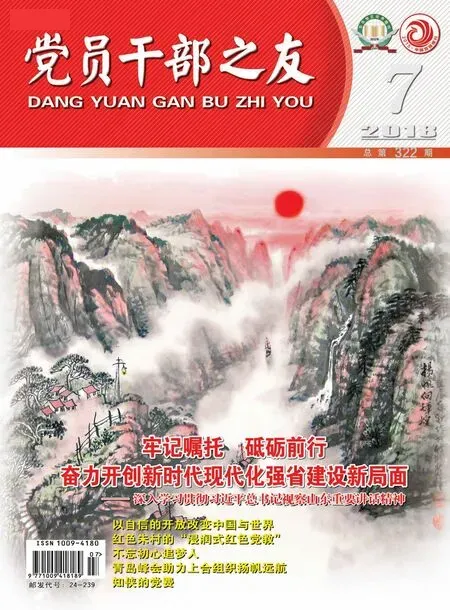麥收最憶是割麥

鹿 毅/ 圖
田野里滿眼的金黃,一陣微風吹來,那飽滿的麥穗輕輕地搖曳著,像一個個含羞的姑娘與她深愛的大地戀戀不舍地揮手告別。又到麥收時節了,腦海里又浮現出兒時割麥的情景……
三麥不如一秋長,三秋不如一麥忙。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割麥忙得讓人喘不過氣來,從碾場、收割、打場、揚場,工序一道道的,少了哪道都不行,每道工作又是那么的緊湊、艱辛,簡直就像跑馬拉松一樣,咬著牙一氣呵成。割麥子是最累的,但那也真是“累并快樂著”。
麥收時節,夜特別短,老天爺知道麥熟一晌,專門為麥收調整了作息安排,留出了更多的干活時間,讓鄉親們把一年的希望趕快撿拾曬干存好。盼了一年豐收的人們也特別沉不住氣,一趟一趟往自家的麥田里跑,看看什么時候,麥子能開始收割。芒種時節的風最懂鄉親們的心情,微微的南風吹來,一天一個麥子熟。
父親是種莊稼的老把式,正午時候,到地頭看看,麥芒已經開炸了,麥粒也已經快掐不動了,地里的麥子明天就能割了。晚上,父母往往一夜都不曾合眼,像過年一年,為明天開鐮作最后的準備。父親把草要子、鐮刀、小推車都一一擺好,看了一遍又一遍,母親把積攢了一年的咸鴨蛋、臘肉也都拿了出來,煮熟、煎好。第二天早上,星星還掛在天上,母親就喊我們起床了,我們也都興奮得不得了,好像大年初一要出去拜年一樣,每人都精心“裝扮”一番:為了防止麥芒對身體的傷害小一些,每人穿了件薄薄的長袖衣服;一人一頂草帽,準備與正午毒辣辣的太陽戰斗到底;扯一根草繩,把一把草要子系在腰上;每人挑一把明晃晃的鐮刀,拿在手里掂量一下,看看是不是合手,父親則要把大拇指放在鐮刀刃上輕輕劃試,聽聽是否有輕輕的脆響,他總是選幾把刃開得好的鐮刀,給我們姐弟幾個使用。
到了地頭,那晶瑩的露珠還掛在麥葉上,麥稈和麥穗都柔軟一些,不很扎人,這是一天中割麥子的最好的時間。一人一畦,割麥子了。先抽一根系在腰間的草要子鋪在地上,右手持鐮刀,左手抓麥稈,左邊一鐮,右邊一鐮,割下的麥子在左手呈扇面著,一就是小半個麥個子,手里滿了,就放在草要子上面,差不多上兩三,就夠一個麥個子了,左手攥一把麥稈連同草要子的一頭,右手攥著草要子的另一頭,左膝蓋壓在麥稈上,兩手一交叉,把草要子勒緊,打個十字花結,一個麥個子就捆好了。幾個姐姐很是內行,雖然手里勁不大,但麥個子捆得結結實實,任其裝車卸車都散不了。我卻摸不著門道,不僅工夫費得多,還捆得稀松,裝車時,往往一提草要子,麥子就散落一地。
日頭越來越高,毒辣辣的太陽鉚足了勁,像要在這幾天里,把全部的能量釋放出來一樣,讓大家在麥田里沒處躲沒處藏,只能“享受”老天賜予的溫暖。看著快要歸倉的麥子,每個人都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大家心里明白,老天爺不長眼,天說變就變,就是不下雨,來一陣風,一年的希望就可能化為泡影。這毒辣辣的太陽是大家盼來的,割麥子就是找熱受,就是要和老天爺賽跑。麥地里,那麥芒也在炙熱的太陽背后狐假虎威,越來越尖銳,稍不留神,一根根頭帶倒鉤的麥芒就把胳膊、腿甚至臉部劃出一道道血印,那帶著鹽漬的汗水流淌在血印上,麻沙沙地痛癢。上面烈日烤,下面麥芒扎不說,那腰疼更是讓人受不了,割上十幾米,腰疼得就成了兩截,上身直不起來,腿也不聽使喚,整個人就像癱瘓了一樣……望著前面金黃的麥穗,那是全家人一年的希望,大家誰也不愿在這時候敗下陣來,彎著腰,揮著鐮,堅持著,一撮一撮地把麥子割下來。
好不容易到了地頭,咕咚咕咚喝上幾碗綠豆湯,就著母親昨天晚上才煎出來的臘肉,吃一根成年累月企盼著的油條,疲勞一下子就消了一半。摘下草帽,一邊用帽檐扇著風,一邊望著麥地里一個個麥個子,真不敢相信自己有了這么多的勞動果實,心中頓時升騰起澀澀的甜意。看著那一粒粒飽滿的麥穗,仿佛已變成了朝思暮想的、已經入口的白面饅頭,甜滋滋的麥香從嗓子眼兒慢慢地流到了心里,滋潤著全身……
多少年過去了,這股甜滋滋的味道還常常在心里流淌著。是啊,回首望,這塊給了我甜澀感覺的土地,不正是全家美好生活的起點嗎?這股甜滋滋的味道不也是全家從貧困走向小康的心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