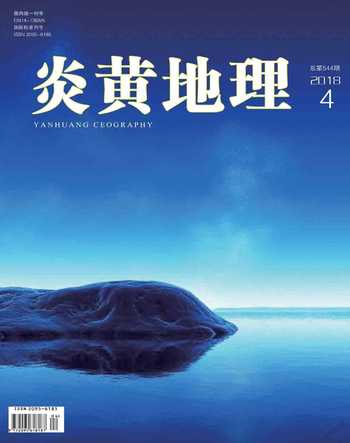日記體《東京一年》——異文化視閾的反思
摘 要: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之邀,蔣方舟開始了有生以來第一次在異國他鄉完全真空的生活。她用日記的形式將凝固一瞬的孤獨與風景在時空中進行擴展,保留了具有自我風格的絮叨囈語與對時事的針砭時弊。本文從主題出發,闡釋這位身為新新人類的作家處于異國文化的迷惘與思考。
關鍵詞:《東京一年》;日記體;文化審視;國民性批判
一
中國“五四”時期日記體小說開始興盛,源于西方日記體小說的影響,現代作家的日記體小說推動了20世紀30年代的日記體小說寫作進行微觀考察,試圖勾連起日記體小說的現代發展。蔣方舟的《東京一年》以日記形式書寫,共記46則,收錄其最新短篇小說、時評與演講,駁雜而不失純粹,從社會、藝術等領域到當今中日兩國的民間百態,都有其獨特又不失嚴肅的描摹與思考。同時,這也是一本診斷當代國人的病例,記錄著屬于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迷惘與掙扎,如同書中所說“就像在東京度過的一年并沒有把我變成一個新人,我們只是更像自己本來該成為的樣子。”本書將相片與文字結合,邀請日本紀錄片導演伊滕王樹一路旅拍,展現鏡頭下最真實的作者在東京的生活日常。
日記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體,“私語言說”是其存在的理由,而這一理由同語言的交流功能相悖,決定日記文體的解構與蛻變的可能,出現各種假借或仿擬日記的文體。縱觀日記發展的歷史,在種種日記變體中。日記文體的“私語言說”已經蛻變為“形式的誘惑”,特別是日記體為代表的日記文學。蔣方舟的《東京一年》以日記體形式記錄自己在一年期間游走于“大和文明”的寶地所見所聞,卻又不局限于自我情感的無克制宣泄,以精英視角對照中日兩國的文化差異。蔣方舟作為主流文學的青年作家同樣關注社會熱點問題。深刻揭示社會矛盾。通過日記體小說這種文體的轉換與功能的嚴謹,顯示其理性意識的增強。
二
《東京一年》不能被定義為一本的游記,因為它僅是將地理坐標顯示于生活中的日常。作者在這些清寂的日子里四處拜訪新朋與故交,在與之交談的過程中產生自我與他者“思想與文化”的碰撞。除去描寫“脫衣舞娘”熱舞的畫面略顯俏皮之外,整部作品的格調深沉且克制。我對于這種精英視角的審視向來是不太熱衷的,但又被作者所關注的議題所吸引。蔣方舟在“2016.2.18”中寫到“在缺乏宗教的社會里,過剩的中產需要跑步這種宗教般的歡愉來緩解自己的焦慮和壓力。”不得不說,近幾年跑步已成為中國中產階級的新宗教。我曾連續幾日在廣州塔附近的珠江邊游蕩,除了驚嘆于廣州精美的吃食外,大概還有江邊那些如機械一般的跑步者。他們的運動裝備比他們的跑步姿勢更顯專業,在被霓虹包裹的夜色中毫無表情的奔跑著,耳機里播放的音樂將他們與這個呈現虛假滯態的世界相隔絕。或許在如今日新月異的社會中,強身健體并非是跑步的唯一目的,因為誰也無法講明我們在奔跑的過程中,到底將它視為一種自我磨練還是一種逃避,就好像是那些在江邊的跑步者一樣,他們中有多少是為了擺脫工作應酬所帶來的壓力,亦或是想要遠離家庭的瑣碎與紛擾。關上房門,換上跑鞋,試圖讓那些糟心之事在汗水中得到溶解,這種自律與強大的背后或許只是一個脆弱柔軟且畏懼回家的人。但蔣方舟并未過多的感懷于中產階級的“高壓”處境,而是筆鋒一轉將視點聚焦于“中產階級”這一群體,他們傲嬌且嚴謹,沉浸于自我小群體的階級認同。在跑步與廣場舞構成的運動鄙視鏈中,將群體廣場舞視為鄙視鏈的最末端,從而把跑步看作是中產階級自我意識的覺醒。蔣方舟還是未放下她知識分子式的情懷,寫道“很多中產并不認為自己有推動社會變革的責任,而僅僅是想通過長跑和秋葵把自己修煉得百毒不侵,水木清明。”筆者不能確定這是否是她對中產階級的犬儒與自私的一種審視,但可以看出蔣方舟在《東京一年》中的蛻變,拋卻少女的情思,在旅途中找尋自我,反思文化的共性與差異,也許風和日麗、歲月靜好并非是她在日本旅居生活的全部意義,那顆年輕而敏感的心在異鄉的孤獨中卻更能接近生活的本質。
三
人是一種視覺動物,科學研究證明因視覺沖擊與情感體驗的相互影響作用,導致男性對于美麗女性的向往與憧憬。翻閱《東京一年》時,其中斑斕的相片總比黑色的文字更吸引受眾。其中有一張蔣方舟的側顏照,上面略帶調侃的寫著“我最不喜歡拍照時被攝影師指揮:露出沉思的表情。一是因為被強迫沉思,實在想不出什么來;二是因為我喜歡嘲笑知識分子的裝腔作勢。結果被抓拍時,還是露出了憂國憂民的表情。”結合時事分析,影視受眾在《圓桌派:自由女神婚不婚?》這期節目播出后,將蔣方舟與徐靜蕾相對比,有公眾號甚至打出“為什么42歲的徐靜蕾被捧上天,28歲的蔣方舟卻被貶成渣?”這類并不怎么高明的標題。身為女性,我同樣被老徐在談話中具有邏輯與深度的言論所折服,那是一種成熟女性才能展現出的個人魅力,也是一種充滿智慧的生活態度。反觀蔣方舟的言談自然不難看出她的迷惘與青澀,在談話中她搬出高舉“女性主義”旗幟的波伏娃奶奶,還引用了蕭伯納爺爺的婚戀觀,同時自嘲自己是在婚戀市場中被挑選的“大齡饑渴女青年”。激進的看客看到這里開始產生不適,并斥責她是帶著“高知帽子的EQ低能兒”。但人在生活閱歷與感悟處于匱乏的狀態時,大眾分析與評論一件事物往往都會引經據典,試圖從前輩那里習得最直接的經驗去解釋當下的人生,這是多數年輕人所共同擁有的特性。在這個世界上,眾人皆是微弱的存在,但每個人依然擁有表達自我困惑的權利,蔣方舟同樣如此,即便持有“才女人設”的她,也不可能用全知全能的視角去審視人生中的所有是非,我們都在成長,宇宙絕無先知。
王小波散文中記錄其二十一歲是一生中的黃金時代,他想愛,想吃,想變成天空中半明半暗的云,但他又接著寫到“后來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一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或許生活的本質就是如此,年輕的張狂會伴隨著歲月褪去,所有的光鮮亮麗都敵不過現實的打磨,蔣方舟在“三十而立”之年已經不再去想與這個有些荒唐的世界決裂,但也從未打算與它握手言和。
參考文獻
[1] 蔣方舟.東京一年[M].中信出版社,2017.
[2]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3] 戴維 洛奇.小說的藝術[M].作家出版社,1998.
[4]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M].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
[5] 韋勒克 沃倫.文學理論[M].三聯出版社.1984。
作者簡介:
王文林(1993-),女,山東濟南人,聊城大學文學院2016級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語言與文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