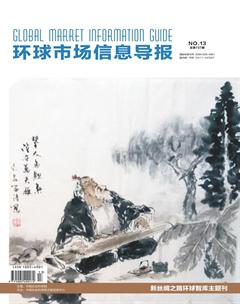鄉村生活的本色冉現與重鑄
甘浩
在現代文學中,鄉村民間敘事存在著兩種典型的寫作,一是“丑化”敘事。這一類敘事大都出現在現代知識分子的啟蒙筆鋒下。“丑化與20世紀西方文化價值取向密切相關,通過對鄉村諸種丑行的揭露、批判,鄉村人物就成為鄉村文化、社會的典型載體,成為民族傳統的歷史寓言。于是,對丑的審視,便潛隱勾勒出一條否定之否定的民族救亡路線以及與此相關的文化敘事策略。”二是詩化敘事。
這類敘事又有多個層面,常見的有兩類,第一類是沈從文式的,鄉村是作家夢魂縈繞的精神家園。他們進入鄉村敘事時,大都站在虛遠的立場對鄉村生活和鄉村人物進行精神關照,其情感基點是眷戀、留連、懷念。這種敘事的文化立場仍然是典型的知識分子立場;第二類是革命敘事。這種敘事對鄉村政治的改天換地和鄉村生活的改顏換貌有一種革命浪漫主義情懷,由于作家對鄉村生活的改顏換貌有超前的理想性,這種超前性寫作是以革命理想主義為內質的,所以革命敘事對鄉村的詩化不可避免。需要注意的是,對鄉村民間無論是丑化敘事,還是詩化敘事,都沒有正視鄉村的現實和真正把住鄉村的脈搏。在這些敘事觀照下,鄉村民間被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視作任由他們開墾的蠻荒之地,鄉村的真實和鄉村的價值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表現與尊重。
趙樹理的民間敘事也是一種典型的革命敘事,但是這種革命敘事與上述兩種關于民間的寫作有明顯的不同。差異就表現在趙樹理的民間敘事恰恰真實地表現了鄉村生活,對民間生活表現了起碼的尊重,恰切地說,尊重民間和正視現實是趙樹理民間敘事的基本的文化立場與價值觀念。在此基礎上,他試圖改造鄉村禮俗社會,使之進入國家意識形態和現代知識分子所要求的現代化軌道。
根據民間的道德倫理、生存邏輯去理解民間是趙樹理介入鄉村民間的一個基本寫作策略。建國后趙樹理有很多關于創作的談話或文章,其中一個反復提到的觀點就是“作者必須參加到社會實踐中去”。熟悉農村生活與鄉村人物是趙樹理寫作的一大優勢。他曾經自得地說:“當他們一個人剛要開口說話,我大體上能推測出他要說什么——有時候和他們開玩笑,能預先替他說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話。”
由于非常熟悉農村生活和鄉村人物,他的鄉村敘事自然樸實,事件的發展和人物的情感完全符合鄉村的倫理道德和生存邏輯。如《李家莊的變遷》中鐵鎖對革命者小常的接受同樣是從農民樸素的道德意識出發的:“凡是他見過的念過書的人,對自己這種草木之人,總是跟掌柜對伙計一樣,一說話就是教訓,好的方面是夸獎,壞的方面是責備,從沒有見過人家把自己也算成朋友。小常是第一個把自己當成朋友的人。”“他自從碰上小常,四五年來一天也沒有忘記,永遠以為小常是天下第一個好人”。鐵鎖對小常是“好人”的道德認同發展到后來的革命認同,放在特定的鄉村文化環境中就顯得自自然然。與趙樹理相比,同樣是寫農民對革命者的接受,梁斌明顯有“生硬進入”的痕跡,《紅旗譜》中朱老忠接受革命者賈湘農是通過嚴運濤,在聽過運濤講述的賈湘農的工農理論后,他就興奮地告訴運濤他找到了窮苦人的“靠山”。兩位作家有這種區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們關于民間的價值觀念的差異,而在于對民間生活了解程度的差異。膚淺地了解民間生活與鄉村人物的作家,便很容易像梁斌一樣不是從事物的事理邏輯出發寫作,而是生硬的“套”用現存的理念。十七年文學正是在這一點上呈現出“理念”寫作的傾向,現在看來,趙樹理的價值之一,就是他創作中遵循的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客觀上顯示了對抗了這種“理念”寫作的事實。
當然,這種嚴肅的現實主義寫作態度在十七年時期日益“左”傾的寫作語境中是步履維艱的。趙樹理建國后的小說產量明顯下降。孫犁說,趙樹理解放后的創作“遲緩了,拘束了,嚴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當年青春潑辣的力量”,這個見解是學界的共識。人們在責備趙樹理時,不應該忽視趙樹理日益艱難的創作環境。趙樹理進入新中國的身份,是“解放區文學的方向”,解放區文學在建國后的文化地位,使趙樹理的文化身份不可能是一個單純的作家。權力意識形態也給他施加壓力,《登記》發表后,趙樹理被調入中宣部“入部讀書”,“胡喬木同志批評我寫的東西不大(沒有接觸重大題材)、不深,寫不出振奮人心的作品來”。在這種環境下寫出來的《三里灣》仍然受到了批評,主要涉及到在寫“兩條道路”斗爭時沒有附和主流——張揚農村中尖銳的階級斗爭;作品對三對青年的愛情描寫被諷刺為“沒有愛情的愛情描寫”。趙樹理對后者的申辯,就可以見出趙樹理創作理念與當時流行理念的沖突:“向你們所說的這種‘沒有愛情的愛情描寫,目的是想看到‘有愛情的愛情描寫。這種寫法,目前我還寫不了。”原因是農村盡管解放多年了,但在戀愛婚姻上還不能像城市那么開放,而且,農村青年當時根本沒有時間沒有條件像城市青年一樣擁有花前月下的愛情。
當然,切近生活本色并不意味著小說創作的成功,這是一個常識,否則人們大可不必去創作小說而寫報告文學好了。就現實主義小說來看,是否塑造出鮮活的人物形象將決定小說的審美層次。趙樹理小說歷來受人稱道的一個方面,就是其筆下出現了一批富含鄉土意蘊的農民群像。早就有人指出,趙樹理的作品“像風俗畫,多是日常人情世俗的描寫,鄉土味十足,調子輕松愉快”。這種風俗性的黃修己:《趙樹理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第149頁。
內容在人物形象方面有明顯的展示,譬如,三仙姑的老來俏與裝神弄鬼,小諸葛的迂腐與陰陽八卦,李有才的幽默機智與膾炙人口的快板……他的大多數作品都有一個甚至多個讓人難忘的鄉土人物。鄉土人物與鄉村生活和鄉村文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他們身上顯示了極其濃郁的三晉文化神韻,從而使他的人物既具有典型性,又有個性。趙樹理的小說本來有強烈的政治功利性,但是由于他對鄉村人物既貼近民間文化又超越民間意識的描寫,使他的作品兼具了傳達民間訴求,表現主流意志和進行文化啟蒙的多種功能。小說多重的文化功能,也使站在不同立場上的人們對他的小說莫衷一是,這是人們至今難以對趙樹理的小說有一個明確的文學史定位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