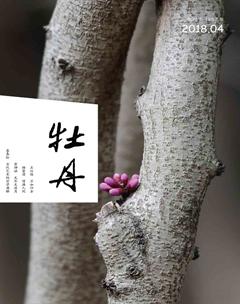論文學的經典化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構
馬驍騁
將現代文學經典化,將會對文學史的模式產生一定影響,對于現代文學史也會有一定影響。文學經典化將使得中國現代文學史重構,其廣度、深度、格局都會受到一定的沖擊,中國現代的文學史的影響力將會得到一定擴大。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與研究將和傳統文學史寫作產生不同,應該去粗取精,由復雜變簡單,將中國文學史經典化。因此,本文簡要介紹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并對文學的經典化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構進行了討論。
經典的文學作品是指作品中要包含有一定的人生哲學又要具有一定的藝術可觀賞性,經典的文學作品應該是能夠經得起推敲的,可以傳承下去的,供一代一代人閱讀和學習的。有的經典文學作品具有批判價值,可供閱讀者領悟文中諷刺的內容,有的經典作品具有民族史詩感,可供后代學習領悟,有的經典文學文字優美,具有美學意義,同時經典作品一定具有原創性。經典文學就像細胞的碳骨架一般是組成文學史的骨架,是我國文學瑰寶中
的龍骨。
一、中國現代文學史
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與研究顛覆了傳統的寫作模式,融入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度、格局、影響力。中國現代文學經歷了三十年,第一個十年是1917年到1927年,文學革命進程經歷了維新運動的詩界革命、小說革命、文界革命;晚清以裘延梁為代表人物的革命;清末民初的翻譯小說盛行。辛亥革命后,民生發展、社會比較安定,文學革命以新知識者群體為代表。1915年9月新文化運動開始,以陳獨秀、易柏莎、李大釗、吳虞等為代表,他們寫文章批孔、反孔,認為其思想易演變成獨夫專治;1917年2月文學革命以陳獨秀為代表,提出三大主義作為目標;1919年五四運動,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周作人、魯迅等為代表,五四運動納入新文化運動最有力的組成部門。
第二個十年是指1928年到1937年6月,1928年1月,《太陽》《文化批判》等月刊創辦,這和《新月》月刊的自由主義作家對立。文學隨社會變革而政治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獲得傳播,多種傾向文學彼此競爭。1929年下半年,引進日本左派文學理論,以太陽社為代表,主張新寫實主義,看重客觀的真實性,表現出革命的理想主義氣度,使許多作家都錯誤地以為不能再寫自我的情感心理,只能寫群像,公式化、概代化弊病普遍。1931年11月左聯執委會決議,以文藝大眾化研究會為代表,這一事件引起廣泛的討論,對于促進文學的現代化與民族化發展有重要意義。1933年11月,論文《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橫空出世,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無產階級文學的一種基本創造方法,旨在清算“拉普”機械論的文學思想以及“唯物辯證法創作方法”的編誤,但因作者對此理論的認識不夠深入造成事
與愿違。
這一時期,左翼作家以矛盾、丁玲、蕭紅等為代表,京派作者以葉圣陶、王統照、林徽因、朱光潛、沈從文、楊振聲等為代表,海派作家以張資平、曾虛白、黑嬰等為代表。通俗小說中,北派言情小說企圖將章回體調整為一種新舊問題都適宜的文體,其中以張恨水、劉云若為代表,代表作有《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等。南派小說進入低谷期,代表作品為《紅羊豪俠傳》《神秘的上海》等。北派武俠小說較遠離現實,對民間社會的武俠觀在書中加以表現,內容沉醉于超現實世界,代表人物是顧明道、還珠樓主白羽等,代表作有《荒江女俠》《青城十九俠》等。新詩代表有徐志摩、何其芳等,散文分為自由主義作家、京派、左翼作家、開明派、報告文學與游記。戲劇因為大革命失敗后大量追求革命的知識分子被實際斗爭擊潰,這些人希望在文藝中寄托自己的苦悶,所以戲劇作品層出,如《梅雨》《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打出幽靈塔》《走私》等。第二個十年的主要影響人物有矛盾、老舍、巴金、沈從文、魯迅、
曹禺等。
第三個十年是1937年七月到1949年9月,這個時期的問題中心主要是民族形式,關于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生活的關系,關于現實主義的“主觀”的論證。此時期具有影響力的作家主要是趙樹理和艾青。
二、文學的經典化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構
當代中國文學的經典問題不是一個新命題。長期以來,“文學經典”一直是評論家在當代作家作品的經典取向和當代文學史研究兩個層面上的熱門話題。命題本身具有豐富而復雜的內涵與外延,是歷史與文學的交叉融合,因此不斷推陳出新。首先,在歷史河流的發展變化中,“文學經典”不僅是自然進步的歷史過程,也是相對獨立的生存空間。人們沒有必要將其定義一個單一的標準尺度,或者擴大沒有邊界的范圍。嚴格地說,“文學經典化”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古典文學作品”的延伸。
第一個十年之中,魯迅的作品具有獨特的題材、眼光與小說模式,他被稱為創造新式的先鋒。魯迅創作了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狂人日記》“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它以“‘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的確,《狂人日記》在近代中國的文學歷史上,是一座里程碑,開創了中國新文學的革命現實主義傳統。魯迅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散文詩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華蓋集》等十六部,并著有《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等,為我國現代文學史留下了燦爛的文學瑰寶。因此,魯迅被稱為文化
的戰士。
郭沫若也是第一個十年的文學名家,他在現代文學史上是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詩人與歷史劇作家。郭沫若的詩集《女神》成功把時代需要和詩人創造個性融合,在其作品中,人們既可以讀到自我抒情的主人翁形象,也可以感受其充滿想象力的藝術特征。郭沫若的詩歌散文戲曲集主要有《星空》,詩集有《女神》《恢復》《前茅》《瓶》等。從本質上講,中國古典文學的問題不在于討論當代文學是否古典,也不在于衡量當代文學經典的標準和原則。筆者認為,今天討論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原因,應該是不斷質疑和反思偉大的歷史眼光和新的歷史觀念。
今天討論當代文學經典,不僅是為了確定一個具體作家的作品的文學價值,而且是一個文學存在和表達的歷史記錄。21世紀以來,多元的當代文學大廈是對當代人精神和靈魂的深刻挖掘和表達,隨著全球化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文化視域不斷發生變化,新的網絡媒體和區域空間整合已經形成,文學已經從內到外發生了變量。無論是網絡文學的出現,還是當代小說傳統文體意識的巨大挑戰與突破,抑或是非小說、新筆記、寓言等多種類型的跨文體創作的成功范例,都為當代文學注入了生命力。在經典化方面,當代文學的成就可以說明文學經典的存在具有獨特的時代標準,同時這些標準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演變。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其經典過程的歷史研究實際上是對當代文學從靜態到動態的歷史考察與思考。這本身就是對當代文學批評的文學批評,它以印象和感知為中心,轉向尋找差異,發現問題,思考真相。這也是學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問題充滿熱情的原因。文學經典的討論不是針對具體作家的作品或某些文學現象的經典,而是從文學史觀角度對當代文學進行審視和分析。例如,人們談論西方文學和西方重要作家的作品,地區文學和作家顯然沒有必要討論。但是,獨特的作家和作品所浸潤和滋養的特殊地域文化資源,是豐富中國當代文藝寶庫的重
要基礎。
“經典”的歷史視角和新的歷史觀念對文學史寫作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一帶一路”的文化背景下,拓展文學經典和深層思考與當代文學結合的誠信問題,探索當代文學資源也是當代文學不斷“經典”的過程。對于作家和文學現象的微觀具體作品的“經典”認識,人們需要實現對“文學經典”問題的文學史和觀念的宏觀理解。一方面,要超越單純的價值判斷和標簽確定,進一步引出對深層歷史原因和文化內涵的合理公正揭示;另一方面,“文學經典”的思想也應該關注當代文學。
三、結語
文學評論家和學者在從當代文學批評向現當代文學史研究轉變的過程中,認為經典作家的作品基本上是通過對理性沉思的感性敏銳觀察,最終擁抱現實與虛構,構建擁有真誠和良知的藝術世界,有批判性地檢查現實和復雜創作形態的多重影響。因此,對當代文學經典的討論既是對文學史研究的一個過程,也是對作家、文學評論家和研究者的文學觀念的批判性反思,它決定了“過程”,應該是最高原則和底線。
(湖北天凱風林電子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