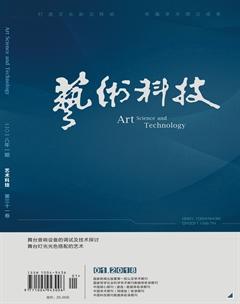對“展場”的再認識
陳瑋文
摘 要: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從建筑物的意義上理解“展場”,把“展場”與藝術作品機械地割裂開來,認為“展場”與作品的關系,就是容器與物品的關系。筆者認為這種觀念違背了藝術發展的大眾化趨勢,是片面的、不科學的。因此,我們有必要用發展的眼光和動態的思維,從“展場”的歷史演變、基本特征和現實意義等多維度對“展場”予以重新審視。本文概括了“展場”演變的4個歷史時期,即“珍奇屋”時期、“白立方”時期、“替代性空間”時期和“多樣化空間”時期,凝練出“展場”的3個基本特征,即包容性、延展性和可塑性,論述了“展場”的現實意義,認為“展場”是藝術作品的載體,是虛擬與現實相互連接的紐帶,是觀眾與作品交流互動的平臺,是藝術作品的組成部分。
關鍵詞:展場;演變;特征;意義
“展場”是藝術實踐中一個被廣泛使用而且非常重要的概念,無論是藝術創作,還是藝術展示,都離不開“展場”,策展人、藝術家和觀眾無時無刻不在與“展場”發生某種聯系和互動。那么,何謂“展場”?《辭海》和《新華字典》中均沒有答案。從筆者查閱有關“展場”的資料來看,絕大多數人把“展場”定義為“藝術展示的空間”或“展示作品的特定場所”。這種定義,從傳統的觀念上講,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從當代藝術的發展來看,卻是片面的、不科學的。傳統的“展場”觀念,受歷史的局限和技術的制約,以特定的場所為本體,從建筑物的意義上考察“展場”與藝術作品的關系,把“展場”和藝術作品看成兩種相互獨立的語境,認為“展場”的功能就是展示藝術作品。但當代藝術的發展,特別是新媒體藝術的發展,對這種傳統觀念發起了挑戰,使“展場”與藝術作品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實踐證明,“展場”已經成為藝術作品的有機組成部分,“展場”與藝術作品已經融為一體。因此,我們有必要從“展場”的歷史演變、“展場”的基本特征和“展場”的現實意義3個方面,以藝術作品為本體,從藝術空間延展的意義上對“展場”予以重新審視。
1 “展場”的歷史演變
“展場”的歷史演變大概經歷了4個時期:“珍奇屋”時期、“白立方”時期、“替代性空間”時期和“多樣化空間”時期。
1.1 “珍奇屋”時期
早在17世紀,歐洲一些國家的王公貴族和特權階層對稀有物件如油畫、雕塑和掛毯等,具有特別的喜好,他們在宮殿或城堡中營造專門的空間,用以收藏這些稀有物件。這種用于收藏稀有物件的專門空間被人們稱為“珍奇屋”(Cabinets of Curiosities)。這就是“展場”的雛形,也是“展場”觀念的發端。
1.2 “白立方”時期
從18世紀開始,“展場”進入“白立方”時期。這個時期的“展場”以博物館為主要形式,如巴黎的盧浮宮、倫敦的大英博物館、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維也納的藝術史博物館等。博物館空間采用潔白的墻面、拋光的木質地板、隱藏的電線,以營造神秘、神圣、獨立、隔絕的氛圍。這個時期的“展場”——博物館是國家意志的象征,是主流文化的象征,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絕對的權威性。
1.3 “替代性空間”時期
20世紀初,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受現代主義的影響,歐美國家一批激進的藝術家不滿傳統的博物館體制,開始反抗傳統藝術機構的絕對權力,尋求新的展示空間。他們利用廢棄的廠房、車間或建筑物,甚至私人住宅來展示自己的作品。杜尚1935年至1941年間創作的《行李箱的盒子》,用一個手提箱裝滿了24件微型作品,第一次走出與世隔絕的潔白空間,深入喧鬧的城市中進行展示。之后,波普藝術、貧窮藝術、環境藝術、裝置藝術(InstallatiOn)、身體藝術(BodV art)、地景藝術(Earthwork)或稱大地藝術(Land Art)應運而生。“替代性空間”的出現標志著“展場”開始脫離畫廊——機構語境的束縛,從室內走向室外,從城市走向鄉村,從封閉走向開放。
1.4 “多樣化空間”時期
20世紀末,特別是21世紀以來,受后現代主義、消費主義和互聯網思維的影響,藝術進入大眾化時期,“展場”的外延進一步拓展,并向多樣化空間發展。在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社會雕塑”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許多藝術家完全擺脫固定的建筑空間,將藝術品呈現在廣闊的地理空間中——山巒、湖泊、大海、街道、公園、廣場、商場和交通工具等場所。這個時期的“展場”雖然仍以博物館、藝術館、展覽館為主流,但大量非主流的、民間的“展場”逐漸形成,并越來越受到藝術家和觀眾的青睞,正如藝術家阿德里安·派珀(Adrian Piper)所聲明的那樣:“對我而言,畫廊、博物館、表演中心這樣的一些藝術場地,已越來越沒有可用之處……我一直在運用各類非主流場所展示我的作品:如地鐵、公共汽車、梅西百貨、聯合廣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1]這個時期,“地球村”的預言已經變成現實,世界藝術的中心不再是歐洲或美國,而是全世界。世界各國的藝術融為一體,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對藝術本質、評價標準、社會意義等的認知和理解逐步趨同。特別是隨著數碼技術、互聯網技術和多媒體技術的發展,影像裝置藝術、多媒體藝術、網絡藝術、虛擬現實藝術等新型藝術形式脫穎而出。與此同時,“虛擬展場”迅速崛起,成為創作、展示和體驗藝術作品的重要場所。
我們從展覽空間的演進過程不難看出,“展場”一詞不僅是對藝術博物館及其各類展覽的闡釋,更是順應當代藝術創作與展示形式發展需要的產物。因此,“展場”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征,我們對“展場”的認識必須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的發展緊密結合起來。
2 “展場”的基本特征
為了全面、準確地把握“展場”的內涵,我們僅對“展場”的變遷過程進行考察是遠遠不夠的,還有必要透過“展場”發展的歷史,對不同時期“展場”的共性進行分析,從而凝練出“展場”的基本特征。
2.1“展場”的包容性
就“展場”的建筑物意義而言,無論是“珍奇屋”,還是“白立方空間”,抑或“替代性空間”,就像一個容器,裝載著各個時代、各種形式的藝術品,包容它可以承受范圍之內的所有媒介,如聲音、光線、色彩、氣味、物質、精神等,這些媒介讓“展場”變得豐富多彩,充滿活力,正如挪威建筑理論家克里斯蒂安·諾伯格-舒爾茲所說:“我們所指的是由具有物質的本質、形態、質感及顏色的具體物所組成的一個整體。這些物的綜合決定了一種環境的特性,以及場所的本質。”[2]隨著“展場”的演進,多元化空間逐漸消解了“展場”的建筑物意義,使“展場”的包容功能更加強大,幾乎能夠容納現實空間和虛擬空間中的所有元素。正是因為“展場”的包容性,才激發了許多藝術家創作的靈感和激情,才使得許多經典的藝術作品得以保存,才使得眾多觀眾能夠欣賞作品,參與創造,陶冶情操。
2.2 “展場”的延展性
我們如果僅從建筑物意義上去理解“展場”,就會只看到有限的空間,就會嚴重制約藝術活動的開展。其實,廣義的“展場”可以打破國界,延伸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展場”不僅可以從現實空間上延展,還能從虛擬空間上延展,更能從思想空間上延展。“展場”在虛擬空間上延展就是把展場虛擬化,在網絡空間展示作品;“展場”在思想空間上延展就是展場的氛圍和作品的感染力能帶領觀眾進入自由想象的精神世界,并參與創作。
2.3 “展場”的可塑性
從“展場”的歷史演變就可以看出,“展場”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可以塑造的。“展場”從權貴走向大眾、從封閉走向開放,就是“展場”可塑性的具體體現。不僅如此,藝術家和策展人還可以根據他們的作品和想表達的思想內涵及社會意義,將“展場”塑造成創作者需要的語境和范式,通過解構重組、破壞、拼接、消融、重置位移等等,來激發“展場”空間的未知潛能,發揮它的最大功能。“展場”所具有的可塑性讓觀賞者甚至是策展者和藝術家不得不把“展場”作為首要的考慮因素之一,其次才是藝術作品,正如愛爾蘭藝術家布萊恩·奧多爾蒂所說:“我們已經到了這樣一個節點,首先看到的不是藝術而是空間。進入腦海中的是一個白色的、理想化的空間,而不是任何一張獨特的圖像。”[3]德國達達主義領袖之一庫爾特·施維特斯在1923年至1936年間,在自己雙親位于漢諾威郊區的家中利用收集而來的廢棄物品拼接搭建了一整個嶙峋古怪的白色空間《情色與苦難的大教堂》,他將空間展場解構并重組,將空間變成了藝術作品語境的一部分,將展場與作品的結構融為一體,第一次模糊了“藝術作品”與“空間”的界限。
3 “展場”的現實意義
“展場”因藝術需求而出現,反過來又促進藝術的發展。“展場”從誕生之日起就將藝術納入自己的懷抱,精心呵護著藝術的成長。藝術的進步和繁榮與“展場”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作為藝術的物化成果,藝術作品受“展場”的深刻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3.1 “展場”是藝術作品的載體
“展場”對于藝術作品來說尤其重要,因為藝術作品通常以“展場”為載體和依托,藝術作品不能脫離“展場”而單獨呈現,離開“展場”,藝術作品就變得毫無意義。一方面,“展場”就是特定的容器,承載著各個時代的藝術作品,沒有“展場”,藝術作品就無法傳承,更無法展現;另一方面,“展場”就是肥沃的土壤,“展場”中的空間因素包括燈光、音樂、色彩、容積和角度都是藝術作品表現效果的肥料,沒有“展場”空間的烘托,藝術作品就會黯然失色,枯燥而了無生機。有的藝術作品甚至直接利用了“展場”空間,如鬼才藝術家托尼·奧斯勒在利用“展場”方面有自己獨特的手法和方式。他利用燈光、暗箱和雕塑等不同的媒體創造出一個身臨其境的視覺體驗,“展場”中奇形怪狀的雕塑正好結合了投射在上面影像里怪異的面孔,讓那些虛擬的面容變得更加猙獰、古怪,也更加富有現實感,仿佛就像真的存在于現實生活中一樣,不禁讓觀眾直打哆嗦。
3.2 “展場”是虛擬與現實相互連接的紐帶
在當代藝術中,數碼技術被廣泛應用,影像裝置藝術和虛擬現實藝術發展迅猛,并已滲透到商業領域。這些新媒體藝術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廣泛使用虛擬技術,將虛擬影像與現實環境有機結合在一起。那么,這種結合是如何實現的呢?除了傳感技術的作用外,“展場”在這里起到了基礎性、關鍵性的作用。“展場”的包容性、可塑性和延展性,決定了“展場”具有將虛擬與現實連接起來的功能。許多優秀的藝術作品就是藝術家和策展人通過巧妙利用“展場”的特點,將虛擬和現實成功連接起來的。1989年,杰弗里·肖(Jeffrey Shaw)發表了《可讀的城市》(The Legible City),這件作品呈現在一個房間內,由1輛固定的自行車和3個環繞自行車的大屏幕構成。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虛擬的、運動的城市及街道影像就是通過房間這一特定的“展場”,與人及自行車等現實因素連接起來的,“房間”就成為人及自行車進入虛擬城市及街道的橋梁和紐帶。
3.3 “展場”是觀眾與作品交流互動的平臺
當代藝術改變了傳統藝術作品以單向的、視覺的方式向社會和觀眾傳達藝術信息的狀況,代之以雙向的,具有視覺、聽覺、觸覺、味覺等多感官體驗的互動模式,打破了生活與藝術的屏障,消除了藝術與大眾的界限,實現了觀眾與作品的交流互動。傳統的封閉式的“展場”隔絕了藝術作品與社會生活的聯系,使觀眾成為“旁觀者”,而現代的開放式的“展場”打破了藝術作品與社會生活的界限,使觀眾成為參與者。在這種藝術模式的轉變中,“展場”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具體地講,“展場”在這種藝術模式轉變中的作用就是搭建橋梁、構筑平臺。許多有影響力的藝術作品就是充分利用“展場”的橋梁與平臺作用來完成的。2014年6月,在首屆中國新疆國際藝術雙年展中,來自美國的藝術家丹·柯林斯的影像裝置藝術作品《海市蜃樓》成為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該作品就是通過利用“展場”內的環境及多種感應設備成功實現了觀眾與作品的有效互動。
3.4 “展場”是藝術作品的組成部分
如果說傳統的“展場”與藝術作品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即“展場”離不開藝術作品,否則就是普通的物理空間;藝術作品也離不開“展場”,否則只能成為深藏閨中無人識的普通物品。那么,當代“展場”則與藝術作品存在著融合發展的趨勢,“展場”成為藝術作品的組成部分,正如英國媒體藝術先鋒羅伊·阿斯科特(Roy Ascott)所說:“在藝術實踐中,融合主義可能會成為方法論的當務之急。融合主義,在試圖調和不同或相反的信念,匯集了不同的實體——物質的和非物質的——以及它們哲學、宗教、文化的習俗和代碼。融合的思想是關聯的和非線性的。”[4]美國藝術家米歇爾·阿舍就提倡一種“情境美學”的藝術,主張藝術品所處的場所是作品的主體,是獨一無二的組成部分。德國卡爾斯魯厄媒體藝術中心(德文為Zentrum für Kunst und Medientechnologie,或簡稱ZKM)的館藏作品《超越界面》(Beyond Pages)是由日本新媒體藝術家藤幡正樹(Masaki Fujihata)于1995年創作的影像裝置作品。在這件作品中,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完全融為一體,置身其中的人們很難分辨出哪些是真實物品、哪些是虛擬物品。
4 結語
“展場”的歷史演變過程表明,“展場”是一個發展的、動態的概念,具有強烈的時代烙印。“展場”具有包容性、延展性和可塑性3個基本特征。“展場”是藝術作品的載體,是虛擬與現實相互連接的紐帶,是觀眾與作品交流互動的平臺,是藝術作品的組成部分。因此,“展場”不僅僅是“藝術展示的空間”或“展示作品的特定場所”,也是藝術創作和藝術交流的舞臺,更是藝術文明的搖籃和藝術成果的孵化器。
參考文獻:
[1] Sandy Nairne(英).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issent,Thinking about Exhibitions[C]. 1996:387,392.
[2] 克里斯蒂安·諾伯格-舒爾茲(挪).場所精神——邁向建筑現象學[M].施植明,譯.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6.
[3] 布萊恩·奧多爾蒂(愛).白立方體內:畫廊空間的意識形態[J].藝術論壇,1976.
[4] 羅伊·阿斯科特(英),袁小瀠.未來就是現在——藝術,技術和意識[M].周凌,任愛凡,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314.
[5] 張浩,展場.藝術展示的空間模式[J].美與時代(上),2013.
[6] 陳建軍.西方當代藝術展覽的替代空間[J].文藝研究,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