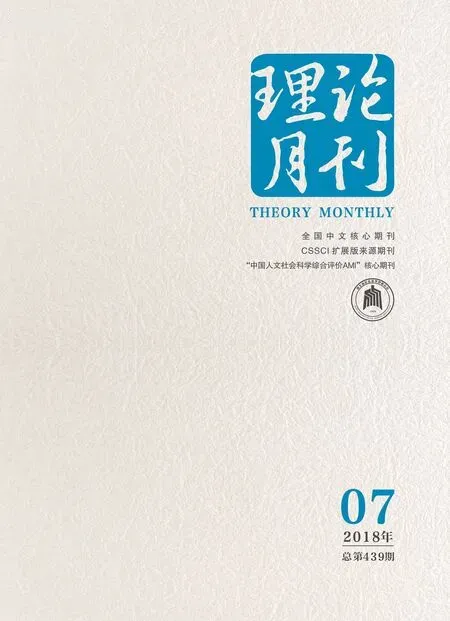行政案例指導制度之困局及其破解
——以最高法院公布的11個行政指導性案例為分析樣本
□李昌超,詹 亮
(1.西南政法大學 法學院,重慶 401120;2.重慶市梁平區人民法院,重慶 405200)
行政案例指導制度潛存諸多價值功能預期并突出“指導功能”核心界定,然則,囿于制度自身缺漏其功能實現并未達至預期,亦因此該項制度備受質疑。如此,本文即是以最高法院發布的13批11個行政案例為分析樣本,同時借以對其固定格式和基本內容的分析,凝練行政案例的“通識特質”,檢視行政案例之“制度短板”和“現實困境”,并借以對其“核心功能”的必然證成,提出對該項制度予以“實然重構”的可行且高效的路徑。
一、“運行現狀”:對行政指導性案例的定量定性分析
(一)行政指導性案例的數據統計與屬性分析
截至目前,最高法院發布了13批64個指導性案例①最高法院先后發布13批64個指導性案例,其中民事案例37個、刑事案例12個、行政案例11個、海事和國家賠償案例4個。,其中,行政案例11個,占17.20%,即涉及行政處罰的3件(第5號案、第6號案、第60號案)、行政征收的2件(第21號案、第41號案)、行政確認的1件(第40號案)、政府信息公開的1件(第26號案)、行政訴訟受案范圍與主體確認的4件(第22號案、第39號案、第38號案、第59號案)(見表1)。
(二)行政指導性案例的體例格式與通識特質
最高法院所公布11個行政案例的體例格式均基本呈現“七部分”相對固定組合(見表1),依次是編號和標題、關鍵詞、裁判要點、相關法條、基本案情、裁判結果、裁判理由”,其中“裁判要點、基本案情和裁判理由”被界定為指導性案例的核心要素,“裁判要點”作為“通過解釋和適用法律,對法律適用規則、裁判方法、司法理念等方面問題,作出創新性判斷及其解決方案”[1],則被界定為諸上組合要素的核心。
雖然行政指導性案例總體數量單薄,但是依然可以提煉歸納如下“通識特質”:(1)行政案例體例固定且相對統一。雖然最高法院將“關鍵詞”和“相關法條”在第38號、39號、40號、41號行政案例中予以刪除,但其后所發布行政案例的體例格式并未有實質變更,依然維持“八部分”的體例要素構成。(2)行政案例的類型多集中呈現。最高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多涉及行政處罰、行政征收、行政確認、政府信息公開及涉及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或者主體確認等“傳統型”行政行為。(3)行政案例“基層供給”比重較高。最高法院公布的行政案例中三個是經由一審判決生效并依照程序報送,即第5號案由江蘇蘇州市金閶區法院一審終審、第26號案由廣州越秀區法院一審終審、第41號案由浙江衢州市柯城區法院一審終審。(4)行政案例均經剪輯加工而非原文再現。經由最高法院所發布行政案例并非對原生效裁判文書內容的“簡單復制”,而均歷經“縮減—修正—剪輯—凝練”等加工過程,行政案例中不僅表征“立法技術”,亦滲透著“司法目的”。

表1:行政案例的格式及其內容情況
二、“現實困境”:對行政指導性案例的短板瑕疵厘定
行政案例指導制度雖承載諸多價值預期,但該項制度無論在制度設置抑或實踐操作層面均暴露諸多短板瑕疵,囿于此行政案例“指導效果”難以契合甚至游離于“功能預期”之外。如此,即須首先對面前的運行困境予以清晰厘定與審慎思考。
(一)案例數量困境:供給短缺消減整體效果
截至目前,最高法院共計發布11個行政案例。雖然不能因其數量孱弱而全然否定其“指導裁判”的制度價值,然則,在社會轉型與全面改革背景下,各級法院案件數量均呈現“爆炸式”增長,尤其是伴隨新類型案件的日益增多,案件審理難度亦不斷加大,如此數量的行政指導性案例對案件裁斷的“指導功能”確是微乎其微。如此,行政指導性案例因絕對數量“少”之限制而不能為行政審判提供具備整體意義的參照與指引。
1.行政案例與行政案件間“供需嚴重失衡”。根據最高法院年度工作報告統計:2011年至2015年,各級各地法院共審結一審行政訴訟案件121.1萬件,即2011年13.6萬件、2012年62.4萬件、2013年12.1萬件、2014年13.1萬件、2015年19.9萬件,但是最高法院同時段所公布行政案例僅11件,且案例類型過分集中呈現。
2.行政案例與行政法規范“總量差額巨大”。囿于統一行政法典的缺位,行政法規范雖制定諸如行政訴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等綜合性或專門的行政法律,并借以諸多行政法規及“紅頭文件”形式呈現,但其依然多散見于憲法、法律、地方性法規等法律規范當中。因此,其數量龐大、內容廣泛,且極具專業性、技術性和易變性,“不能結合具體的案件事實去闡釋某一法律規定的含義,它走的仍是‘從一般到一般’的道理,而‘從一般到個別’這條路子仍然是封閉的。”[2](p431)上述缺漏雖可借以公布行政案例予以填充,然則,因其“數量短缺”而未能清除甚或挪動障礙。
3.行政案例與民事等案例“比例整體失衡”。最高法院公布的11個行政案例所占比重僅為17.20%,雖較之于海事和國家賠償案例(共計4件,占比6.25%)具備明顯數量優勢,與刑事案例(共計12個,占比18.75%)的比重差別亦不大,但相較于民事案件(共計37件,占比57.80%)近60%的比重明顯不足。
(二)案例功能困境:指導不足壓縮存續空間
行政案例的功能期待即應恒定為“指導”,然則,縱觀目前發布的11個行政指導性案例,其所潛存或者明示的指導功能囿于“三種趨向”而未得以完全呈現,甚或漸趨消解:
1.“國家政策宣講”。諸如行政案例第21號案即僅系立足“現實需求”對“除非法律法規例外規定,經濟適用房須修建防空地下室,未修建的不能適用免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設費優惠”而作出“政策確認”,而非對現行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的創新與延伸①最高法院最近似乎對此有所認識,從而將明顯是在回應公眾關切的案例以“典型性案例”的形式在“月度案例發布”中披露,而不再作為指導性案例發布。。
2.“法律法規表征”。諸如行政案例第40號案旨在為“工傷認定中‘工作原因’和‘工作場所’的界定”提供指導,但其“裁判要旨”對“因工作原因”和“工作場所”的闡述,實際上即是對潛存《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條、第五條中“工傷認定須與工作職責具備關聯性,工作場所應予以合理區域延伸”的法律內涵的“具體外化”。
3.“必然結論推定”。諸如行政案例第6號案雖將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罰前告知當事人享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的規制范疇擴大到“沒收較大數額涉案財產”,但是該適用范圍的拓展實際上通過法律條文本身即可作出“必然推定”:行政處罰法第42條①《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的規定雖明確具體但卻并非有限列舉,“沒收較大數額涉案財產”具備拓展可能,同時根據“舉輕以明重”原則,既然處罰程度較輕的“較大數額罰款”被納入規制范疇,處罰程序相對較重的“沒收較大數額涉案財產”則當然應予以拓展確認。
(三)案例參照困境:剛性缺失導致適用自治
雖然最高法院借以司法規范性文件對行政案例作出“應當參照”的效力認證,但并未清晰厘定該系列案例效力的實現機制,如此,便導致法官關注行政指導性案例的程度較低,其對行政案例的適用亦是呈現“過分自治”:
1.對“應當參照”內涵的理解缺乏同一性,諸如有人認為“應當”和“參照”的語詞組合本即不相契合,“參照”僅限于某種程度的“比照”而非全然意義上的“依據”,如此,即便借以“應當”詮釋但依然未能賦予實質層面的“強制效力”;有人認為雖因諸如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的剛性效力缺失而允許不予參照的例外,但“應當參照”依然具備“較低”強制屬性;有人認為“應當就是必須,參照就是參考、遵照的意思”[3]。
2.對“應否援引”未能達成司法通識。司法裁判或者控訴一般僅將強制性規范作為行為依據,行政案例是否能夠界定為裁斷和控訴依據予以援引并未形成統一意見:法院系統普遍認為行政指導性案例系經由最高法院審委會討論通過,雖因立法基礎缺失而未被賦予法律強制效力,但“指導性案例具有事實上的拘束力,法官在處理同類或類似案件時,應當充分注意、參照指導性案例”[4](p12)。檢察院系統則認為囿于行政指導性案例并非具備普遍約束效力,對于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各級檢察機關可以作為法律文書說理的參考,但不能等同于法律條文或者司法解釋條文直接作為法律依據援引。
3.對“未予參照”的行為后果未予明確。行政案例指導制度的設置目的應歸結為借以“個案要旨”為類案提供“通識指導”而確保公正裁判,如此,即要求辦案法官在對類案作出裁判時應當借以行政案例呈現的諸項要素為參照并予以援引,若其“應當參照指導性案例而未參照的,必須有能夠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則,既不參照指導性案例又不說明理由,導致裁判與指導性案例大相徑庭,顯失司法公正的,就可能是一個不公正的判決,當事人有權利提出上訴、申訴。”[5](p85)然而,有人對此亦提出質疑:“由于法律對上訴和再審的程序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并沒有把這一理由作為再審的原因,所以在有關訴訟法律沒有進行相應修訂之前,還不能將未參照指導性案例作為進行上訴和再審的啟動原因”[6](p77)。
(四)案例監督困境:制度缺漏克減監督實效
目前最高法院對行政案例制度的運行監督主要呈現“內部自控”,對“外部滲透”式監督未予足夠重視:
1.行政案例的“合法性”未予審查。最高法院雖設置專門機構負責行政案例的遴選與審查工作,縱觀整個流程,其并未涉及對行政案例的“合法性”審查,其審查的內容主要圍繞行政案例的典型性、現實指導性、社會關注度、疑難復雜程度、法律依據充實程度、是否新類型案件及是否為生效裁判等實施。
2.行政案例適用的“民主性”未予呈現。囿于當前對行政案例“應當參照”非剛性效力的界定,法官在類案裁斷中對“能否適用或者應否適用行政案例”均享有絕對的控制權。易言之,行政指導性案例的參照適用并非依照當事人申請而啟動,而僅系憑借法官主觀判斷與選擇,即便是對行政相對人提請適用行政案例主張的回應亦是呈現純粹的“理由釋明”。
3.行政案例的“公開性”未達至充分。經由最高法院公布的行政案例均呈現對原判決裁定的高度凝練,如此,在對行政案例“基本案情”部分的剪輯和過濾過程中,部分重要案情表述欠缺明晰甚或被遺漏便不可避免。諸如行政指導性案例第6號案中被告金堂工商局比照《四川省行政處罰聽證程序暫行規定》對“較大數額的罰款”——“對非經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處以1000元以上,對經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處20 000元以上罰款”的標準,徑直將扣押三原告的33臺電腦主機界定為“沒收較大數額的財產”,但其并未對被告金堂工商局所扣押三原告33臺電腦主機的價格鑒定結論予以明示。同時行政案例公開內容的充實程度均相對孱弱,諸如生效法律文書和案卷資料等并未納入公開范圍,行政相對人之外的社會大眾甚或同一系統但分屬異區的司法工作者便因“信息傳輸介質”缺失而遭遇“案情盲區”,“那么‘裁判理由’論述得再嚴密也會顯得牽強附會,進而引發各種猜想,‘裁判要旨’再精辟、再符法意,也可能落得名不副實的評價。”[7](p52)
三、“突破路徑”:行政案例指導制度的證成及重塑
(一)“正當證成”:以指導功能為中心的多元價值呈現
行政案例潛存的諸多價值功能已然為其制度繁衍提供最強“佐證”。然而,囿于行政法規范剛性規制約束,行政指導性案例的“漏洞填補”功能并未得以足夠關注與挖掘,易言之,行政指導性案例的“指導性”即是對其“實際價值”的唯一界定:
1.對裁判規則的指導:法官借以行政案例為參照而對待審案件作出裁斷,其對行政案例的“參照適用”應當以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所凝練的裁判要點為直接依據,其應當與裁判要點所呈現的裁判規則相契合。
2.對類案認定的指導:法官對“類案性質”的辨識與界定不能僅憑“案情類似”而徑直作出,其應將“爭議焦點是否類似”作為最具核心價值的參照標準,易言之,若待審待判行政案件與指導案例間僅系案情相似或者相近,其訴訟爭點未能達至契合,則該行政案例不具現實指導性。
3.對裁判結果的指導:即便對行政指導性案例的參照對象不是案件的裁斷結果,而系案例所蘊含的精神實質[8],然則,法官一旦借以對“爭議焦點類似”“案情類似”等參照標準作出“類似案件”確認,及應當遵循“同案同判”既判力原則,作出與行政案例指導結果相一致的裁斷。
4.對文書制作的指導:囿于“規范化文書樣式仍未走出格式化的窠臼,只是取代了老八股文的新八股而已”[9](p123),如此,法官在制作裁判文書時應參照指導性案例的文書結構與語言表達,研析其思維方式與說理技巧,詳盡說明裁判理由、推理過程、批駁意見等關鍵環節內容。
(二)“制度重塑”:最大程度實現制度應然價值的現實選擇
1.補強案例數量:確保“供需均衡”。囿于行政指導性案例“供需失衡”的既定困境,當前首要的即是借以對行政案例數量的補強緩和案例供應與司法需求的“脫節態勢”。(1)案例“數量基準”:囿于行政案例公布程序較為簡潔且其與司法需求具備較高契合度,最高法院年度范圍內所公布行政案例的絕對數量應當等于甚或多于同期其所制定出臺的司法解釋及規范性文件。(2)案例“多樣渠道”:①案例層報機制。將基層法院作為基點,將本院所生成典型案例定期向中級法院報送,中級法院對報送案例進行嚴格審查和篩選并擇優報送高級法院,高級法院對推薦的典型案例進行全面審核并擇優遴選后統一報送最高法院討論決定。②案例培養機制。指導性案例的生成雖未能絕對排除“偶然因素”,但“主動挖掘和培養”卻系指導性案例高效運行之必然。如此,各級各地法院應當強化對本院抑或下級法院辦理案件的關注,對具備指導性案例備選價值的行政案例予以精心培育,從案件受理、開庭審判、文書制作、案例編寫等各個環節提供必要的跟蹤指導,待條件成熟時即可對其予以直接確認。③案例民意融通機制。行政指導性案例的選定雖然呈現最高法院的“絕對主導”,但此并非意味著對社會參與的排斥。易言之,行政指導性案例亦應當注重法學教授、行業專家和律師等社會力量的融通,立足行政法規范既定框架對經由理論與實踐充分論證并形成共識的疑難復雜案件予以“附條件”吸收。(3)案例“質量擔保”:最高法院應通過定期舉辦行政案例專題培訓等諸多形式加強對高級法院的案例工作指導,確保辦案法官培育和撰寫行政案例之“自覺”,強化其編纂行政案例的技巧及運用案例指導訴訟并予以裁斷的能力。各級法院亦應建立完善行政案例創制考評機制,將行政案例的創制情況納入績效考核范疇,“對參與案例創制的承辦法官、所在部門及法院,給予必要的精神和物質獎勵,將案例創制成效與法官評先晉級掛鉤”[10],同時單列“行政案例創制”項目經費,并對行政案例創制所需的時間和人力等資源予以優先調配。
2.修正功能偏差:突出“指導優位”。最高法院作為政治架構中的關鍵環節,其功能界定并非因時代不同或者國別差異而僅限為“案件審判”,然則,囿于最高法院政治功能實現路徑的多元化(比如向中央作專題報告、出臺司法解釋、提出法律的制定意見等),將行政案例納入其政治功能實現載體的范疇既無必要亦非理性。如此,最高法院發布行政案例應當避免甚或杜絕“單純回應政策需求”“表征法規范內涵”“法律適用必然推定”等案件類型,而突出“指導功能”——“行政指導性案例必須限定于揭示法律適用疑難問題的類型化案件,其通過裁判要點所呈現的裁判規則應當是對‘原本規制模糊、欠缺明確的既定行政法律規范’的解釋、明確與細化[11](p03)”,諸如行政指導性案例第39號案對“高等學校行政訴訟被告主體資格的確認”、第59號案對“建設工程消防驗收備案結果通知行政確認行為性質的確認”等。
3.賦予強制效力:增強“適用剛性”。雖然占絕對多數的法官對行政指導性案例的制度價值和應用空間予以認可,但囿于行政案例“僅具備事實約束力”的效力通識,其均選擇對行政案例“避讓或者棄置”并最終導致“制度虛無”。如此,為保證行政案例的適用剛性應當賦予其法律強制效力:(1)“應當參照”中“‘應當’就是‘必須’,‘參照’就是‘參考并仿照’[12](p33)”,即法官必須清晰厘定行政指導性案例與待審案件之間“相類似之處”,提煉剝離貫穿案件每一節點上可供參照的裁判規則和方法、法律思維和司法理念,甚或法治精神,最終作出呈現“高仿性質”的公正裁斷。(2)行政案例所凝練的裁判要旨和規則在裁判文書中應當作為依據和理由徑直援引。現行規制下的指導性案例并非能夠達至與諸如司法解釋及規范性文件等同的法律位階界定,然則,此系列案例所呈現的裁判規則均系經由最高法院審委會討論通過并予以固定,若以此為基準,行政案例應當具備同司法解釋及規范性文件相近甚或同等的法律效力,各級法院應當將其作為依據和理由在裁判文書中予以援引。(3)“應參未參”應納入提請上訴與申訴的理由范疇,即當法官在審理類似案件時應當參照行政指導性案例而未予參照的,應當在裁判文書中詳細載明“不予適用”行政案例的理由。若承辦法官未主動參照或者當事人申請而拒絕參照的,同時亦未在裁判文書中明確載明正當理由的,導致裁判與行政指導性案例差距較大而顯失公正或者違背行政案例指導精神的,當事人均有權提出上訴或者申訴。
4.拓寬監督路徑:凝聚“監督合力”。為確保對行政案例指導制度運行的監督實效,在注重“內部自控”之同時亦應當強化“外部滲透”,即構建“權力機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的“多維聯動”監督機制:(1)全國人大“合法審查”。由全國人大及其常設機構承擔監督行政案例的“具體職責”并非現實且亦無必要,如此,即可借以司法解釋備案審查機制為參照,設置行政案例備案審查“工作室”對行政案例進行篩查過濾,并將符合既定標準的案例提交法制工作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對上報行政案例的“上位法違背情況、權限僭越情況及與規范性文件契合情況”等予以實質審查,同時依據確認情況分別作出“維持、修正或者廢止”行政案例的決定。(2)檢察機關“實效檢視”。為確保對待審待判案件強有力指導功能的充分發揮,檢察機關即應強化對行政案例的“滲透式”介入,以“法律監督機關”的職能定位,對涉及指導性案例適用的重點事項予以檢視并作出確認,諸如“類案的判定是否準確”“案例的參照程度是否適當,有無超越裁判規則范疇”“案件裁判是否契合同案同判標準”等,繼而對事實認定或者法律適用“確實存在錯誤”的生效裁判依法啟動抗訴程序。(3)人民法院“內部自控”。最高法院確定和發布行政指導性案例應當沖破“追求平穩”的傳統標準束縛,盡可能減少對原始生效裁斷的過分縮減與修整,最大程度地再現生效裁判的“基本案情”“事實理由”及“裁判依據”等關鍵內容,漸趨增加行政案例呈現內容的寬度和深度,例如原告訴訟請求、被告答辯或者第三人陳述意見、主要證明材料等,甚或涉案卷宗材料亦可“附條件”予以公開。(4)社會力量“適度補強”。行政審判中法官雖主導行政指導性案例的“選擇適用”,但并非意味著法官對此項選擇權的“絕對壟斷”,如此,在將“應當參照指導性案例而未予參照”納入提請上訴或者申訴理由范疇之同時,亦應當賦予當事人同法官相對等的對“是否適用指導性案例”的選擇權。同時,在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案例推薦之基礎上,亦應允許其就“行政案例違法”向人大提出審查建議,人大職能機構應當進行考究并及時向提出建議者甚至社會公眾反饋審查結果,確有必要的應當移送專門委員會審查并提出意見。
四、余論
案例指導制度被賦予強烈的時代氣息和本國特色,其承載解釋法律、統一標準、指導裁判等諸多價值預期,作為司法改革的重要內容,其本應呈現強大的生命力和制度活力。然則,從近六年行政指導性案例的發布情況看,指導性案例遭遇諸如數量短缺、功能異變、效力未定、監督失范等運行困境,易言之,行政指導性案例并未達至制度預期,其因“影響力限制”和“適用率低下”而處于實質的“虛置狀態”。如此,即須要對“應然層面”的行政指導性案例制度進行“實然意義”上的重構,確保指導性案例在“數量、質量、功能、效力”等諸項元素與審判現實需求相契合,激活“沉睡制度資源”之同時最大程度實現其功能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