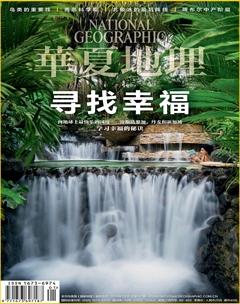末代冰洋
蒂姆·福爾杰



我們先看到的是獵殺殘留的現場:海冰之上的雪地中一道殷紅血跡,寬得嚇人,可能是一頭環斑海豹的血。然后北極熊出現了。這頭母熊體型碩大,估計有兩百多公斤重,身后跟著只熊崽。它們剛剛從一條裂溝跳進冰海,沒過幾秒卻又爬上冰面跑起來——我們乘坐直升機飛近,驚擾了它們。長久的奔跑會傷害北極熊:滿身脂肪和絨毛的隔熱性太好,以至于體內有過熱的風險。33歲的魁北克人駕駛員弗朗索瓦·萊圖爾諾-克盧捷帶我們爬升了一些,熊母子便放緩腳步,從容起來。
跟著它們飛了幾分鐘后,萊圖爾諾-克盧捷使直升機緩緩停落在百米之外的冰面上,關了引擎。母熊前腿離地,直立著打量我們10米長的飛行機器,眼神里帶著北冰洋頂級捕食者的威嚴。小熊仍四足著地待在它身后。我們在時間仿佛斷流的片刻里品味著這幕畫面——除白熊與我們之外就是空曠而廣大的冰雪,融水匯成數不清的淺池,映照著微弱紅藍光暈中的夏日艷陽。后來,螺旋槳用一聲狂躁的哀鳴打破沉寂之境,我們再次升空,折向西南,那邊有我們的營地,設在加拿大巴芬島最北端,距南邊的哈得孫灣約1100公里。
再過幾十年,這般光景就不大可能存在了,至少不會是在夏季的這個區域。隨著地球升溫,夏季海冰以及它所養育的那些適應性超群的生靈如白熊、海豹、海象、鯨、北極鱈魚、蝦蟹、冰藻,都很可能從巴芬島周邊絕跡。在飛越廣袤的冰原時,我們實在難以相信自己正見證著——并且與全人類一起正加劇著——它的消亡。1980年代,衛星數據表明夏季結束時北冰洋海冰的平均覆蓋范圍為750萬平方公里。從那時到現在,損失的冰面已超250萬平方公里,差不多等于美國阿拉斯加、德克薩斯、加利福尼亞三個大州的面積總和。

哈得孫灣最北端,渾身濕透的北極熊爬上一塊浮冰。它們會蹲守在冰上,等海豹露頭時發動攻擊——這種獵物為其提供了90%的食物熱量。國家地理學會駐會探險家恩里克·薩拉正在主持一項守護北極熊最后棲息地的事業。“在俄羅斯,我們看到有北極熊困在島嶼上,靠吃草和海鳥充饑。”他說。
氣候電腦模型顯示,到2050年代,僅有不到52萬平方公里的多年冰留存。也有好消息(雖然只是大喪中的小幸):剩下的冰將集中在一個緊密區域,位于格陵蘭島和加拿大的埃爾斯米爾島以北。那座縮小的冰雪堡壘將是許多北極野生物種最后的求生陣地。
“依附于海冰邊緣環境生活的動物夏季將在那里聚集,”國家地理學會原始海洋項目的主導者、海洋生態學家恩里克·薩拉說,“情形類似非洲草原旱季的飲水點,各種動物都會露面。”
薩拉這次帶著潛水員和電影制作團隊來到巴芬島,一是為了拍攝記錄已在劫難逃的冰雪世界,二是為保護更北邊“最后的海冰”之必要性取證。自十年前“原始海洋”項目啟動以來,已幫助約800萬平方公里的海域取得受保護狀態。但若要保護殘存的北極海冰,還須取得格陵蘭和加拿大政府的合作,并將是該項目旗下愿景最大的一項事業。
也是至為緊要的一項事業。“北冰洋的改變比任何地方都快。”薩拉說,隨著海冰消退,船運、捕撈、油氣開發等事業可能進駐。如果要對海冰和它庇護的動物們加以保護,就必須趕在外界開采北冰洋資源的勢頭變得不可遏止之前。薩拉說,為了促成這項事業,“我們的前瞻跨度是25年。”




在衛星照片中——或許在我們的想象中也一樣,地球之巔那片白釉般的冰原看似無比沉寂,如同一座毫無特征的白色大陸,是靜止而永恒的。其實它卻是一大群相互擠撞的浮冰,在風與洋流推動下往復漂行于北冰洋兩岸之間,單程可持續數年。
“有些人說已經沒希望了;照我們現在的趨勢下去,將喪失全部的海冰。但冰量下降曲線還拖著這條長尾,使我們有時間采取行動。”
海洋學家斯蒂芬妮·普菲爾曼
“世人不了解北冰洋。”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的海洋學家斯蒂芬妮·普菲爾曼說,“他們把它和‘冰冠混為一談,以為它凍得很結實,融化只會沿著邊緣緩緩進行。他們想不到它還有充滿動態的方面。”
2010年,普菲爾曼效力的團隊找出了北冰洋夏季海冰可能性最高的末期退守位置,這項工作后來對“原始海洋”項目發揮了指導作用。他們對多種電腦模型和衛星數據進行比較后發現,風與洋流會合力把整片冰洋里的漂浮海冰歸攏,擠向格陵蘭島北部邊緣和加拿大的北極群島——該區域有超過3.6萬個島嶼和景色壯美的峽灣。年復一年,巨大的浮冰會在這片相對平穩的海域堆積,到本世紀中葉將成為北冰洋最后的多年冰。
雖然在今后幾十年里會迎來海冰量的急劇下降,但一條殘存的狹長多年冰帶卻能支持到本世紀晚期。如果我們終結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剩余的冰還能留存更久,甚至也許能撐到我們找出辦法,從大氣中去除足夠二氧化碳、使地球重新變涼的時候。“海冰預測模型并不是直降到零的。”普菲爾曼說,“有些人說已經沒希望了,因為照現在的趨勢我們會喪失所有海冰。但如果用氣候模型來判斷,就能看到冰量曲線雖然劇降,卻拖著長尾,這給了我們一些時間來行動,并有機會減輕暖化效應。”
到時,那些確實在北極堅守下來的海冰可以為依附冰生存的物種提供一個穩定環境,只是有些擁擠。“關注棲息地的人可能會說,夏季有時在西伯利亞近海或波弗特海還會有冰。但這是靠不住的。”普菲爾德說,“因為到處移動的冰無法支持棲息地。實際上它們十有八九還是會拱到格陵蘭和加拿大的海岸線一帶。”
“這是個新來的。”西奧·伊庫馬克在營地附近彎腰指著一棵嫩綠的新芽說。60歲的伊庫馬克作為伊格盧利克島土著,是我們這次考察的向導和顧問。6月的午后陰冷多霧,海岸之外,小灣冰封如故。已有多日看不到太陽。伊庫馬克背著一支步槍,必要時用來嚇走北極熊——我們已在離營地僅幾百米的沙地里看到熊爪印了。
那棵小小的綠芽只有幾厘米高,在這片北極地區的因紐特方言中找不到對應的詞匯。伊庫馬克不認得它,只知道它是這里的土地和生活正在發生變化的又一個例證。行走中,我們見到了伊庫馬克所說的當地新景觀——闊大的圓形落水洞,那是永凍土消融造成的。
后來我們待在吃飯用的大帳篷里,伊庫馬克教了我幾種極地動物名稱的本地叫法。aarluk意為“一切通殺”,指的是虎鯨;tingugliktuq意為“肝臟壞,吃不得”,指的是角百靈鳥。但還有些鳥獸,例如知更鳥,對于北極地帶是極陌生的新客,伊庫馬克不知該叫它們什么。
隨著全球變暖,南方的動植物物種已開始向北移動。阿拉斯加大學生物學家布倫丹·凱利說,未來這個趨勢只會越來越快。北極野生動物的棲息地萎縮后,存活下來的種群很可能產生深遠的變化。各式各樣的物種將被迫在前所未有的緊密空間內共存。
“整個北冰洋內有發生大規模基因洗牌的潛在趨勢。”凱利說,“我們對海洋哺乳動物做了一次調查,找出的可雜交物種有34個。”出于一些科學家尚未查明的原因,海洋哺乳動物在分化成不同的種屬時傾向于保留同樣數量的染色體,也就是說,滿足跨種雜交的關鍵條件。
“所以就出現了從其他各方面看都歸于不同‘屬的動物,實際上卻能夠混搭生出有繁殖能力的后代。”凱利說,“琴海豹和冠海豹就是一例,還有證據顯示白鯨與獨角鯨之間也存在一個雜交種。”棕熊與北極熊的混血后裔已經在北極地帶游走了。遺傳學研究表明,北極熊于50萬年前開始從棕熊家族中分出;如今,全球變暖則威脅要把兩個物種重新統一。
“我們可能失去北極熊。它們也許會被重新吸收到棕熊基因組中——那是它們的老本家。”凱利說,“我們面對的不僅是生態改變,還有大大加速的進化改變。”
凱利說,轉變的最終結果可能是一場規模巨大、不可逆轉的基因多樣性災難。就算避開這種結局,北極野生動物的日子仍不好過。“我們令棲息地環境改變得太快,即使它們擁有可以應變的基因多樣性,也未必來得及應變。”對世上的某些標志性物種來說,北極最后的冰區意味著生存與滅絕的分別。
“多寧靜呀,是吧?”海灘上,恩里克·薩拉微笑著湊過來,身后是我們的宿營地,分兩排支著二十幾座橙色帳篷。我們向東望去,視線越過納維伯德灣的重重冰面,投向幾公里外的拜洛特島。它比夏威夷島還要大,布滿山巒與冰川,是蟄伏過冬的北極熊和數十萬筑巢鳥類的避風港。太陽出來了,天氣終于轉晴,幾乎無風。已等了一個多禮拜的薩拉和他的潛水員們開工心切,想到拜洛特島西岸之外選幾個小島,在其周邊的開闊水域一探究竟。再過幾周,海藻就會瘋長,水體變渾,下水拍攝的機會將不復存在。但此刻的冰海還只是剛燃起生機。
“陽光就像生態系統的‘打火機。我們此行也是因為這個。”海灘上,身穿潛水服的攝影師馬努·圣費利克斯也走了過來。在之后幾天里,如果天公作美,他和薩拉等人將記錄這里的生機之美——如果我們不能保住北極最后的海冰,就將眼睜睜地看著這份美消逝。
還有更難的工作——比起在冰海里潛水更艱苦——要花上數年來完成:說服各地政府協力拯救一片超越國界的海域。光保護最后的冰區還不夠,因為海冰會長距離漂行,它的源頭最后也同樣需要得到保護。眼下就有現成的例子:西伯利亞冰中混有俄羅斯工業城市諾里爾斯克(世上污染最嚴重的地方之一)流出的鎳和鉛,這樣的臟冰有時會漂入加屬北冰洋,一經消融就會毒害食物網。
“我們這次看到了獨角鯨、白鯨和北極熊,這是個好跡象。”圣費利克斯說。這意味著此地的食物鏈仍處于健康狀態。我們談到前些天在一次直升機巡航中看到的成群座頭鯨,它們能憑借碩大的腦袋撞破半米多厚的冰。座頭鯨的壽命可達二百歲以上。(研究者斷定其年齡的方法之一是對嵌在它們身體中多年的魚槍尖進行碳同位素年代測定。)圣費利克斯說,現在它們中最年長的個體剛出生時,拿破侖可能還在世。“想想看吧!”他說,“我們拍攝的那頭幼鯨說不定到2215年還活著吶!”
那得是在我們運氣好,而且眼光夠長遠的情況下。薩拉說:“這不是一件簡單、線性發展的事情。我們現在還看不出它的結局。”
末代冰洋
據預測,北冰洋的多年冰將于今后幾十年內縮減到只剩加拿大、格陵蘭北緣的一條狹長區域。風和洋流的作用將加固這處最后的冰棲野生動物避難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