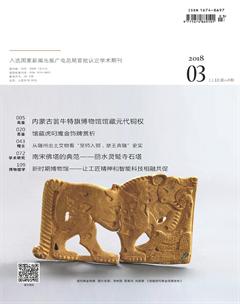試析長江三角洲地區三足陶器的起源
程正榮
摘要:在新石器時代初期產生以來,陶器都以圜底器居多。新石器時代早期和中期陶三足器出現并發展成熟,但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河姆渡文化中陶三足器的出現較為特殊。文章嘗試以河姆渡文化出土的陶三足器為例來分析長江三角洲地區陶三足器的產生,并認為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陶三足器產生與環境的突變和文化的向外擴張而引起的交流關系密切。
關鍵詞:長江三角洲;河姆渡文化;陶三足器;環境突變
1長江三角洲地區考古學文化譜系梳理
新石器時代早期長江三角洲地區典型的考古學文化有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跨湖橋文化的年代為距今8000~7000年,河姆渡文化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5000~前4000年,馬家浜文化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5000~前4000年。
跨湖橋文化以跨湖橋遺址的發掘而命名。跨湖橋文化中的陶胎呈黑色是跨湖橋文化陶器的一個顯著特色。器類主要有釜、圜底罐、雙耳罐、直口缽、圈足盤、圈足碗、支座和器蓋等。其中支座的發現很特殊。而有關跨湖橋文化的來源目前還不能下定論,只是其某些陶器顯示出與皂市下層文化陶器相似的特征,但也有自己的特色陶甑。跨湖橋文化的分布范圍與后來的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有大量重合,跨湖橋文化的陶器與河姆渡文化的陶器有很多相似之處。但需要說明的是,兩者的陶器形制還是有區別的,因此有的學者認為由跨湖橋文化發展到河姆渡文化的斷層期間,文化發生了突變,但還需要更多證據證明。
河姆渡文化是以河姆渡遺址命名的一種考古學文化,揭示出一種嶄新的文化遺存。但學者對其內涵有不同的認識:有的學者認為它只包括河姆渡遺址第3層和第4層遺存,還有的學者認為應包含河姆渡遺址的全部4層遺存。
馬家浜文化是太湖周圍地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以紅色陶、腰沿釜和大量的骨器等為主要特征。關于馬家浜文化的性質問題,最早認為其文化應屬于青蓮崗文化,但隨著桐鄉羅家角遺址的發掘,表明馬家浜文化與青蓮崗文化有區別,與河姆渡文化有密切聯系但又不是相互繼承的關系。
從以上的文化梳理中,我們發現在長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早期并沒有很成熟的陶三角陶器,但到了河姆渡文化的第3期和第4期的時候,三足陶鼎產生了,并且所發現的陶鼎已經非常成熟,因此這不得不讓人思考在河姆渡文化的三四期制作三足器的技術是如何產生的。
2河姆渡文化中的陶支腳
長江三角洲地區最早的陶支腳是在距今8000~7000年的跨湖橋文化中發現的。雖然跨湖橋文化與河姆渡文化的繼承關系還沒有得到確認,但河姆渡文化同樣也出土了大量的陶支腳,則說明兩者之間所反映的人們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相似之處。
在河姆渡文化中還有一個現象就是文化層的斷層。在河姆渡文化的三四層文化層和一二層文化層之間有近400年的空白時期。聯系到河姆渡文化在一二層文化中才出現了陶鼎,而且陶鼎一出現就顯示出較為成熟的形制,這就讓人對河姆渡文化陶鼎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河姆渡文化早期的陶支腳以豬嘴形為特點,而晚期陶鼎的鼎足卻是扁足形。那么河姆渡文化中的陶鼎究竟是產生于自身觀念的轉變,還是與其他文化交流的結果?
陶支腳的產生主要是生產生活中為了便于更快地炊煮食物。而三足陶器的產生應該是源于陶支腳的長時間使用過程中的不便進行改進而演化而來。但有學者對此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博士生導師錢耀鵬先生認為,史前陶三足器的產生與環境惡化關系密切。他認為:由于史前環境的惡化,燒造陶器的燃薪短缺,促使人們在燒造陶器的過程中要不斷提高陶器的成品率,因此需要改造陶窯結構和改變陶器的形態來達到目的。而與改變陶窯結構相比,通高改變陶器的形態來提高陶器的成品率顯然更為簡單。因此,為了一次能夠燒造更多的成品陶器,為陶圜底器加裝三足以使陶器在燒造過程中均勻受火,成品率提高。而隨著陶窯技術的不斷改進,陶三足器的三足也逐漸增高(錢耀鵬老師授史前考古學專題時提及此觀點)。對此筆者雖然很受啟發,但認為史前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三足器的產生可能與柴薪的減少無關,卻與水患的關系較為密切,或者說它們之間應該有著間接的聯系。
3長江三角洲三足器起源的討論
一種新生的器物形態的產生,首先要考慮有產生這種器物形態的若干條件。三足器的產生首先是為了更快地加熱圜底器的液體等的現實實用性。其次是要考慮這種新型器物的原始形態,只有在原始形態上獲得經驗的突破時才能產生一種新型的器物。基于以上的考慮我們來分析河姆渡文化陶器的起源。
無論是跨湖橋文化,還是河姆渡文化,都有陶支腳的存在,而據嚴文明先生說在河姆渡文化發現有經過火燒的石質陶支腳的存在。陶支腳作為圜底炊器的輔助設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陶支腳作為方便加熱的實用工具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在陶支腳使用的過程中,人們積累了三角形具有穩定性的經驗,這對于完整的三足器的產生啟發性很大。史前長江三角洲地區是東海的迎風口,地形又是丘陵和平原地帶,河湖發達,一旦東南季風到來,對于居住在這里的人們是極大的威脅。為了獲取更多的資源,人們不得不時常進行遷徙,而遷徙過程中陶支腳總是攜帶不夠方便。因此,產生了改進為固定三足器的可能,但這種改進需要一種啟發。在河姆渡文化的第二層中發現了大量成垛水稻的沉積,很顯然這些水稻是沒有來得及運輸回家就被掩埋覆蓋了。從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地形和環境分析,出現這種情況只有一種可能,就是河姆渡文化遭受了洪水或者泥石流的自然災害。而自然災害的發生勢必導致人口的遷移。從馬家浜文化所處的位置和出土陶器的相似性等特點來看,河姆渡文化應該是向東北等高地轉移。而東北部正是馬家浜文化早期的范圍之內,此時的馬家浜文化已經有了陶盉陶三足器。在獲得了種種啟發后,河姆渡文化在第二層和第一層文化中也開始出現了陶鼎等三足器。陶鼎的形態,特別是足部與馬家浜文化陶鼎十分相似,也說明了兩者的密切關系。根據河姆渡文化四層、三層出土的器物與二層和一層出土的陶器分析,應該是同一族群的文化。這就意味著在環境狀況惡化的情況下存在北遷的河姆渡人南返的情況。因此,河姆渡文化的陶三足器的產生應該和文化的傳播有著密切的關系。
但馬家浜文化的陶三足器又是來自哪里呢?馬家浜文化與北辛文化的關系十分密切,北辛文化中的一些釜應是受馬家浜文化的影響而產生(灌云大伊山遺址,所出腰沿釜與草鞋山等遺址的圜底筒形釜相似),馬家浜文化在第三期出現鼎很可能與北辛文化的影響有關。但也有人認為馬家浜文化的鼎(如草鞋山)為圓腹,腹中部飾堆紋一周,三足呈扁錐形而微向外伸。這兩類鼎不論在器形上、紋飾上都有區別。但無論如何,三足器產生的北方總是在觀念上影響到了長江三角洲地區,并且在創造器物的過程中給予了極大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