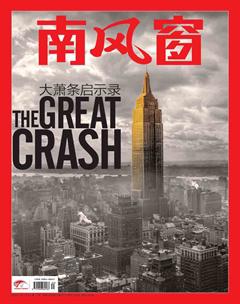那場不能遺忘的貿易戰
雷墨

“這個法案將創造一個新的繁榮時代”,1930年5月,《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在美國國會辯論正焦灼之時,共和黨參議員威利斯·霍利做出了這樣的承諾。他是這個關稅法案的兩個主要發起人之一。1930年6月17日胡佛總統大筆一揮簽字后,并沒有出現“新的繁榮時代”,緊隨其后的是波及當時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大蕭條。
歷史已有定論,旨在提高關稅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不是1930年代大蕭條的始作俑者,但它所引發的貿易戰卻起到了極大的催化作用。此前,世界經濟之水已經“渾濁不堪”—生產過剩、需求萎縮、貿易下滑,但這個法案的通過像是在往水中投毒,嚴重惡化了世界經濟環境。《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已被歷史定格為保護主義的同義語。
毋庸諱言,特朗普是最能讓人聯想起1930年代世界大蕭條的美國總統。他最近說“關稅是最偉大的”,此前還說過“貿易戰是好事”。更為關鍵的是,特朗普政府已經在頻繁揮舞關稅大棒,已經挑起了貿易戰。如果歷史有所借鑒,那么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不會輕易在貿易上休戰。國際貿易體系正處在巨變前夜。
大蕭條催化劑
在美國經濟史上,1919年-1929年被稱為“新經濟時代”。但從1928年開始,歐美主要經濟體都不同程度出現經濟疲軟,1929年10月華爾街股市崩盤成為轉折點。根據英國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世界經濟千年統計》,當時世界27個主要經濟體(占當時世界GDP總量70%),在1929年至1932年間,GDP總量平均下降了15%,對外出口額下降了50%。
貿易坍塌,是大蕭條的顯性特征之一。一戰爆發前,美國經濟總量尤其是制造業實力已碾壓歐洲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穩居世界第一。也正是在“新經濟時代”,戰后恢復期催生的巨大需求,使得國際貿易在GDP中的比重大幅攀升—以歷史上未曾有過的范圍和幅度。美國龐大的經濟體量,以及通過貿易構成的經濟聯結性,解釋了為何它的政策行為能產生空前的連鎖效應。
根據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歐文的研究,貨幣與財政因素才是導致大蕭條的始作俑者。一戰后,美國事實上成為整個歐洲的債權國。為了應對經濟增速下滑,1928年美國大幅提高利率,資本輸出減緩使歐洲資本流入幾近枯竭。歐洲經濟疲軟的后果迅速反作用于美國,世界經濟已經一只腳踏入大蕭條的泥潭。但道格拉斯·歐文也認為,美國提高關稅導致局勢大幅惡化,使國際合作應對危機幾無可能。
1929年華爾街股災后,同樣也是出于危機應對,美國在1930年推出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把關稅從38%提升到45%。這個法案只是臨門一腳,但這一腳后果嚴重。根據道格拉斯·歐文的記載,法案在國會辯論期間,美國收到了23個國家的正式抗議。法案生效的1930年,有61個國家針對美國進行了關稅報復。從“保護”到“報復”,貿易戰“惡魔”被釋放出來。
1928年大選期間,總統候選人胡佛最響亮的競選口號是提高關稅保護美國農業。
高失業率,最能體現大蕭條造成的悲劇。美國經濟學家巴里·埃森格林,對1920年-1939年歐美主要經濟體失業率做過統計。根據他的數據,1928年危機初露苗頭時,美國(6.9%)、英國(10.8%)、德國(8.6%)、法國(4.0%)的失業率大多在10%以下。這些國家失業率觸頂,正好發生在貿易戰威力觸頂的1932年、1933年(美國:37.6%;英國:22.1%;德國:43.8%;法國:15.4%)。
貿易戰不是觸發因素,但也絕不能算次要因素。《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歷史罪過”在于,它的負面效應在實施之前就產生了。1928年大選期間,總統候選人胡佛最響亮的競選口號是提高關稅保護美國農業。在這些政治信號之下,投資者不會等到法案通過、實施后再做投資決策。這個法案的醞釀過程,很大程度上也是1929年華爾街股災的醞釀過程。
道格拉斯·歐文的書中提到一個細節,國會辯論《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是否對西紅柿征稅都有20多頁的記錄,但對其他國家的抗議竟然沒有任何議員辯論的記錄。也就是說,當時美國的政治精英們,根本沒有意識到,或者沒有把其他國家可能的反擊當回事。
以歷史視角來看,對這個現象較為合理的解釋是,當時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分量,與其所應承擔的責任嚴重不匹配。對于其他國家的抗議,胡佛總統的回應是“關稅屬于美國內政”。美國學者查得·布朗在其2011年的《大蕭條與進口保護》一書中提到,那時的美國已是“世界銀行”,但卻乳臭未干,“美國反復無常、不可靠,不愿展現耐心,不想承擔作為領導者的代價”。
歷史魅影重現
查得·布朗筆下的美國,與如今的特朗普政府執政的美國有幾分神似。1928年大選那一年,美國很多農場主已經資不抵債,瀕臨破產邊緣。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胡佛喊出“給農民創造更好的生活”,與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期間許諾給藍領工人“創造工作”如出一轍。2018年7月24日,特朗普政府宣布120億美元補貼農業的計劃,這項政策的實施方“商品信貸公司”(隸屬于美國農業部),正是創建于大蕭條時期。
那個時代的美國,保護主義就是愛國主義的同義語,經濟民族主義并不是個貶義詞。1928年美國大選,胡佛大打貿易保護主義牌,不僅擊敗民主黨候選人阿爾·史密斯,還使得共和黨掌控參眾兩院,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在國會通過鋪平了道路。這一幕與2016年的大選結果,以及此后特朗普政府頻繁揮舞關稅大棒,給人某種“歷史魅影重現”之感。
反對的聲音,同樣遭到忽視。《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在國會通過之后,美國1028位經濟學家聯名發表公開信,向胡佛總統請愿不要在法案上簽字。據美國經濟史學家的記載,當時的摩根合伙人,同時也是胡佛總統的非正式經濟政策顧問托馬斯·拉蒙特說,“我幾乎是要跪下祈求胡佛總統否決這個法案,這個法案助長了全世界的民族主義。”
2018年5月,美國1040位經濟學家也向特朗普發了一封公開信(聯名的包括14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勸他改變現行的貿易政策。這封信一開始就提到了1930年的那封信:“國會不聽從1930年經濟學家們的建議,結果是所有美國人為此付出代價。”至少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特朗普沒把這封信當回事。
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實施后,課稅對象涵蓋1/3的美國進口商品。截至目前,特朗普政府的關稅大棒,受影響的進口商品占比不到5%。但有學者預計,如果特朗普政府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征稅的政策落地,那么比例將會升至12%,如果特朗普政府進一步對汽車及其零部件征稅,那么所占比例會大幅提升到27%,直逼《斯姆特-霍利關稅法》。
為了遏制貿易保護主義,在國際聯盟的召集下,1930年、1931年連續兩年召開了“協調經濟行為國際會議”,但都無果而終。那時奉行孤立主義的美國,既不是國際聯盟的成員國,對這類會議的興趣也不大。美國不會重回孤立主義,但特朗普入主白宮后,在七國集團會議、二十國集團會議等國際多邊場合,的確讓美國表現得像個孤家寡人。
歷史魅影重現,但歷史不會簡單重復。美國因《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遭到了貿易對象的關稅報復,同時這些國家之間也競相提高貿易壁壘。也就是說,那時的貿易政策特點不僅有以牙還牙,還有以鄰為壑。但截至目前這種狀況還沒有出現,未來出現的幾率也不太大。而且,如今的全球經濟環境、地緣政治、政府治理與危機應對能力,都與大蕭條時期明顯不同。
自由貿易幻象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是個歷史節點,它把美國的關稅推向了此后歷史中沒有再出現過的最高點。1934年羅斯福政府實施《互惠貿易協定法》后,美國走上了在國際上推動降低關稅的進程。二戰后,美國牽頭關貿總協定談判,直至主導世貿組織的建立,美國都是以自由貿易旗手的角色出現在國際社會。但為何換了總統后,美國卻扛起了保護主義大旗呢?
所有的發達國家歷史上都曾實施過嚴格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只是當它們具備了相對于對手的技術優勢之后,才主張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
“歷史地看,自由貿易是例外,保護主義是常態。”法國已故著名戰后經濟史學家保羅·巴洛赫在其《經濟與世界史:神話與悖論》中有這樣一個觀點。在該書中巴洛赫記述了這樣一個現象,自由貿易思想之源的英國,實施高關稅政策的時間遠比低關稅政策要長。1820年英國關稅曾高居全球榜首的59%(那一年美國關稅40%)。英國真正實施零關稅是在19世紀中后期至大蕭條前,但那也是國際貿易史上空前絕后的插曲。
英國劍橋大學研究發展經濟學的張夏準教授,在其2002年撰寫的《過河拆橋:歷史視角中的發展戰略》中對這個現象做過分析。他認為,現在所有的發達國家歷史上都曾實施過嚴格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只是當它們具備了相對于對手的技術優勢之后,才主張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美國走的正是英國道路,只不過走得更堅決,也更高明。
美國獨立直到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關稅長期扮演著聯邦政府主要收入來源的角色。南北戰爭后,美國制造業開始蓬勃發展,關稅才開始被賦予保護主義的功能。主張自由貿易的民主黨與奉行保護主義的共和黨輪番執政,導致美國關稅上下波動,但總體上遠高于當時的歐洲。1913年至大蕭條前,歐洲平均關稅維持在25%左右,但美國長期保持在近40%的高位。也就是說,美國那時是國際貿易體系里的絕對另類。
1934年《互惠貿易協定法》的意義,廣為人知的是美國扛起了自由貿易的大旗。但另一個影響深遠的意義在于,該法案把部分關稅權和貿易談判權從國會轉移到白宮。這使美國在國際貿易博弈中反應更快,應對也更高效。1970年代中后期,美國制造業面臨日本、歐洲的競爭,國會通過了一系列貿易法案,如今為人所熟知的“301條款”“特別301條款”等,都是在那個美國感覺到競爭威脅時期出現的。
這些條款本質上屬于保護主義,其邏輯內核與歷史上美國貿易保護政策沒什么不同,都是為了培育、維持競爭優勢。商人總統特朗普眼中的威脅,會本能地偏向經濟威脅。“當一個國家(美國)與幾乎每一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之間都蒙受數10億美元的損失時,貿易戰就是好事,而且能輕易取勝”,特朗普今年3月說的這話,不能掉以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