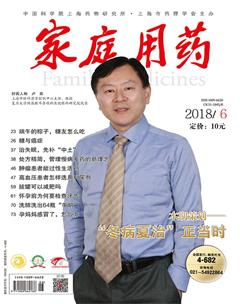這“支架”裝不裝
楊秉輝
救護車“嗚嗚”地叫著,在省立醫院急診室門前戛然而止,救護車車門一開,跳下擔架員,口中叫著“心梗、心梗”,抬出一位60多歲的男士,只見患者面色蒼白、額角滲汗、目光游移,陪送的家屬大叫:“醫生快搶救、快搶救!”
患者躺在可移動的推床上被推進室內,接上心電圖儀一看:“急性大面積心肌梗死!”血壓只剩下90/56毫米汞柱,患者急需緊急救治,于是緊急啟動心肌梗死綠色通道,工作人員一面將患者送進心導管室檢查,一面通知患者家屬:“病危!”
兩位患者家屬等在心導管室門口,一位年長的女士嚶嚶哭泣,估計是患者的妻子,她身邊還有一年輕的女士,約30來歲,短發,戴眼鏡,很干練的樣子,正在安慰著年長的女士,估計是患者的女兒。
過了一會兒有一位醫生走出來向患者家屬解釋病情:左側兩根冠狀動脈分支一根完全阻塞、一根阻塞90%以上,右側冠狀動脈阻塞70%,需放置支架治療。
冠心病患者發生急性心肌梗死是因為冠狀動脈內的粥樣斑塊破裂所致,所謂“粥樣斑塊”是聚集在冠狀動脈最里面一層薄薄的內膜下的脂類物質形成的隆起,這斑塊一旦破裂,這些脂肪類物質便會順流而下被沖到下游較細的冠狀動脈中將其堵塞。同時還會促成局部血液凝集,進而造成血栓,被沖到下游血管中,加重了血管的堵塞,血管堵塞后心肌缺血、缺氧,便很快壞死,即心肌梗死。
搶救心肌梗死可以用藥物溶解血管里的血塊,叫作溶栓治療,但最直接有效的辦法是通過導管放入支架,這“支架”到位后能撐起被堵塞的血管,使血管再通,心肌缺血、缺氧的情況可以立即得到改善。不過,心肌梗死的搶救必需爭分奪秒,一般認為發病6小時內為搶救心肌梗死的“時間窗”,超過這一時間,救治的效果極差。心肌梗死的“支架”治療在國內外已實施多年,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
二
該醫生說明患者需放置支架治療后,患者的妻子似乎聽說過放置支架可以搶救心肌梗死的,只是微微地頷首,表示遵從醫生的意見。但此時年輕女士卻開始了提問:“放支架能肯定搶救成功嗎?”
“放支架是搶救心肌梗死很好的辦法。”醫生道。
“我問的是:放支架能肯定搶救成功嗎?”似乎有點生硬。
“不能說‘肯定能搶救成功。”這是實話
“那好,人命關天,我們要肯定有效的辦法。”
“放支架便是有效的治療方法。”
“就沒有別的有效方法了嗎?”
“可以做溶栓治療,用藥溶解堵塞冠狀動脈的血栓。”
“好嘛,那你為什么不先說?”年輕女士不友好地質疑。
“我們認為放支架最好,因為現在需要爭取時間立即開通堵塞了的血管。溶栓治療我們也會考慮合并使用,不過溶栓治療也有可能引起腦出血的風險,家屬亦需理解。”醫生說得很清楚了。
“網上說得很多了,中國醫生濫用支架,跟經濟利益有關。”
“這個說法不準確,這個患者現在必須放支架,不然會有生命危險。”
“你別嚇唬人,濫放支架是一位權威專家說的。”
醫生覺得這位女士似乎無理可喻,退回了心導管室。
幾分鐘后一位年長的醫生與一位護士走到門口,醫生對該女士說:“我是負責搶救這位患者的王醫生。”
“心臟科王主任。”護士補充道。
“患者的情況現在非常不好,如果現在還不放支架,可能沒機會再放了,放支架是必需的,請相信我的話。”王主任說得很誠懇。
“為什么你們都要放支架?我真不懂,網上說的北大的老教授三根血管都阻了,他就不放支架,后來他運動就好了嘛。”
“噢,病情不同,現在是急性心肌梗死,不是慢性心肌缺血。”
“不是可以用藥物治療嗎?溶解什么。”
“溶解血栓,溶栓藥我們已經用了。”
“把血栓溶解了不就好了嘛。” 患者家屬還在堅持,不愿放支架。
王主任還準備說什么。導管室里另一位護士出來在王主任耳邊低聲說了句什么,王主任對患者家屬說了句:“患者情況不好!” 立即返回導管室搶救患者去了。
最終患者未能搶救成功,死于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并發大面積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休克。病情嚴重固然是主要原因,患者家屬未能配合醫療應該也是原因之一。
月底,省立醫院心臟科例行病例討論會上又討論到這一病例,討論的焦點是:當患者家屬不理解治療措施、不愿表態,而此種治療又涉及患者安危時,應如何處置?有意思的是陳醫生在會上提出:若患者家屬出于不夠理解,作為醫生應該妥為解釋,但也有的如這位患者的家屬,似乎對醫生、對某些醫療措施有很深的成見,不信任醫生、干擾醫療措施的實行,事實上也是一種 “新形式的醫鬧”。陳醫生便是最先與患者家屬說明要放支架的那位醫生,對患者家屬不能積極配合醫療,以致搶救未能成功有些耿耿于懷。但他的“新形式的醫鬧”一說也得到幾位醫生贊同。
三
“新形式的醫鬧”一說卻又引起了一位新聞記者的注意,一天下午這位記者先向陳醫生了解了這個病例的救治過程,對這位患者因家屬未同意放支架而使搶救失敗亦覺“有新聞性”。當然,陳醫生亦指出:“大面積心肌梗死本身病情嚴重,放置了支架也不能保證搶救成功。”但這位記者認為:“應放、可放而未放,最后搶救失敗終是憾事。”他要探究的是為什么這位患者家屬不愿放支架,陳醫生告以患者家屬不準確地理解“中國醫生濫用支架,跟經濟利益有關”之說 。
“中國醫生是不是濫用了支架?”記者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宏觀的問題,便又去主任辦公室采訪了王主任。
“王主任您好,我們在某些新聞報道中確實看到有‘支架在中國被濫用的說法,而提出此說法的的確是著名專家,您的看法是怎樣的?”
“專家的說法是提醒大家別濫用這種治療方法,也是不錯的。冠狀動脈置入支架是搶救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關鍵性治療措施。當然并非所有冠狀動脈堵塞都必須放置支架,在非急性心肌梗死的情況下,如穩定型心絞痛者,需先經冠狀動脈造影檢查,狹窄程度在70%以上的冠狀動脈分支才有放支架的指征。”
“‘有放支架的指征的意思是必須放支架?”
“也不是,有的患者在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形成的過程中,某支動脈在逐步阻塞的同時一些側支循環形成,心肌缺血并不嚴重,可以用藥物治療,放支架的必要性也就不大了。”
“側支循環形成是什么意思?”
“打個比方吧,您要來我們醫院,可是醫院門前的大路堵塞不通,您正著急,有人告訴您:這條路不太好走已經有些時候了,大家要到醫院去,就想法繞點路、走小路,走多了,這些小路也通順了,一樣可以到醫院來。”
“哦,有道理。明白了,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急性心肌梗死和慢性心肌缺血情況不同。我想專家講的應該是指后面的一種情況。”
“是的,新聞報道有時不夠準確,或者讀者的理解有些誤差。”
“是的,所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記者說,但他又問道,“那么,在慢性心肌缺血的病例中有無‘濫用的情況呢?”看來這記者有點韌勁。
“臨床醫療工作中也有實際上的難處,過去做冠狀動脈造影檢查都需插入導管,對患者來說是一種‘侵入性檢查,檢查時發現某支冠狀動脈已堵塞69%,放不放支架?等到下個月這支冠狀動脈堵到71%了,再重新插管放支架?萬一下個月一下子發生斑塊破裂導致心梗呢?如今可以做CT冠狀動脈造影,這種造影檢查對患者而言是‘非侵入性檢查,可以比較充分考慮是否必要放置支架。不過,在冠狀動脈有相當程度堵塞時放不放支架也需考慮患者的意愿。”
“啊……”記者理解了臨床醫療決策的難度,對王主任的解釋十分信服。微笑說道,“網上傳‘北大老教授三根血管堵塞,不放支架,堅持運動,竟全好了,看來這位老教授必定是屬于慢性心肌缺血的情況。”
“那是當然,若是急性心梗還能去運動嗎?”王主任說。
“網上的信息常不可靠。”記者認為。
“在醫生指導下的適當運動當然是可以的,不過對于慢性心肌缺血的患者來說主要是應認真進行藥物治療,并定期檢查。”
“是的、是的,難就難在臨床醫療是復雜的,而患者與醫生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患者或家屬不容易做出準確的選擇。”
“醫學很復雜,這信息不可能絕對對稱,關鍵是患者應該信任醫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