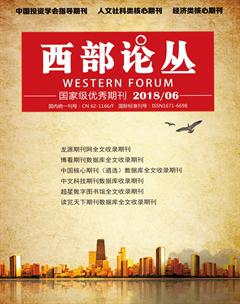論婚生否定制度訴訟主體資格
黃躍程
摘 要:婚生否認制度本在追求親子關系中血統的真實正確,但是在與親屬法中的其他重要價值,亦即家庭的制度性保障以及子女最佳利益保護原則折沖之后,產生了種種不同的面貌,這尤其展現在訴權主體的變動上。隨著我國婚姻法的不斷發展進步,《婚姻法解釋(三)》中的第 2 條已經確立了婚生否定制度,然而,該條司法解釋僅是原則性規定,訴權主體不盡合理,本文從婚生否定的原則出發,借鑒德國和我國臺灣地區規定,試提出完善我國親子關系否認訴訟主體資格的立法建議。
關鍵詞:婚生否認;父母子女關系;子女利益;訴訟主體資格
1婚生否定的三種原則
在世界各國確立婚生否認制度的修法過程中,所發生的諸多爭議,基本來源于婚生否定的三種價值觀,即保護家庭完整、保護血統真實以及保護子女利益原則。三原則的側重不同,是影響當事人能否成為訴訟主體的重要因素。故在此先對此三原則作一簡單的說明。
1.1保護家庭完整原則
在文化傳統之洗禮下,婚姻與家庭被視為具有特殊意義的制度,而應給予特別的保護。在此思考下,受到保護的并非婚姻或家庭中的個別成員,而是婚姻家庭制度本身。該原則側重尊重婚姻所代表的價值以及所默認的功能,即以父母有效的婚姻為基準來建構的親子關系,而并非以血緣關系來判斷。
1.2血統真實原則
血統真實主義系指親子身分關系之歸屬,以雙方生理性的血緣關系為依據。婚生否認之訴的出發點,就是以血統真實主義為原則所設計的制度,在經由婚生推定所成立的父子關系中,如與血統真實主義相違背時,得以婚生否認之訴推翻婚生推定之結果。
1.3子女利益原則
子女利益原則系指以保護子女權益所為的考慮,其性質為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必須在具體事件的脈絡下加以詮釋,其解釋的方向則會受到社會價值觀的左右。但對于某些已一再重復發生之案型,立法者則將其成文化,而成為現行法制度的一部份。例如親子關系身分歸屬中,依現行德國法1599條第2款的規定,于離婚程序進行中所出生的子女,由于在婚生推定的范圍內,仍為夫之婚生子女。但此婚生推定可在夫、妻與第三人之同意下推翻,即以第三人于離婚程序終結前,認領該子女為前提下,而改定該子女之父子關系歸屬。此制度之設計,不再以形式上存在的婚姻家庭為考慮,也不以血統真實主義為內容,而以子女利益為出發,衡量在哪種情況下,子女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顧,故稱為子女利益原則。
2三原則下的我國婚生否認訴權主體擴張之現實與展望
2.1夫方之訴權
我國從1931年民國時期民法開始,就賦予男方否認權,畢竟受推定的是父子關系,所以男方乃當然權利人。不過依照舊法的規定,男方須在子女出生后一年內提出婚生否認之訴。但隨著社會形態之轉變,夫妻因工作之故未必共同生活,等到夫方知悉時,可能已過訴訟時效,無法保障夫之權利。因此臺灣地區在2007年修正的新法,在保障家庭與貫徹血統真實主義的指導下,作了更適合的平衡規定。
首先,婚生否訴之訴期間起算的時點,不再為子女出生時,而為知悉子女不為自己親生開始。從此男方可以審慎考慮,是否要接受該與自己無血緣關系之子女為法律上之子女,并且考慮的期間也由原來的一年延長至兩年,使其有充足的猶豫期。比起舊法而言,雖更重視血統真實主義,但同樣的家庭保障也并未忽視。只是更尊重夫之意愿,而有助于建立更實質健全的家庭生活,同時對子女之利益更為保障。
我國之現行婚姻法解釋已經賦予男方以否認權,但仍未規定男方行使權力的期間,雖然可使男方得隨時請求婚生否認,從而徹底貫徹血統真實主義原則,但卻使得親子關系久久懸而未決,不利于維持持久穩固的家庭安定。而家庭生活的保障和子女關系的穩固,也應該是我國立法者所應追求的目標。
2.2妻方的訴權
依1931年民國舊法的規定,女方并無請求婚生否定的權利。但是,此時女方的婚生否認權被禁止的原因,只是來自封建傳統的貞潔義務。其后,基于男女平等之理念,并信賴母親寧為子女利益,而犧牲自己隱私的偉大情操,我國臺灣地區于1985年將女方納入婚生否認權之主體,以避免子女免于遭受推定父親之虐待,頗具有獨到之處。但生母的婚生否認權,是獨立的請求權還是以子女的法定代理人來形式,若為前者,是否可以通過直接賦予子女獨立訴訟的權利,從而避免訴訟過程和法理的復雜化 ,則有重新檢討的必要;若為后者,則應以新的觀點檢視母親的訴權,即母親在家庭的組成中能擁有何種權限。
依筆者之見解,婚生否認制度乃在婚生推定之下,為貫徹血統真實主義的方法,但家庭生活的保障或對子女身分安定性的需求,仍舊是立法者所應一并追求的目標。雖說婚生否認之訴的對象是父子關系,但直接的利害關系人,尚應包括該家庭成員的母親。畢竟親子關系的否認與否,的確會影響到母親行使親權的權限,而不能說與母親無利害關系。誠然賦予母親婚生否認權,與子女利益或有沖突之可能,但考慮母親于親子關系之建立中,亦為有關之當事人,有其自己之利益以及考慮,雖子女現亦有獨立之訴權,然妻之婚生否認權仍應肯定,只是就立法理由,應為另一種對子女利益保障之解讀,方符合現今之社會形態。
2.3其他可能的權利主體展望
(1)子女的訴權
子女的訴權的行使有兩個疑問,一是子女在未成年時,應如何行使婚生否認權?第二個是當父母作為代理人提起婚生否定之訴時,與子女的利益沖突如何解決?
在子女未成年時,若賦予子女直接提起針對自己的婚生否定之訴,從而讓子女本人承擔家庭破碎的風險,實屬不妥,然而,若不賦予子女訴訟權利,則既不符合憲法對公民人格權的保障,也不符合聯合國兒童國際公約的要求[1],更阻礙了子女獲知其真正的血統來源,在子女的訴權中,可參考德國民法第1600a條第三項之規定:“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子女,由其法定代理人行使其婚生否認權。”來防止未成年子女負擔家庭破碎的重責,又可依第1600b條第三項之規定:“若法定代理人并未及時替該未成年子女提起婚生否認之訴時,其可于成年之后自行提起之,且該兩年之除斥期間,自子女知悉其不為夫之血統時起重行起算;若子女于成年前即已得知,則自成年時起重行計算”來賦予子女是否提起婚生否定之訴的選擇權,來保護子女對自身血統真實的追求。
至于當父母身為法定代理人時可能與子女產生利害沖突,則應有兩種情況:其一是子女欲提而父母不欲提,當然可從成年后自行提起而獲得救濟,自不必多言,但若是子女不欲提而父母欲提如何?筆者建議將司法機構審查納入到該種情形之中,在此種情況下,法庭應酌情判斷何為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決定是否駁回父母的訴訟請求。[2]
(3)血緣生父的訴權
第三人如子女之生父,是否得以介入已因婚姻而受推定之親子關系,在家庭保障的考慮下一直被謹慎處理,甚至全盤否定其具有婚生否認之訴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當子女與其法律上之父親(即經婚生推定之父親)已不存在所謂的社會生活關系,彼此也無實際共同生活與撫養關系時,此際家庭生活的保障優先于血統真實主義之正當性即不存在,則應給予生父以第三人之身分介入家庭之機會,換言之,當無家庭保障之必要時,生父始得請求權。此舉一來可確保該子女于婚生否認之訴勝訴后,仍有生父替補成為法定父親,不致使其失去扶養之依靠;二來生父必須于該家庭無實質存在時方得提起婚生否認之訴,亦不會破壞原先法律在婚生制度中所欲保障的家庭。
筆者認為,自親屬法的角度來看,以婚姻安定、家庭和諧及子女受教養權益為由,并輔以不宜揭發他人婚姻隱私及自己不法行為,否定生父之婚生否認權,是合理的,但在上述理由歸于消滅是,完全否定生父之訴權將喪失其正當性。此時保障婚姻家庭之客體已不存在,而子女之利益與生父所建立之家庭,實應優先受到保障。故在此情形,宜允許血緣生父得提起婚生否認之訴。但有學者指出,雖認可生父之補充性訴權,但仍應防止權利濫用之情形,特別在子女成年后,且家庭生活關系因父母婚姻解消或推定父親死亡而消滅時,應禁止未盡扶養責任之生父,透過婚生否認并認領該子女,以巧取受子女扶養之權利[3],筆者認為有其一定道理。
3結語
我國《婚姻法解釋三》僅僅規定了夫妻雙方才有婚生否定訴權,可能會在來婚姻家庭形式日趨多元化之下面臨挑戰,原本為了保護家庭利益的法律,可能最后反成了子女利益保護的絆腳石。這在現代親屬法確立以子女本位走向后,對于子女利益在婚生否認制度的實踐中亦不應忽視。希望在我國未來婚生否認之訴制度修正之時,學界可以借以思考。
參考文獻:
[1]鄧學仁,論否認子女之訴與真實主義—評釋字第五八七號解釋,月旦法學雜志,第121期,2005年?
[2]戴瑀如,血緣?家庭與子女利益-從德國立法之沿革探討我國民法上的婚生否認之訴,東吳法律學報第二十卷第二期?2008年?
[3]許勻甄,子女血緣認知權在親子法上實踐之研究─以死后認領為中心,國立臺北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7月?
注文:
1聯合國兒童國際公約第7條
2參考德國法,第1600a條第四項之規定,當父母以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提起婚生否認之訴時,應于訴訟程序中由家事法院依子女之最佳利益進行審查,方得為之?
3鄧學仁,論否認子女之訴與真實主義—評釋字第五八七號解釋,月旦法學雜志,第121期,2005年,2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