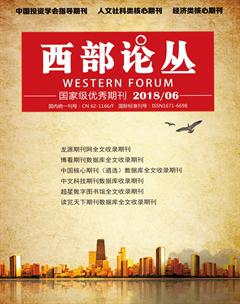從“到此一游”中探尋題壁、詩詞與書法藝術
摘 要:“到此一游”是中國傳統“題壁文化”在當代社會中的一種現象遺存。文人借文字的形式記錄旅途見聞,題寫于壁板之上,尋求心靈的寬慰。時至當代,大多數的人已不在學習傳統國學、古典詩詞也鮮有人作,然詩詞、題壁文化與書法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
關鍵詞:到此一游;題壁;詩歌;書法
在題材的表現上,詩詞與書法藝術的結合是中國古典藝術特有的形式之一。在題壁文化中,大多以書法題寫詩詞的形式表現出來。詩詞與書法都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粹,書法中,以神韻的灑脫、飄逸、自然為上,詩歌中,以神韻的和諧、暢然,舒適為美。無論是題壁文化、詩歌還是書法,都在時代的審美風尚中趨同性的成長演變與衰弱。
1題壁文化的發展演變與書法
據現存的文獻資料來看,題壁文化起源于兩漢,漢代書法家師宜官是最早的可考的題壁實踐者:“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而師宜官為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灑直,計錢足而滅之。”通讀文獻可知,師宜官所題為酒肆之壁,師宜官所寫字體,應為隸書。魏晉時期經過漢代藝術的自覺,書法的字體已基本完備,行草書經王羲之、王獻之的開拓演變,開啟了今草的時代,與題壁文化的發展相承接。文獻中: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凈,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此時,所書字體已不是端莊嚴謹的隸書,而是更為性情流利的行草書。
題壁文化在唐代實現了大發展,儼然成了文人書寫的一部分,據統計當時題壁詩的作者有百十數人。可以說,墻壁書法的發展對文化、詩詞的交流可謂功不可沒。題壁書法的盛行使得草書得以發展并與實用性的書寫技能分離,更注重展示藝術個性與魅力。如:“張長史則酒酣不羈,逸軌神澄。回眸而壁無全粉,揮筆而氣有余興。”。而懷素題壁時又是另外一種狀態:“援筆掣電,隨手萬變。酒酣興發,遇墻壁衣服器皿靡不書之。”懷素繼承和發展了張旭的草書,又把禪佛之學熔鑄到作品之中,為僧人書法的意境美和宋代尚意書風的形成奠定的基礎。
唐末五代的書法家楊凝式有題壁的癖好。《翰墨志》中云:“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在洛中往往有題記,平居好事者,并壁畫,置坐右,以為清玩。”宋代文人題壁也蔚為大觀,大書法家蘇軾、黃庭堅、米芾等人也多有題壁的事例流傳。在題壁文化中,題壁詩作為一種非主流的載體,隨著宋代印刷業的興起,逐漸衰弱,雖然明清兩代也有文人墨客的題壁詩流傳,但與之相伴的文藝作品,明清市井小說已經不適合題與園林山水之間。
文人的身份使得騷人墨客的題壁詩流傳下來,而題壁文化的發展與書法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在當代的題壁文化中,涌現的更多的是“某某到此一游”等帶有惡俗、不文明的因素的題壁現象。與前人相比,電腦及當代信息化自媒體時代已擺脫了毛筆題壁的局限性,文明的趨同性向著所有的當代人敞開,蘊含在題壁文化中的人文關懷、傳統士人的野逸的趣味也漸行漸遠。
2詩歌的發展演變與書法
書法與詩歌同屬于精英文化的范疇之中。縱觀書法、詩歌發展史,不乏既是書家又是詩家的人存在。漢魏晉時代是中國書法的第一座高峰,甲骨文書法已經形成了獨特線條美、章法美,如《祭祀狩獵涂朱牛骨刻辭》自然瀟灑富有變化;《大盂鼎》體勢嚴謹,布局質樸平實;《毛公鼎》則充滿了理性的張力;而這一時期的詩詞,主要是以《詩經》為代表。這些書法風格,在《大雅》《小雅》中都有體現。
隸書是漢代普遍使用的書體,代表性作品是東漢的隸書。在現存的百余種漢碑中,風格各異,琳瑯滿目,有大氣磅礴者,亦有婉轉可愛者。與之平行的是漢樂府,內容上繼承《詩經》現實主義傳統,語言更為樸素自然活潑生動。魏晉時期,既有方圓兼備的北碑,又有妍麗秀美的二王書風,這一時期的“建安風骨”追求是內容的充實與作品的抒情性;正始文學繼承了建安文學的優秀傳統,或沉郁艱深,或風調峻切等。在發展上,書法與詩歌有如此的相似性,所以有人說:觀南朝詩風,如觀魏碑體。
隋唐是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唐楷講究的是中正與法度,是書法藝術標準的極致;而唐朝的律詩發展也漸至頂峰。此時的書法藝術和詩歌藝術,在審美趨向上有著一致性。與此同時,作為楷書極致對立面的狂草也由張旭和懷素推至頂峰;癲張醉素以狂放不羈的態度,追求書法內在的意境和精神,在審美境界上獲得了突破。
五代之際,在書法上值得稱道的,當推楊凝式。此外,還有李煜、彥修等有兼有詩詞成就的書家。宋代蘇軾、黃庭堅既是江西詩派的代表,又是當時的一流書家,在藝術審美中,向著“理”和“意境”的追尋。如蘇軾的《黃州寒食詩帖》、黃庭堅的《花氣熏人帖》、等本身就是很有意味的詩文。
唐代以前是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壯大期,樸拙渾厚;唐代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期,直抒胸臆百花爭艷;宋代是中國詩歌的轉型期,意境的追求和理的思辨;宋代以后則是中國詩歌的繁盛期,流派繁多,然終未能突破原有的詩歌模式;字體的演變至唐代達到了法度精研的地步,楷書、行書、草書發跨入了一個新的境地,開始了向著意境、筆墨趣味方向改變,與詩歌的發展亦步亦趨。
在當代展覽中,詩詞作品的韻律感更符合視覺藝術的審美需求,也更容易使書寫者受到感染,從適意書寫中與古人交流,心手雙暢。其次,是詩詞作品本身意韻豐富,用筆墨的形式展示出來,更貼近與書齋式的書法創作,賞詩賞書各得其宜。再次,即使當代書家不學格律、不寫詩詞作品,潛藏在書家性情中的“詩性”是無法拋開的。在詩性的思維模式中所建立的中國傳統文藝審美范疇,也在影響著書法藝術的審美格調。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詩詞和書法一千多年來相隨相伴,不曾廢離,但與前人相比,書法中,少了些厚重,多了些輕浮與喧囂。
參考文獻:
[1]《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頁,見衛恒《四體書勢》
[2]《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頁,見虞龢《論書表》
[3]《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版,第256頁,見竇臮《述書賦(上)》
[4]《古籍資料的復印本》,第34頁,見盛熙明《法書考》卷3書譜
[5]《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版,第371頁,見趙構《翰墨志》
作者簡介:寧方偉,男,1992年2月,民族:漢,山東泰安人,碩士學位,云南藝術學院,研究方向:當代藝術與批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