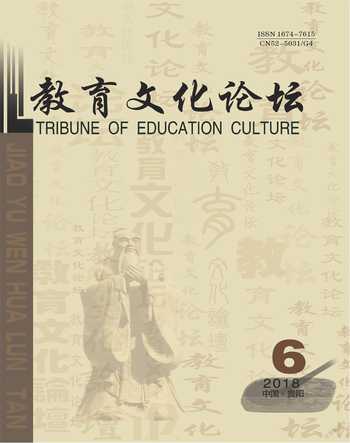知行合一:人類學視野下的教育思考
摘 要: 自社會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之后,人類學開始要求研究者到研究的地方去做深入的調查探索,是為田野研究。從摩爾根到本尼迪克特,再到中國近代以來的種種調查研究,可謂歷來有之。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人類本性的回歸。田野研究不僅僅是一種研究方法,更是一種嘗試對人的本真生活還原的研究范式(paradigm)。通過自我對生活本真的體驗,給人們傳達出一個真善美的世界。它雖然沒有明確說出形如教育界宣揚的知行合一,但無往而不在踐行著知行合一理念。從某種意義上講,教育應該適當向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看齊。因為教育從本真的生活中來,也應該鉆進本真的生活中去。可時下的教育似乎和這種生活風馬牛不相及。教育正在脫離我們的生活世界。
關鍵詞: 人類學;田野研究;知行合一;教育思考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615(2018)06-0041-04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8.06.008
人類學(anthropology)作為一個名詞,起源于古希臘文,由ανθρωπο(族體、民族)和λογο(科學)兩個詞合成而來,主要致力于民族共同體相關方面學問的研究,一度也譯為“民族學”。古希臘三哲之一的亞里士多德在論及具有高尚道德品質及行為的人的時候,第一個對該詞作了描述,潛在的賦予了人類學以道德的寓意。英文ethnology、法文ethnologie,德文volkerkunde,都是民族學的意思。英國的“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美國的“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和當前合稱的“社會文化人類學”(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 ),無論從研究對象和范圍來說,都基本上等同于人類(民族)學,彼此間也經常互相通用[1]1。人類學從字面上理解就是有關人類的知識學問,是研究人的學科。“人類學是研究人性與文化的學問,無論從人本的出發點,還是從不同地理區域的族群生活方式的理解考慮,人類學都處在探索人類與國民未來發展的基礎理念的重心之中”。[2]
一種使命:人類學與田野研究
人類學在一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許多流派。不管是哪一個流派,其理論都不是空中樓閣,都要建立在大量材料的基礎之上。這些材料,不同于一般的文獻,也不同于自然學科中的實驗獲得的數據,它必須通過田野研究(fieldwork)的方式來取得。有學者就說:“大約在20世紀初期,人類學家開始意識到,如果想要創造出任何具有科學價值的研究成果,就必須像其他科學家研究他們的對象那樣來研究自己的對象——即要系統地進行觀察。為了更準確地對文化進行描述,他們便開始同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他們觀察,甚至參與那些社會的某些重要事務,并向土著詳細詢問他們的習俗。換句話說,人類學家開始了田野工作。”[1]150在這些人看來,沒有田野研究或者田野研究不過關,就不是一位合格的人類學者。
田野研究是人類學研究工作賴以生存的法寶,就其研究的空間、時間和內容而言,呈現出三個特點。
一是從空間上看,具有跨空間、跨區域的研究特性。它需要研究者跳出既有的地域,深入到異域中去做詳細的調查研究,因此,人類學也被稱為是對異文化或他文化的研究。這種方式也增添了人類學的浪漫氣息,使得研究者看起來像是獨行者,又像一個孤獨的旅行者。他們要去往某個遙遠未知的地域,經歷不同習俗、文化等帶來的考驗與“磨難”。
二是從時間上看,具有長期性、歷時性和共時性的特性。長期性指的是田野研究需要較長時間進行,一般認為,理想的時間閾限至少應有半年以上;歷時性指的是在實際研究過程中,研究的內容(如文字記載、家譜或族譜、口述歷史、文化交流等)在時間上呈現先后順序、多點交叉的跳動現象,研究者需要做好記錄,適時重構“歷史”;共時性指的是在同一時期內,研究的內容包括調查文化的結構、功能或象征意義等呈現出靜態分布,需要研究者理清因果關系和期間的邏輯意義。
三是從內容上看,具有紀實性、多樣性特點。紀實性指的是用自然的形式描摹研究對象的原貌,突出客觀、真實。多樣性主要指內容的呈現方式和風格,可以以記敘、散文、小說等形式呈現。目的在于通過不同的記錄方式觸發人們在文化、文明、精神、道德等方面的沖擊。瑪格麗特·米德在研究薩摩亞人的青春期問題時記錄的的一段內容具有典型的代表性:“1967年,我回到了闊別29年的塔布南村(Tambunam),這個村莊位于新幾內亞境內的沙比克(Sepik)河畔。文明通過各種途徑影響著這個村子。雖然當時教會已獲準進入村中,為孩子們提供學校教育,但宗教儀式仍被明令禁止;雖然戰爭已經停止,首長們已經遷居它處,但土著居民們仍然喜好建造那種他們自認為漂亮的房屋,生產西(谷)米,并且還是用老方法捕魚......但是,請不要忘記,那些耗費金錢、時間,創造出妙手回春的奇跡的醫生卻往往是些對現行的軍事政策從無抵牾的人。在這種政策的指導下,每天都有大批的無辜者投身沙場。每一年里,汽油彈燒傷的兒童遠遠多于施里納醫院所拯救的兒童。當我們一旦領悟到這點,誰的心靈能不為之震顫?‘人類就因此而墜入深淵,難以自拔嗎?每一個人都被迫捫心自問。”[3]
基于這些緣由,人類學研究者在研究歷程上總是飽受情感、健康的困擾,并與孤獨寂寞相伴,時常遭遇文化的沖擊和震撼,還會時不時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困境。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和特羅布里恩島考察期間寫就的《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其中的一段文字對此作了生動映照:
“4月7日(1918年)。我的生日。我還是帶著照相機工作,到夜幕降臨,我簡直已筋疲力盡。傍晚我與拉菲爾聊天,談到特洛布里安德島人的起源和圖騰制度。值得一提的是,與拉菲爾這樣的白人交往(他還算是有同情心的白人)……我困惑,我陷入到了那里的生活方式之中,所有一切都被陰影籠罩,我的思想不再有自己的特征了,與拉菲爾對話時,我的想法總要在價值觀上發揮。所以,星期天的早上,我去四處走了走。到10點才去土烏達瓦,給幾條小船拍了幾張照片……”
馬林諾夫斯基在生日當天,用灰暗的筆調寫下了上述的內容,這樣的情愫很可能源自其長期以來與土著民族中做實地研究過這樣的生日,實在寂寞、無聊,令人困惑。縱觀國內外人類學者的人生軌跡不難發現,在他們眼中,田野研究帶來的種種憂郁和不快,并非一文不值,反而正是他們對于人類學理解能力的發揮,在極端陌生和惡劣的環境下,體會人的生活的本來面貌,是對人性一種莫大的熱忱與關愛,因為這些很有可能是盧梭筆下人類僅有的接近自然狀態下的本真的人類原型。它似乎要從野人生活出發,向著極樂世界探尋,尋求人類的“真善美”的價值。恰如亞里士多德所言:“人的每種技藝與研究、實踐與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的。所以有人就說,所有事物都以善為目的。”[4]這也是人類學的一項使命。
知行合一:道德意識和道德踐履
人類學的研究使命和研究方法,某種意義上是要從人的體質和文化方面將人帶進人類的原型中去,思考人類存在的原型以及終極生命價值意義。它要將研究者從書齋捉到田野中去,把做學問的態度從椅子上解放出來。它要以“動”制“靜”,區別于其他的學問態度和方法,在“動”的過程中參與和觀察,以此獲取研究所需要的第一手材料,得到新的認知,并根據自身的知識結構,通過民族志的撰寫,來理解和解釋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學研究要求人們知行合一。
明朝思想家王陽明在對傳統儒家思想的理解和加工基礎上,開辟了“知行合一”的境界。 暗合于亞里士多德,在他看來,“知行合一”并非一般意義上的認識和實踐的關系,其間也融合著深沉的道德底蘊。“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識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因此,知行關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踐履的關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實際行動的關系。“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人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5]中國古代哲學家認為,不僅要認識“知”,尤其應當實踐“行”,只有把“知”和“行”統一起來,才能稱得上“善”。把善作為知行的最高目的,這與亞里士多德和中國《大學》里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大學》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6]這種追求和人類學對人的研究的終極意義是一樣的。“一般不專精人類學的人,往往以為人類學只是一種研究人類種族問題和文化研究的學問,在實用,只在開發邊疆和使淺化部族開化這類工作上有所貢獻。這是一種片面的看法。”[7]人類學在某種程度上肩負著一種道德的責任,通過理論和實踐的共同參與,以期盡可能接近事物和人類的“本真”與“至善”,達成美好生活的愿望。
這頗有點類似中國儒家里說到的經世致用哲學。《辭源》中對“經世”的解釋為:治理世事;“致用”為:盡其所用。《辭海》的解釋為:明清之際主張學問有益于國家的學術思潮。因此,經世致用要求人們要關注社會現實,用所學之識來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現實問題,已達成傳統儒家的修齊治平的理想。當然,也有人認為,經世致用的思想也從側面反襯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調和功利、求實、務實的倫理價值上所作的努力,以期圓潤出“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
實際上,從先秦起,一大批思想家就已經在踐行著“經世致用”的理念。譬如孔子的儒家思想,其本身就是一種入世哲學,夫子周游列國,談經論道,目的就是要在那個禮崩樂壞時代,修復應有的社會秩序。孟子更是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的這一愿望:“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8]
經世致用學者比較實事求是,重調查研究。在這方面,明清時的一大批文人學者皆可為其代表。顧炎武顯示是那個時代備受推崇的典范。在全祖望《魚土亭集》卷十二《顧亭林先生神道表》中:“凡先生之游,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他遍游北方,心懷探討“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的目的,歷經“一年之內半宿旅店”和“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用畢生之力,研究“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為泥古之空言”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規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的《日知錄》等名著。無獨有偶,地理學家顧祖禹則“舟車所往,必覽城廓,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 這種調查研究之風,在清初學者中比較盛行,成為清初學風的一大特點。足以為中國學者作出表率,給教育以莫大啟示。
一種思考:人類學視野下的教育味道
人類學研究除了倡導田野研究,還要求進行民族志的撰寫和文化理論的建構,做到知行合一。這既是一種學問態度,也是一種道德責任追求。它要從人類的起源和文化生活的根上將人和生活給拿出來,放在日益浮躁的現代社會,重新進行一番審視。這是歷史,也是文化的責任。它要還原某些真實的東西,要求人們敢于面對人性的虛偽,兇惡,丑陋,而目的卻是奔著“真善美”而去。
今天的教育同這些似乎越來越遠了。人類學研究中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寫在教育領域里看來,近乎是“海客談瀛洲”般的飄渺難求。老師們坐在書齋里對教育侃侃而談,學生們坐在教室機械接受。學校將大門封鎖起來,學校是學校,老師是老師,學生是學生,家長是家長,農民是農民,彼此世界沒有什么關系。師生之間早就沒有了孔孟與學生之間的那種關系了。老師和學生的稱呼僅是一個頭銜,一門職業,一份工作而已,甚至異化為經濟關系。老師按時上下班,學生也按時上下班。你過你的生活,我過我的生活。老師們再也不會像陶行知先生那般關注自己的學生“會不會燒飯種菜”,學校也不會有這樣看似“荒謬”的規定:“不會種菜,不算學生,不會燒飯,不得畢業”。[9]究其根本,大概是缺乏對人的一種本真體驗以及對生活的本真體驗,缺乏一種人類學的勇氣和使命感。更深層的,或許是缺乏對人性倫理和道德的基本責任與擔當。
人們對現在教育理解得似乎過于狹窄,教育看起來僅僅是在學校中的“教”和“學”的關系。老師負責教,學生負責學。像工人操縱機器一般,單調而機械。學生看起來只是一件產品,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教育沒有像人類學那般設身處地,身臨其境的感覺。沒有人的味道在里面。
然而,最初的教育并非如此。在西方,教育一詞源于拉丁文educare,意為“引出”或“導出”,意思是通過一定的手段,把某種本來潛在于身體和心靈內部的東西引出來。這與先哲蘇格拉底的“產婆術”如出一轍。最終意在引出善,并把善作為最高的目的。[10]但是,我們的教育一方面忘卻了蘇格拉底教育的本真目的,另一方面也忘卻了蘇格拉底進行教育的方式。蘇格拉底說,“未經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在進行教育之前或是教育的過程中,蘇格拉底從未將之閑置。在他看來,教育是一種靈魂的轉向,是引導人自我發現真理的過程,思想的澄清通過教育的對話顯現。不是通過世俗的物質的方式,而是要透過理性,審視人的生命的終極需求,從而引導出一種新的生活態度。因此,教育者必須要親身出馬,審查自己和受教育者。回望蘇格拉底一襲單衣,穿梭于雅典的大街小巷當中。再看孔子風塵仆仆,來往于各個諸侯國之間。他們都是教育的集大成者。為何幾千年過去了,教育當中再也沒出現這樣的人物,這足以讓后人反思檢討。誠如陶行知所論述的教育:“它教人離開鄉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它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11]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人類學的研究方式和教育本來的味道是相近的。人類學與教育都應該要求研究者將自己的衣食住行融入到研究對象的生活當中,知行合一,然后嘗試著發掘出人類的本真面貌,還原出生活的真實滋味。它融道德意識和道德踐履為一體,同時肩負著一種道德責任,那就是尋求真善美的生活。教育和生活不是水與火的關系,而是水乳相交的關系。教育從生活中來,也應該鉆進生活中去。
參考文獻:
[1] 林耀華.民族學通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1.
[2] 莊孔韶.人類學通論[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3.
[3] 〔美〕瑪格麗特·米德.文化與承諾[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8.
[4]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廖申白譯.尼各馬可倫理虛[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3.
[5] 杜就田.王陽明全書(一)[M].上海:上海東方書局,1935:38.
[6] 王國軒.大學中庸[M].北京中華書局,2006:3.
[7] 〔美〕弗蘭茨·波亞士,楊成志譯.人類學與現代生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2.
[8] 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8:82.
[9] 方明.陶行知名篇精選教師版[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51.
[10] 周杰.文本的出世與僭越——從詮釋學視角看教育的文本化[J].現代中小學教育,2012(06).
[11] 方明.陶行知名篇精選教師版[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45.
(責任編輯:涂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