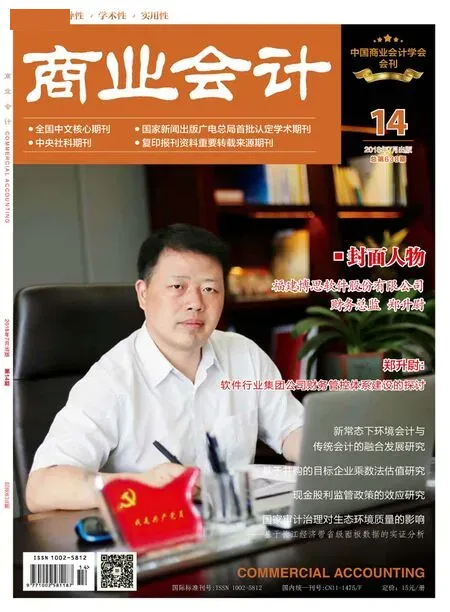國家審計治理對生態環境質量的影響
——基于長江經濟帶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南京審計大學江蘇南京211815)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為打造更美麗、更宜居的家園,治理生態環境問題刻不容緩。國家審計是國家治理的基石和重要保障,對生態環境也會產生重要影響。本文主要從國家審計方面入手,探討國家審計治理作用于生態環境質量的途徑。通過構建國家審計治理的相關指標、建立相應的函數關系和計量模型,揭示國家審計治理對生態環境質量產生的影響。
一、國家審計與生態環境文獻綜述
(一)國家審計相關研究
王孜(2016)提出,政府審計治理水平越高,越容易揭露高管的腐敗行為。王會金、戚振東(2013)認為,國家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國家審計。上官澤明、吳秋生(2017)指出,通過構建國家審計治理能力評價指數,可以更好地對其作用進行衡量。張世鵬(2015)認為,應通過國家審計的本質及審計風險的相關概念研究、國家審計風險的影響因素及機理分析、基于結構方程的國家審計風險影響因素實證檢驗,來對國家審計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李鳳(2018)提出,供給側改革及經濟新常態等對國家審計提出了更高要求,應對國家審計進行準確定位,并考慮國家審計新的路徑機制。唐琴珠(2017)提出,大型國企是我國經濟的重要成分之一,對其進行審計監督,減少違法亂紀等不良現象,不僅可以促進其自身的發展,還可以對其他企業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使市場秩序更加井然有序。蔡高銳、白皓冉(2018)指出,應以INTOSAI為視角,探索國家審計提升我國財政透明度的路徑。胡耘通(2017)認為,在現階段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背景下,國家審計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審計治理作為審計機關服務黨和國家監督的重要手段,還存在不足之處。馬軼群、崔倫剛(2016)提出,國家審計的著力點是通過對金融機構和金融監管部門的兩方面審計,對監管套利行為、套利空間以及套利根源進行監督,最終實現穩定金融和防范風險的目的。唐大鵬、李鑫瑤(2015)認為,國家審計會成為權力運行內部控制構建的主要外部推動因素之一。汪德華(2016)認為,在供給側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宏觀調控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的國家審計,也應該適應市場潮流,開展創新,以促進經濟更好發展。陳信賢(2017)認為,政府性債務風險的預警、控制較為困難,可以將審計相關理論貫穿其中,以實現對風險的有效控制。歐文勝、李玉英、劉偉(2013)認為,本質上,國家審計就是保障國家經濟社會健康運行的“免疫系統”。金晶(2017)基于“壓力-狀態-響應”(PSR)模型,研究了環境和環境政策審計之間的關系。王素梅(2014)提出,從財務審計跨入合規審計,最后向著績效審計邁進,是環境審計的必經之路。
(二)生態環境相關研究
郭榮茂(2017)認為,完善生態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制度是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一環,要求制度創新和多元化的社會主體參與到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來,以加強對信息的監督與反饋,從而更好地為進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保障。王芳、黃軍(2017)認為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生態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樣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維度。李周(2001)認為,為改進生態環境治理,應最大限度地減少項目實施中的依附關系,不僅有利于提高上述工作的質量,并能保證其客觀公正性,還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項目評估中的信息不對稱。黎明、李春華、楊寶(2015)認為,生態環境具有外部性,必須借助外部力量平衡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活動,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田千山(2012)認為,面對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無論是采用市場調控模式,或是政府強制模式,或是企業自覺模式對生態環境問題加以治理,在運行一段時間之后,都會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多元共治模式即三者聯合則會產生新的局面。
綜上所述,我國學者對于生態環境治理已提出了很多解決方案,國家審計也已進入了較為成熟的發展階段,但關于國家審計環境治理方面的研究還比較滯后。首先,對于國家審計環境治理研究的系統性不足。其次,對于國家審計環境治理基礎理論的研究較少,現有研究比較側重于對應用方面的研究。第三,缺乏完善的國家審計環境治理理論和規范的國家審計環境治理方法。是否需要對環境事項予以關注并實施必要的審計程序依賴于審計人員的職業判斷,加大了審計人員實施國家審計環境治理的難度和風險,使得國家審計環境治理的實施效果大打折扣。最后,國家審計環境治理缺乏科學、合理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本文認為,為了更好地解決生態環境治理問題,應將國家審計與生態環境治理進行更好的結合。
本文選擇了與國家審計直接相關的四個指標:審計執行能力、審計處理處罰能力、審計矯正能力、審計協作能力,盡量涵蓋國家審計治理的各個方面。此外,還引入了外資引進水平、城鎮化水平、研發支出三個指標。這三個指標與國家審計治理不直接相關,但與環境質量有關。將這七個指標與生態環境質量建立起函數關系,并進行變量的分析說明。最后與實際相結合,探討國家審計治理對生態環境質量的影響及途徑,并提出相應的結論和建議。
二、計量模型及分析說明
(一)計量模型及相關變量
本文建立的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i為省份,t為年份,EN為各省的生態環境質量水平,FWZ為各省的外商直接投資水平,URB為各省的城鎮化水平,RD為各省的研發支出,SJZX代表國家審計執行能力,SJCF代表國家審計懲罰能力,SJJZ代表國家審計矯正能力,SJXZ代表國家審計協作能力,α為常數項,θ1—θ7為各變量的參數估計值,ξ為隨機誤差。下面詳細介紹各變量的含義及構建過程。
1.生態環境質量(EN):與生態環境質量直接相關的主要是工業廢水、廢氣及煙塵的排放量、城市綠化水平,故本文以市轄區工業廢水排放量(萬噸)、二氧化硫排放量(噸)、工業煙塵排放量(噸)和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來衡量生態環境質量,并對數據進行處理:先區分生態環境質量中的正向指標和逆向指標,然后進行標準化處理;再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生態環境質量的綜合指數,該指數越大,說明生態環境質量越好,反之亦然。
2.外資引進水平(FWZ):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單位:億美元),并按當年匯率換算成人民幣(單位:億元)。
3.城鎮化水平(URB):各省市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
4.研發支出(RD):各省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R&D活動經費支出額(單位:萬元)。
5.審計執行能力(SJZX):因難以獲取審計實施情況的具體信息,長期以來國家審計機關都將查出的問題金額作為審計實踐的重要成果(宋常等,2006)。審計機關披露的問題金額與審計工作執行能力成正比。故本文采用審計機關查出的違規金額數量作為審計執行能力的替代指標。
6.審計處理處罰能力(SJCF):本文參照朱榮(2014)的方法,使用審計機關做出的審計處理處罰金額與查出的問題金額的比值來衡量審計處理處罰能力。
7.審計矯正能力(SJJZ):本文根據李江濤等(2015)的研究,采用違規違紀金額處理率來表示審計矯正能力。違規違紀金額處理率是指已上繳財政金額、已減少財政撥款或補貼的金額與已歸還原渠道資金之和與審計機關查出問題金額的比值。
8.審計協作能力(SJXZ):本文以審計機關提交的審計報告 (建議)和審計信息被采納的比率來測度審計協作能力。國家審計機關提交的審計報告和相關信息被相關部門采納的比率越高,則國家審計機關的審計成果獲得相關部門協作與配合的力度就越大,反之則越小。
本文以2005—2013年長江經濟帶1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為樣本,數據主要來源于2006—2014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以及《中國審計年鑒》。《中國審計年鑒》能找到的比較完整的最早數據為2006年版,報告的是2005年的數據;目前《中國審計統計年鑒》只出版到2014年,報告的是2013年的數據。用于基期調整的價格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上頁表1為長江經濟帶11個省份生態環境質量和其他變量及相應統計量的數據。

表1 長江經濟帶11個省份生態環境質量及其他變量的樣本統計值
(二)計量模型估計結果及變量的解釋說明
1.計量模型的選擇。選擇合適的面板數據模型進行估計是進行計量估計的首要任務,本文使用長江經濟帶11個省份2005—2013年的面板數據進行估計。對包括城市和年份的固定效應方程進行F檢驗,其概率估計值為0.0000,小于固定效應假設下的F檢驗相伴概率,即拒絕原假設,證明為固定效應模型;接著進行LM檢驗,LM檢驗的相伴概率為0.0000,小于臨界值,故模型存在隨機效應。最后,Hausman檢驗顯示,伴隨概率為0.0000,無法通過隨機效應原假設,即應將固定效應計量模型應用于方程。
綜上,方程的估計應采用固定效應面板模型。表2為模型檢驗相關數據情況。

表2 計量模型檢驗結果
2.樣本的計量估計結果與分析說明。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計量估計,可以分析國家審計治理對城市生態環境質量的影響。分別將四個指標引入方程,看這四個指標的估計結果,并將四個指標全部引入方程,再看結果的變化情況,判斷和檢驗結果的穩健性,共計五個模型如表3所示。表3列出了外資引進水平、城鎮化水平、研發支出、審計執行能力、審計處理處罰能力、審計矯正能力、審計協作能力對城市生態環境質量影響的面板綜合估計結果。為了排除國家審計治理影響的融合性,確保結果的準確性,表3中也展示了單個國家審計指標對生態環境質量的數據結果。

表3 各變量對長江經濟帶11個省份生態環境質量影響的面板估計結果
從模型一中t絕對值的大小可以看出,外資引進水平、城鎮化水平、研發支出、審計執行能力、審計協作能力指標的估計值都不顯著,未通過檢驗,說明對生態環境質量的影響不顯著。而審計處理處罰能力的t值為3.49,在1%的水平上顯著,對生態環境質量有影響,且發揮正效應。即審計處理處罰能力每上升1%,生態環境質量上升1.0969%。審計矯正能力的t值為-2.35,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對生態環境質量有影響,且會產生抑制作用。即審計矯正能力每上升1%,生態環境質量下降3.3512%。在綜合作用下,審計處理處罰能力對生態環境質量的影響為正,且大于其單獨發揮作用時的影響。審計矯正能力對生態環境質量會產生抑制作用,且抑制能力強于其單獨對生態環境質量發揮正效應時的影響能力。
從模型二可以看出,各變量指標的t絕對值均小于1.68,不在合適的區間范圍內。可以推論出外資引進水平、城鎮化水平、研發支出、審計執行能力這四項指標對生態環境質量的影響不顯著。
從模型三中各指標的t值可以看出,外資引進水平、城鎮化水平、研發支出指標對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作用有限。僅審計處理處罰能力的t值為3.48,在1%的水平上顯著,對生態環境質量產生了正面影響,即審計處理處罰能力每上升1%,生態環境質量上升0.4557%。
從模型四可以看出,外資引進水平、城鎮化水平、研發支出指標的t值都不符合相應條件,即對生態環境質量的影響不顯著。審計矯正能力的t值為1.96,在5%的水平上顯著,對環境有影響,且產生正效應,即審計矯正能力每上升1%,生態環境質量上升1.2368%。
綜合模型三、模型四可以看出:在審計處理處罰能力和審計矯正能力單獨存在、不產生相互影響的情況下,審計處理處罰能力和審計矯正能力均對生態環境質量產生正面影響,且審計矯正能力的影響頗為顯著。
從模型五的t值可以看出,外資引進水平、城鎮化水平、研發支出、審計協作能力指標的t值都不符合條件,即不顯著,對生態環境質量的作用有限。
實際中,審計處理處罰能力和審計矯正能力一般是并行的,所以本文主要考慮生態環境質量在兩者綜合影響下的結果。模型中,審計處理處罰能力指標值越大,對生態環境質量的促進作用越強,環境能得到改善的效果也就越強;審計矯正能力指標值越大,審計實際上對費用金額的處理程度越高,生態環境質量反而會受到負面影響。
三、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主要結論
本文通過對長江經濟帶11個省份2005—2013年的生態環境質量指標及七個國家審計治理相關變量建立函數關系和五大模型,分析國家審計治理對生態環境質量的影響。其中,審計指標有四個(審計執行能力、審計處理處罰能力、審計矯正能力和審計協作能力),其他指標有三個(外資引進水平、城鎮化水平、研發支出)。通過面板數據研究分析,得出結論:總體而言,七大自變量指標對生態環境質量的影響不同,外資引進水平、城鎮化水平、研發支出、審計執行能力和審計協作能力對生態環境質量的影響不顯著,只有審計處理處罰能力和審計矯正能力對生態環境質量有顯著影響。與審計無關的三個指標雖然對經濟水平的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但對生態環境質量的影響較微弱,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審計處理處罰能力作為一種對破壞環境行為有抑制作用的能力,處理行為越及時、處罰力度越大,對破壞環境的因素起到的負面影響就越大,因此,模型中審計處理處罰能力對生態環境質量產生了正面影響。隨著審計處理處罰能力的提升,城市的生態環境質量也隨之上升。所以,這類指標需要著重提高。
與之相類似,審計矯正能力具有糾正違反行政法規等行為的作用,也對生態環境質量產生正面影響。同時,由于矯正注重防患于未然,而不像處理處罰能力一樣是被動因素,因此審計矯正能力的影響更為顯著。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一中,審計矯正能力對生態環境質量產生了抑制作用,且比審計處理處罰能力的影響更為顯著,可能是由于矯枉過正而產生了負面反彈效果。因此在實際操作中,審計人員要注意多采取矯正的方法,使實施對象易于接受。
(二)政策建議
建議加強審計處理處罰和審計矯正方面的法律規范建設,使審計機構及人員在執行審計過程中有法可依,提高正確性和效率。適當加大審計處理處罰力度,注意審計過后的矯正措施,注意上繳財政金額,防止矯正過度。控制已上繳財政金額、已減少財政撥款或補貼的金額與已歸還原渠道資金之和與審計機關查出問題金額的比值,提高審計監督效果,在拓寬審計思路上見成效。從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的要求中尋找審計矯正工作的切入點和著力點,正確處理好監督與服務的關系,為更好地確定矯正力度奠定堅實基礎。
加強審計信息化建設,運用現代審計手段,提高審計工作效率,提高處理處罰的及時性。大力加強計算機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引進、推廣審計軟件,利用模型計算應處理處罰金額,提高處理處罰的及時性,避免矯正過度,為提高審計工作效率和質量提供技術保障。此外應加大計算機審計的教育培訓力度,培養審計和IT技術相結合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