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選中的加藤嘉一
陳莉莉
2018年8月,他和《南風窗》記者約在北京的一個咖啡館見面。具體的時間和地點,他提前給出兩個備選,這是他與人約訪的習慣之一,讓對方有選擇。即便是盛夏,他仍西裝革履,提前到了約定地點。幾天后,他返回美國,他在社交媒體上說,“會回來的”。
這一年,除了《我所發現的美國》,他還有譯作《人間的命運—致巴金》,原作者芹澤光治良,2018年是其逝世的25周年,這是一位在日本享有盛名的小說家。
2003年,春天,北京。
天空是黃色的,沙塵暴剛剛來過。
一輛紅色夏利出租車停在走出機場的加藤嘉一面前,載他駛向中國知名學府—北京大學。
2012年,離開中國抵赴美國,學習、觀察與寫作。
在中國的近10年間,他從一個普通的留學生成為輿論場上的“青年偶像”,一時風光無兩,隨后因“假學歷”“否認南京大屠殺”等事件,光環逝去,新的標簽貼上來。相關爭議聚焦在他的身上,那年他28歲。
此階段的中國,草長鶯飛,發展迅猛,在浪潮中起起落落、快速升起又迅速滑落的,加藤嘉一并不是唯一一個。

他從小生活在日本伊豆的農村,家境并不優渥,所遇之事也并非都是良善,這些童年以及少年經歷,成為他在日后訴說自己擁有政治主張的原因之一。他希望自己能夠對社會秩序有所改善,而此正是政治所能為。
無論是當初從日本到中國,還是從中國到美國,以及在中國的經歷,日本青年加藤嘉一形容自己與每一段時光的關系是“被選中了”,有些“選中”花了他很多的運氣,有些“選中”讓他看起來像是“落荒而逃”。
“復雜性”
2012年8月,加藤嘉一一定會遠赴美國。這是2011年年底做好的決定。離開中國之前,有三所高校的演講要赴約,西安翻譯學院是最后一所。這是這一年的6月。
演講時,他想他可能會大哭一場。
哭什么呢?
他說,好像有一種預感。從2005年開始,尤其是2008年以來,他看起來享受著很高的關注度和話語權,似乎很歡樂,但是背后承受著各種壓力。“畢竟是個日本人。”
壓力很大,只是很多時候沒空消化。所以在離開中國前,他想給自己一個禮物,讓情緒得以宣泄。“各種情緒,快樂的、感謝的、暫別的、痛苦的。”
這場哭,提前到來,是自己一個人哭,他并沒有能夠到西安翻譯學院演講。
青海民族大學是三所高校演講行程的第一所學校。距離演講還有3小時的時候,他與陪同人員一起在西寧逛寺院。陪同人員告訴他說,出事了。他上了各大門戶的靠前位置,醒目標題是《加藤嘉一否認“南京大屠殺”》。在此前,他被認為是與中國青年偶像韓寒齊名,以正面的或者觀點性的文章出現在各大媒體上。
他腦袋一懵,心想:完了。
甘肅農業大學是演講計劃中的第二所學校,對方表態說活動取消了,西安翻譯學院也取消了。那天他改了行程,直接從西寧飛回上海,他在當天晚上起草并發表了聲明。
從“加藤嘉一”這個形象在中國公眾領域行走以來,這次事件是他整個公眾人物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危機。
加藤嘉一認為源于他把一切事情想得太簡單了。“言論確實很復雜,而且你是個日本人,本來就很復雜。”
發表聲明以后,可能有人原諒了他,認為他只是不成熟而已,他的立場、他的態度沒有問題。但,終歸也失去了一部分讀者。
當時中國改革開放給很多外國人話語空間,讓他們表達作為外國人的觀點,談談個人經歷。他正好處在那樣的時間點里,“但是當時的我肚子里真有那么多東西嗎?”
一個多月后,抵達哈佛時,肯尼迪學院有幾個中國干部對他說,加藤,你出來得真是時候。很多人都認為他因那場言論帶來的變故而離開中國,當時他還會去爭辯,后來就不再了。“我不怕被爭論。”
回想那段時間,他一直在思考,或者說反省。
當時中國改革開放給很多外國人話語空間,讓他們表達作為外國人的觀點,談談個人經歷。他正好處在那樣的時間點里,“但是當時的我肚子里真有那么多東西嗎?”他意識到他所享受到的追捧,實際上與他當年的閱歷、才華不匹配。“它有一個時代的特點,不是因為我的能力,也無關我的意愿,我也控制不了。”
在美國待了三年再回到中國出新書,做演講,加藤嘉一沒再遇到以前那樣受歡迎的擁擠場景。
在中國的時間里,加藤嘉一說,他真的認為自己是有使命的。“確實被那段時間選中了。總覺得如果自己不好好表現,中日關系可能會出問題”,現在回過頭來看,“很自以為是,但其實也很浪漫”。
很少再有哪一個年輕人會有這種天真爛漫的想法,覺得如果不好好表現,中日關系會惡化了。他這么想。
“就是偶爾會覺得有點對不起編輯。”
“國際人”情結
1999年,悉尼奧運會。
初三畢業的加藤嘉一去澳大利亞畢業旅行。其實他是不想去的,但是因為那筆旅行資金就像住房公積金一樣,陸陸續續一點一點存進去。“如果不去,也拿不出來。”
他是通過日本以外的澳大利亞,知道世界很大。當時對他來說,澳大利亞代表的是世界,也是西方,是先進,是文明。他覺得日本與西方的關系是吸收、學習,是知識增量的過程。而與中國就不一樣。從小學開始,語文課、歷史課、道德課,不同的課程中都需要學習與中國有關的東西,他認為對中國應是比較了解的,況且日本社會的每個角落都有中國古代的文化痕跡。但到中國以后,他反而覺得陌生。
高中時期,他不認為將來會去西方學習,學費太貴了,父親公司破產,家中兄弟姐妹多,而他是長子。高二開始,他開始打工,做貿易公司的英文翻譯工作,希望將來最好做一些跟國際社會有關的工作。
澳大利亞的場景起了作用。他想到聯合國工作。他看到幾個條件:一要有碩士學位,第二在聯合國的通用語當中要會兩門外語。中文、俄文、法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后來他發現去中國最便宜。
事實上,他讀北京大學,是免費的。他記得當時的校長把他叫過去說,你不是對國際社會感興趣嗎,要不要去北京大學?他很順利地到了北京大學,他當時覺得那一次把一輩子的運氣都用光了。
他對“國際”或者說“世界”有一種自己的執著。
因為個性,因為與眾不同,他說他小時候受到排斥。什么樣的排斥呢?“就是集體不理你。”當時他懷疑,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這樣的嗎?上地理課,他轉動地球儀,想著自己到日本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一樣會被排斥?他對世界產生了興趣,對國際社會產生了興趣,“就是想知道他們是怎么樣的。”
2002年高中三年級,世界杯比賽時,雖然需要緊張地學習,但是他認為不應該上課,他覺得應該集體看電視,看日本隊在世界杯上的表現。他甚至為此組織簽名,還直接跑到了校長辦公室。“只要有念頭,我一般都會行動。”當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師和同學都希望他行動。但是他的這種表現給校長帶來了深刻的印象,一定意義上也帶來了緊隨其后的北京大學的生涯。
只是在北京大學讀書時,他認為自己沒能控制好自己。“沒有勇氣說不。”但從人生軌跡來看,這是一段難忘的經歷。“就是幸運。”
他離開日本時特別叛逆,對日本充滿了厭惡,懷疑、警惕,什么情緒都有,反正就是沒有好感。
他認為他現在的成長之一是非常愿意而且光明正大地表達對日本的愛,愛它的長處,也愛它需要改進的地方。這些是他到中國以后慢慢發現的。“日本有日本的好,當然它也有很多缺點。”
他比以往更加健康地去看待自己的出生地。
歸零,無用
決定去美國前,加藤嘉一有過一番掙扎。
中國正在快速地變化中,這個過程有風險也有機會。他在這個過程中擁有過機會。但是他也慢慢地感覺到,自己當時所獲得的影響力、知名度和話語權跟自己的年齡、閱歷、能力不吻合,“這是一個膨脹的泡沫的狀態。”
他想重新去一個沒人認識自己的地方,就像當年從日本到中國一樣。“在那里,你什么都不是,就是歸零。”
怎么歸零?一些人建議他盡早去美國。“他們沒有說中國不好,而是說你也應該經歷美國。”
他不僅僅是感覺到了自己的“無用”,他發現很多人都是很健康的無用者。這個世界并不是少了誰就不轉了。
就像當年從東京去北京大學一樣,沒有任何人脈,也不知道怎么申請,同樣到了美國著名學府。他覺得至少這30多年來,很多重大人生決策靠的就是運氣。
到了美國以后,跑步、發呆、看視頻。他看了《潛伏》 《甄嬛傳》 《談判官》《蝸居》 《裸婚時代》《人民的名義》。也看日劇,就是為了了解日本的社交文化,包括人際關系。他自覺在這方面有很多欠缺。
這么多年來,他細細品味,很多年輕人經歷的,他都沒有經歷。比如說,當時太順利了,就沒有經歷年輕人特有的委屈。“怎么著都不行的那種挫敗,沒經歷過。”不帶任何的目的性跟同學瞎聊,那些日常的瑣碎的交往,他也沒經歷過。“作為一個人的生活,很不完整,很有欠缺。”
朋友說,這種事情只有通過生活來建立和體驗。他問什么是生活?他們說你自己尋找吧。所以他就有意地去看電視劇。他有時也覺得不太好,目的性太強了。所以有時會想,別人會不會覺得他這個人很無趣,沒什么話可聊。“我不覺得我這個人很壞,但是他們可能覺得我這個人不好打交道,可能也是我作為一個人的欠缺。我會一步步地彌補。”
他要求自己在美國要少談時政,他給美國生活的定義就是體驗生活,充實自己、發現自己。
在美國,他遇到過很多的挫敗,“因為我畢竟是從被寵壞的中國,到沒人認識我的美國,雖然很多人對我有幫助,我深知我什么都不是。”
他在《我所發現的美國》里寫道:我在美國的生活中感受到的無能,以及在美國的工作中感受到的無奈,最終讓我明白了“無用”的本質,即成長的邏輯。
他不僅僅是感覺到了自己的“無用”,他發現很多人都是很健康的無用者。這個世界并不是少了誰就不轉了。
在中國感受到的強烈的使命感,到美國以后發現的無用感,對加藤嘉一的人生來說兩者缺一不可,他覺得自己當下終于達到了某種平衡,“之前太畸形了,只有使命感,太不正常了。”
“會出問題的。自我迷失。”他想了想,用了這個詞。
對話加藤嘉一:40歲之前繼續漂泊
南風窗:2005年結束三年美國游學生活后,以至最近的新書出版,中國的媒體報道說,加藤嘉一回歸中國,從你的角度來講,為什么不是“回歸”日本?
加藤嘉一:日本的職場,與美國、中國比,排序、年齡很重要,資歷也很重要,我明顯沒到那個時候。但是我也很幸運,在日本也有書出,有文章寫,包括到大學以及地方政府,圍繞中國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但是我認為還不是回去的時候,一是如果我要徹底回日本,那我得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而且有點集大成的積累,以及發揮集大成積累的平臺。另外,畢竟中國、美國以及其他國際事務,在海外的經驗,對海外尤其是對中美的認識、觀察,這些才是我最大的政治資源。
我一個農三代,沒任何背景,沒任何財產,我只能靠這些東西。
那么夠了嗎?顯然沒有夠。
我今年34歲,我回日本搞什么集大成?我是曾經獲得過同齡人根本獲得不了的機會、話語權,但是如果讓我全面地爆發自己,那還是太年輕了。所以我給自己設定一個時間表是40歲以前不回日本,繼續積累,繼續漂泊,做一個無家可歸的無業游民。如果要回日本,就要徹底地放開曾經的所有,讓情緒、狀態、思想、情感都爆發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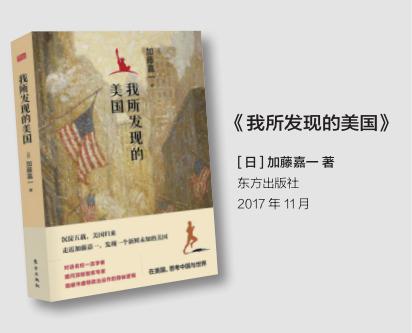
我希望把最好的自己獻給日本,但問題是這是個對話,是個碰撞。我要獻給人家,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人家不接受、不希望呢?那樣就只有反作用了,人家都不接受你現實的東西。那么我一邊積累一邊尋找一邊觀望,我會做一個判斷。現在就是這么一個階段。
南風窗:現在怎么形容你對自我的認知或者說某種社會角色?
加藤嘉一:我的自我認知就是我的名字。這個事情我大概十年前就已經想好了。對我來說,通過這一輩子最想要弄明白的是,我到底是誰,我到底干了什么,沒能干什么。所有這一切,我希望自己死亡的那一刻能夠明白,就很好了。之前我不愿意定位自己,我客觀地看我所做的事情,但我不希望跟自己說我是一個學者,我是一個作家,我是一個知識分子,我是一個投機分子,我是一個政治家等等,我都不愿意說。有可能是退休以后,我會明白我出生做的這一切,原來是為了證明我的名字。這是我給自己的一個純粹的屬于自我的對話,跟社會沒有關系。但是我也非常享受他者能夠從不同角度來告訴我,你是這樣一個人,你是這樣一個人。
南風窗:很享受一個人的生活?
加藤嘉一:可能和我小時候經歷有關系,由于我爸爸破產,我被追債,我當時得跟黑社會有接觸。所以我有點害怕社會、害怕社交。我在日本對社會是怨恨的,到中國很久以后,我才學會根除心理的陰影。與在中國的時間相比,我在美國獨處的時間比較多,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性。
這些年,我已經不會有什么恐懼了,不會沒有勇氣,也不會有那種著急和不安。
花了這么多時間終于明白,現在對我來說什么最重要,哪些是表面的,哪些是本質的,哪些是你需要用心去維護的,哪些是可以順其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