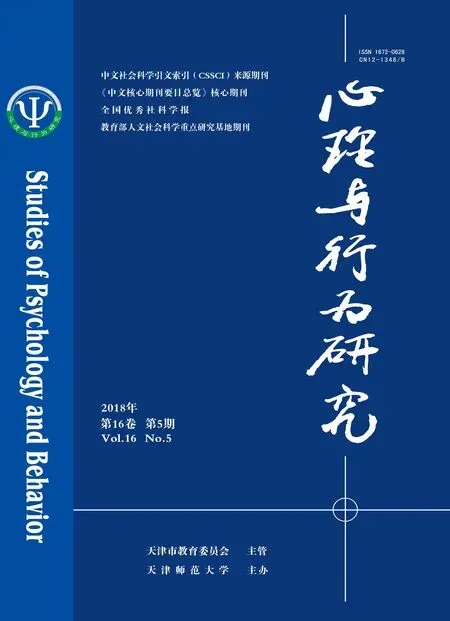威權領導對員工沉默行為的影響: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 *
李宗波 王明輝
(1 中國礦業大學管理學院,徐州 221116) (2 河南大學心理與行為研究所,開封 475004)
1 引言
在當今動態的組織環境中,許多企業都在鼓勵員工主動地提出觀點、建議或共享自己的知識,以幫助企業實現業績的持續提升。然而,組織成員有時候會保持沉默,選擇有意識地保留某些觀點或看法,是組織成員的一種自發行為。換言之,沉默行為(silence behavior)是指員工發現組織中存在或潛在的一些問題,已形成對組織有益的建議、意見及觀點,但卻選擇保留自己真實想法或信息的行為(Madrid, Patterson, & Leiva,2015; Morrison, See, & Pan, 2015)。實際上,組織中員工沉默行為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多數員工對講出工作中發現的問題心存顧慮,認為講與不講并沒有什么不同(Morrison & Milliken, 2000)。員工沉默不僅能夠導致組織無法收集到及時準確的信息,降低決策質量,還會影響到員工自身的工作積極性和投入程度,甚至產生工作壓力或倦怠(Dedahanov, Lee, & Rhee, 2016)。鑒于員工沉默行為的負面效應,厘清導致員工沉默的影響因素是該領域研究的重點。根據以往研究,情境因素如破壞性領導或敵對性團隊氛圍,以及個體差異如建言自我效能感或消極情感體驗等都能夠有效預測員工的沉默行為(Madrid et al., 2015)。但梳理文獻發現,多數基于華人企業開展的研究依然遵循了西方研究范式(Wang & Jiang, 2015; Xu,Loi, & Lam, 2015)。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導致華人企業中的領導與管理迥異于西方,這要求我們必須將沉默行為放在更具本土特色的框架內進行研究。
鑒于此,本研究擬在本土企業情境下,基于儒家文化中的關系主義和等級觀念兩個視角,考察威權領導對員工沉默行為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首先,威權領導植根于華人文化背景,是一種類似父權的領導風格,強調擁有絕對而清晰的權威,對員工沉默行為的消極影響更具有現實意義,因此本研究選擇威權領導作為員工沉默行為的前因變量。其次,根據前人研究觀點,信任是領導與員工之間社會交換過程中一個非常關鍵的中介機制(Dirks & Ferrin, 2002),并且在儒家文化背景下這種信任關系被賦予了更多私人情感色彩(鄭伯塤, 1995),因此本研究選取基于情感的信任為中介變量,以更貼切地考察威權領導對員工沉默行為的作用機制。最后,領導作用的發揮往往與其所處的情境特征相聯系,考慮到儒家文化中的等級觀念,推斷員工如何看待上下級的權力等級將會影響領導行為作用機制的發揮。因此,本研究選擇了個體層面上的權力距離導向作為調節變量,探討其在威權領導與員工情感信任關系中的權變效應。
2 研究假設
2.1 威權領導與員工沉默行為
威權領導(authoritarian leadership)普遍存在于華人企業組織中,屬于家長式領導(包括威權領導、仁慈領導和德行領導)的重要維度之一,是指領導者強調其權威是絕對而不容挑戰,對部屬進行嚴密控制,且要求部屬毫不保留地服從(樊景立, 鄭伯塤, 2000)。根據鄭伯塤等人的研究,威權領導包括四類重要行為成分:專權作風,貶抑部屬的能力,形象整飾和教誨行為,其中每大類領導模式中又包含若干具體的行為表現(樊景立, 鄭伯塤, 2000; 鄭伯塤, 1995)。以往研究表明,威權領導對員工的行為績效具有重要影響,例如能夠削弱下屬的工作績效(Chan, Huang,Snape, & Lam, 2013; Li & Sun, 2015)、導致離職傾向(Wang, Cheng, & Wang, 2016)、阻礙員工積極行為(Chan et al., 2013; Li & Sun, 2015; 李銳, 田曉明, 2014)、甚至導致偏差行為(Jiang, Chen, Sun,& Yang, 2017)。沉默行為作為員工自發的消極行為,誠然亦會受到威權領導的影響。
首先,威權領導的專權作風強調權力的高度集中,凡事傾向于自己決策,獨享信息而不愿分享,且只進行自上而下的溝通;這種獨斷專行的作風會讓下屬敬而遠之,對其沉默行為無疑是雪上加霜。其次,威權領導者經常貶抑部屬以宣示權威,如故意漠視下屬的建議與貢獻,對工作結果持批判的態度,甚至故意貶損下屬;當員工發現工作中的問題時,會認為講與不講并沒什么不同,弄不好還會引致領導的嘲諷。最后,威權領導者會注意維護自己的尊嚴,以嚴父的形象示于眾人面前,表現出極高信心,并選擇性地呈現相關信息;當員工打破沉默提出建議時,意味著指出組織中或者領導自身存在的問題,這將違逆威權領導者形象整飾的初衷,引起領導者反感甚至貶斥。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1:威權領導對員工沉默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2.2 情感信任的中介作用
人際信任(trust)與領導效能有密切關系,當信任遭受破壞時,會給團隊績效帶來十分嚴重的后果。信任是個體對于事情動向有積極預期而容易受他人影響的一種心理狀態,其愿意同對方維持一種關系,并愿意承擔可能存在的風險(McAllister,1995)。目前,學術界主流的觀點是將人際信任區分為認知信任(cognition-based trust)和情感信任(affect-based trust),前者主要是基于對方能力表現、可靠性與可依賴性等而產生的,是根據經驗進行理性判斷的結果,是最基本的信任;后者主要基于相互的關心與照顧而產生,是雙方之間特殊的情感連帶,更多是一種感性的表現,也是更高層次的信任(McAllister, 1995; Ng & Chua, 2006;Schaubroeck, Lam, & Peng, 2011)。當下屬信任領導者時,會相信自己的權力和利益不會被限制或利用。威權領導對情感信任的負面影響可以從三個方面解釋。首先,相互吸引與交往是信任的基本條件,威權領導者獨斷專行的作風,有意地控制關鍵信息,甚至漠視下屬的合理建議,這將降低上下屬之間的交流頻率與深度,破壞雙方的信任基礎。其次,善意和正直是信任的重要決定因素(Zhu & Akhtar, 2014),威權領導者經常嘲諷、貶抑下屬的行為,會導致員工認為領導者缺乏善意、并不關心下屬的發展和期望,從而產生自己未被善待的知覺,進而避免與領導者產生特定的依附關系。最后,當工作目標達成時,威權領導者會將之歸因為自己的英明領導,而工作失敗時則會認為是下屬的工作能力不足,此類推過攬功行為會讓員工認為領導者不夠正直,從而降低對其信任。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2:威權領導對員工情感信任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Dirks和Ferrin(2002)的研究指出,信任是領導與員工之間社會交換的重要基礎,員工對領導者的高水平信任有助于促進或強化相互之間的社會交換質量。根據社會交換理論,當員工對領導產生高水平的情感信任,并感受到領導對自己的關懷與照顧時,依據社會交換的互惠原則,他們會相應地增強自己回報領導的義務感與責任感,通過提升角色內績效甚至展現超越角色要求的利他行為以回報領導者。此外,由于員工指出問題或提出建議時,可能打破組織和諧氛圍而具有一定的風險性,高信任水平有助于降低這種潛在風險(Dedahanov & Rhee, 2015)。當員工對領導具有較高信任時,他們會有較低的風險顧慮,從而愿意打破沉默指出問題。相反,若員工對領導缺乏信任,他們會更多地擔心自己公開發表建議或意見所帶來的負面評價,從而對組織中存在的問題保持沉默以獨善其身。以往研究亦證實,對上司的信任能夠減少員工的沉默行為(Dedahanov &Rhee, 2015; 鄭曉濤, 柯江林, 石金濤, 鄭興山,2008)。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3:情感信任在威權領導與員工沉默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2.3 權力距離的調節作用
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最初被用來衡量一個社會接受和承認權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后來越來越多地被用于個人層面的研究,它指的是在組織中個人接受權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Hofstede,1991; Kirkman, Chen, Farh, Chen, & Lowe, 2009)。在組織研究領域,個體權力距離導向經常被作為組織管理或領導行為與員工表現之間關系的調節變量,這種將組織管理與文化情境綜合考慮的研究范式也是眾多研究的共識。威權領導會削弱員工對上司的情感信任,但這種影響效應在不同權力距離導向的員工身上可能存在差異。高權力距離導向的員工認為領導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下屬需要無條件服從;領導在做決策時并不需要征詢下屬的意見,也不應該把重要任務交給下屬;領導與下屬之間應當保持距離,不應該有過多工作之外的情感涉入(Daniels & Greguras, 2014)。高權利距離導向員工的價值規范符合威權領導的行為表現,他們認為領導的威權不容挑戰,彼此的交往也應該局限于工作范疇,不應該有私人情感的涉入。因此,無論領導者表現出何種行為,員工對上司的信任都不會受到大的影響,不過此時信任程度處于較低水平。相反,低權力距離導向的員工認為領導與下屬之間應該平等相處,權力的高低僅表示工作角色與分工的不同(Daniels &Greguras, 2014)。當上司表現出威權領導行為時,違背了自己所持有的價值規范,員工會產生較大的抗拒感,盡管囿于地位差異有時甚至需要壓抑自己的真實行為態度,但這終將會嚴重傷害到下屬對領導的信任程度。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4:權力距離在威權領導與情感信任之間起調節作用;即當權力距離越高時,威權領導與情感信任之間的負向關系越弱。
綜合上述假設本研究進一步推斷,員工權力距離導向對情感信任在威權領導與下屬沉默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可能也存在調節效應,即當員工權力距離導向較高時,威權領導經由情感信任的中介作用而對下屬沉默行為產生的間接影響相應較弱;相反地,當員工權力距離導向較低時,通過情感信任而傳導的威權領導對下屬沉默行為的間接效應則相應增強。
假設5:權力距離對情感信任的中介效應具有調節作用;即員工的權力距離導向越高,這一中介作用越弱,權力距離導向越低,這一中介作用越強。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被試主要來自廣州、佛山、徐州、蘇州和鄭州等地企業,涉及機械制造、房地產、餐飲服務、信息技術、生物科技和服裝加工等多個行業。本次調查采用領導—員工對偶的方式,共計發放問卷350套,回收領導填寫問卷312份,員工填寫問卷289份,回收率分別為89.14%和82.57%。進行領導—員工匹配、以及剔除無效問卷后,最終得到有效問卷249套。就領導特征而言,男性174人,占69.88%。就員工特征而言,男性141人,占56.63%;在員工年齡方面,平均年齡為30.64歲,標準差為4.93;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大部分員工擁有大學本科(118人)或專科(99人)學歷,分別占到47.39%和39.76%;員工任職期限主要以1~3年為主(91人),其次是3~10年(83人),分別占到36.55%和33.33%。
3.2 測量工具
威權領導:采用鄭伯塤、周麗芳、黃敏萍、樊景立和彭泗清(2003)研究中所使用的威權領導量表,共包括5個題目,如“本單位大小事情都由他/她自己獨立決定”(1=從來沒有, 6=非常頻繁)。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4。
情感信任:采用Ng和Chua(2006)研究中使用的中文版情感信任量表,共包括4個題目,如“我能夠與他們自由地談論我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并且知道他們愿意傾聽”(1=完全不符合,6=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3。
權力距離:采用蔡松純、鄭伯塤、周麗芳、姜定宇和鄭弘岳(2009)研究中所使用的權力距離量表,共包括5個題目,測量個人層次的上下屬權力不平等程度,如“下屬不應該對上司的決策有所質疑”(1=完全不同意, 6=完全同意)。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1。
沉默行為:采用Tangirala和Ramanujam(2008)研究中使用的員工沉默行為量表,共包括5個題目。由于原量表的應用對象是醫護人員,為了適用于本研究情境,在不改變原始涵義的原則下對量表題目進行了適當修正,示例題目如“盡管他/她有可以改善單位工作的想法或建議,但他/她并沒有提出來”(1=從來沒有, 6=非常頻繁),要求上司評價直接下屬表現出此行為的程度。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7。
4 研究結果
4.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1呈現了各研究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從結果可以看出,威權領導與員工沉默行為顯著正相關(r=0.17, p<0.01),與情感信任顯著負相關(r=–0.52, p<0.01);情感信任與員工沉默行為顯著負相關(r=–0.30, p<0.01);權力距離與員工沉默行為顯著正相關(r=0.22, p<0.01)。因此,研究假設1~3得到了初步驗證,為后續層次回歸分析提供了可行性條件。

表 1 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
4.2 研究假設的檢驗
首先,運用層次回歸分析法檢驗威權領導對員工沉默行為的簡單直接影響。數據結果顯示,在控制了人口統計學變量之后,威權領導對員工沉默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b=0.17, p<0.01),假設1得到驗證。
其次,運用Hayes開發的SPSS/SAS宏程序PROCESS分析情感信任在威權領導與員工沉默行為之間的單純中介效應(見表2)。分析結果顯示,在控制了人口統計學變量后,威權領導對情感信任(M1, b=–0.52, p<0.01)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將威權領導與情感信任同時置入回歸模型后,結果顯示情感信任對沉默行為的影響顯著(M2, b=–0.29, p<0.01)。同時,運用偏差校正的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法對情感信任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在威權領導影響員工沉默行為的路徑中,情感信任的中介作用顯著,間接效應值為0.15(p<0.01),占總效應的86.7%,Boot 95%置信區間為(0.08,0.23),置信區間不包含0,表明情感信任的單純中介效應顯著,假設2和假設3得到驗證。

表 2 情感信任的單純中介效應分析
最后,本研究繼續運用宏程序PROCESS分析員工權力距離導向對威權領導與情感信任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以及對情感信任中介效應的調節作用(見表3)。分析結果顯示,回歸模型中威權領導與權力距離的交互作用對于情感信任的影響達到了顯著性水平(M3, b=0.11, p<0.05),即權力距離的對威權領導與情感信任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明顯。

表 3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
為了更直觀地呈現權力距離對威權領導與情感信任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研究者繪制了調節效應示意圖(見圖1)。由此可以看出,在員工權力距離導向高的情況下,威權領導與情感信任之間的負向關系較弱(b=–0.36, p<0.01);在員工權力距離導向低的情況下,威權領導與情感信任之間的負向關系較強(b=–0.58, p<0.01),假設4獲得驗證。

圖 1 權力距離對威權領導與情感信任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
進一步檢驗了權力距離對情感信任中介效應的調節作用(見表4)。結果顯示,當員工的權力距離導向較高時,威權領導通過情感信任作用于員工沉默行為的間接效應較弱(ρ高權力距離=0.10,Boot 95% CI不包含0);當員工的權力距離導向較低時,威權領導通過情感信任作用于員工沉默行為的間接效應較強(ρ低權力距離=0.17, Boot 95%CI不包含0)。根據Hayes(2015)提出的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檢驗參數Index=–0.03,其Boot 95%置信區間為(–0.07, –0.01),且不包含0。綜合可知,情感信任對威權領導與員工沉默行為之間關系的中介效應會受到權力距離導向的調節,即產生了被調節的中介效應。因此,假設5亦得到實證支持。

表 4 有條件的間接效應分析
5 討論與分析
5.1 研究結果討論
首先,威權領導對員工沉默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Morrison和Milliken(2000)指出,組織沉默主要是由管理者所造成的,以往眾多研究也證實了該觀點。例如,領導的辱虐管理或威權管理方式會導致更加嚴重的沉默行為(Xu et al., 2015;于桂蘭, 楊術, 孫瑜, 2016),而積極領導方式則會打破員工的沉默行為(Lee, Choi, Youn, & Chun,2017; 呂逸婧, 蘇勇, 2015)。本研究再次證實了威權領導這種家長式專權管理模式對員工沉默行為的消極作用。對員工來講,威權領導行為在客觀上關閉了員工指出問題、提出建議的上行溝通通道,在心理上也增加了員工在權衡沉默或建言時的風險感知。因此,若要打破員工沉默,首先要改變威權領導的行為模式。
其次,情感信任在威權領導影響員工沉默行為過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這意味著,威權領導不僅能夠直接影響員工的沉默行為,還能夠通過破壞員工對上司的情感信任,進一步導致員工表現出更多的沉默行為。該結果從人際關系視角出發有助于深入揭示威權領導與沉默行為之間關系,更貼合本土企業實際。該結果也符合Dirks和Ferrin(2002)提出的“領導-信任-行為”的理論框架。據此可知,員工會根據領導表現出的行為方式推斷其能力、以及真誠與正直等品質,從而評估彼此之間的關系質量以及領導的可依賴性。如果下屬認為領導者不可信,必然會表現出消極的態度、行為與績效變現等工作反應。相反,員工若對領導者產生信任,則會有積極的工作反應。
最后,員工的權力距離導向對威權領導與情感信任之間關系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更進一步地,權力距離導向對情感信任的整體中介作用亦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該結果同周建濤和廖建橋(2012)關于員工建言的研究結果是間接一致的,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員工權力距離感越大,威權領導對員工建言行為的影響越弱。本研究結果有助于理解威權領導對員工情感信任和沉默行為發揮影響效應的邊界條件或情境限制。威權領導影響效應的發揮會受到員工個體價值取向的約束,當員工本身權力距離感較高時,其對上司的情感信任與沉默行為受領導行為的影響較小,更多是遵從自身內在的價值規范;反之,當員工權力距離感較低時,其態度與行為反應會跟隨領導行為的變化而改變。這也符合權變領導理論的觀點。
5.2 實踐啟示
員工有意隱瞞信息的沉默行為將極大影響組織決策的正確性與及時性,也會阻礙組織的學習和發展。結合本研究結果,提出建議:(1)隨著觀念變遷,組織應該充分認識到家長式威權領導行為的弊端,要鼓勵員工參與組織決策并適當授權,對員工所取得的成就給予及時的贊揚,同時也要培養領導者正直善良的品質。(2)改善領導行為方式的同時,要積極培育良好的人際溝通氛圍,暢通自下而上的溝通渠道,是建立信任的基本條件;同時要關心員工利益,在工作和生活方面提供最大的幫助和支持,以取得下屬的信任,進而收集更多的反饋信息。(3)針對不同的員工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尤其是面對低權力距離導向的員工,在日常工作中應該平等地交流溝通,多用上述激勵措施。
5.3 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局限之處:首先,本研究使用截面數據進行分析,無法檢驗真正的因果關系,未來研究可采用縱向研究設計。其次,雖然本研究采用“領導—員工對偶”問卷調查,避免了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但受限于領導對員工沉默行為觀察的客觀性和全面性,由上司評價員工沉默行為的做法可能放大了測量誤差,未來研究可考慮自評與他評相結合的綜合測量方式。最后,家長式領導強調“恩威并施”,而本研究只選擇了威權領導,沒有考慮仁慈領導對員工沉默行為的影響,未來研究可以將威權領導和仁慈領導同時納入研究框架。
6 結論
本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威權領導能夠正向預測員工的沉默行為。對上司的情感信任在威權領導影響員工沉默行為的過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針對不同權力距離導向的員工,威權領導對情感信任的影響程度不同,權力距離導向越高,威權領導對情感信任的影響越低。進一步地,威權領導通過情感信任影響員工沉默行為的整個過程都受到權力距離導向的影響,即存在有調節的中介效應。